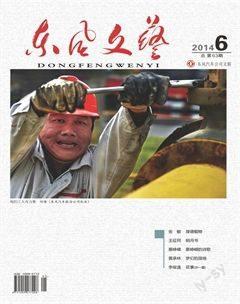去来兮,故乡鸟语(外一篇)
傅祥友
遥远的天边儿,飘来,飘来故乡的鸟语;
幽幽的故乡鸟语,带着泥土的芬芳,春雨秋风一样,潜入了城中人,我的梦乡……
时时地,梦归故乡——
悠悠碧空下,大朵的白云娴静地卧着,入睡如梦了似的;倾听着童话韵味的鸟语,品嗅着不知名的花香,小小的我度过了虽贫穷却环保,且欢乐的七彩童年。
如果没有空中、树梢、林间、房前、屋后涂鴉着的鸟儿,没有鸟语在夜空自由的吟唱,我想,我的营养不良的童年又该是另一种的饥饿,另一种呆板的黯淡色调了。
在鸟儿们扑扑楞楞的嬉戏里,唧唧喳喳的晨问里,我们会一骨碌儿下床,喝碗红薯稀饭,背起老棉布缝制的书包,左邻右舍吆喝一声,三五成群雀跃着,叽喳着,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向着三几里外的学校蹦蹦跶跶而去。
那时,只要是乡下的孩子,几乎都是在鸟儿清越的歌唱声中成长着;对大自然的认识,似乎也是从鸟儿身上开始的。
……对故乡鸟的别样的依恋中,我记忆着,也享受着许多的有关鸟的诗词和成语里的精神食粮。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微微的南来的风中,故乡的美丽是在此时生动起来,也是在此时进入世外桃源意境的。这是一幅怎样的清亮的水墨田园!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飘闪的绿丝绦,高远的蓝天,悠然的白云朵,离不开鸟的翩翩舞蹈。大自然的舞台上,总有着精灵一样的舞蹈家表演着!
“沉鱼落雁”、“燕雀处堂”、“雪泥鸿爪”、“鹦鹉学舌”、“鸢飞鱼跃”等等,这些或飞翔着,或小憩着的鸟,在与人的和谐相处中,以彼此特别的情谊,演绎着一个又一个的传奇故事,孵生着一个又一个的奇闻掌故,谱写着一曲又一曲的生态文化。
是啊,故乡的鸟儿,都是大自然时装的标致模特,勤勉的环保使者。每一种鸟儿,都有着非凡的霓裳羽衣,都扮着缤纷的盛妆;即便在不同的季节,都有着不同的鸟儿闹枝头;空中飞翔着的,是不同鸟儿的快乐!
是啊,故乡的鸟语,都是大自然的天籁之音,带着花香的清澈的歌声。她们的每一声啼鸣,都带着谜语一样的玄妙,都长了翅膀般的在乡下人的耳畔飞翔!
这些宇宙间最为质朴的歌唱家,最为率真的演奏家,它们在飞翔中,在栖息中,合奏着大自然的生命交响曲。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在故乡,在遥远了的故乡,梦里一样的故乡啊,总有着鸟的情结在牵挂中浓郁起来。
故乡的那些鸟儿,故乡人不知其学名,却别出心裁,创造性地依其啼鸣声而名之——
暖的惠风,从南方裹着性感眩晕般袭来,五月端午便莅临,金色沁镀上村头树上的杏儿后,又从满谷、满坡的麦尖儿上滚过时,“脱脚儿过河”(布谷鸟鸣)边在田野上、小河畔歌唱着季节的变换,催促着农人要手脚麻利,割麦、插秧“双抢”在即。
蒙咙着几许忧伤的黄昏时分,“哥哥儿苦”在忧忧地哀诉着,一声复着一声,不绝盈耳。这样的鸟儿,这样的哭鸣,总让小小的我们心头儿莫名地发颤,担心着她哭哑了嗓子。
听母亲说,“哥哥儿苦”背负着一个凄惨悱恻的传说。老辈老辈的人说,从前,有穷苦人家的哥妹相依为命,哥哥在地主家打工时被害。多日不见哥哥回来,妹妹便去地主家看望哥哥。地主编造谎言,说哥哥外出,便拿哥哥的肉来招待妹妹。妹妹不知是哥哥的肉,便吃了。心有灵犀,妹妹晓得吃了哥哥的肉,晓得了哥哥的冤屈,便变成了一只鸟,整天整夜地在地主家的上空嘶鸣“哥哥儿苦”,哭得村里人个个潸然泪下。
讲完了“哥哥儿苦”的故事,母亲红了眼眶;听完了“哥哥儿苦”的故事,小小的我们咬牙切齿,恨不得马上去找地主老财算账。
是啊,一声的鸟鸣会给小小的我们上一堂难忘的人生课。
“黄瓜瓠子着点油儿”,带着与人为善的歌声,从这一家的房顶唱到另外一家的前院,快乐的,充盈着希望的话语,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温暖。那个时候的乡下,食用的油料奇缺,每次炒菜,母亲会用瓷调羹勺儿,在祖上留下的瓷罐儿里,轻轻地舀出一勺,小心翼翼地在大铁锅里均匀地淋上一圈儿,香喷喷的油沁润开来时,哗地声响,菜下锅了。
当然,伸着脖儿,盯眼看的我们,口水也就流了出来。
于是,“黄瓜瓠子着点油儿”,形象而又生动的鸟语,总会给乡下人唱来无限的幸福的企盼。
哦——,还有那年年春天南来的小燕子,剪着双尾,带着桃红柳绿,飞越千山万水,在农家堂屋梁上安家落户,很多的时候且飞且语:“不吃米,不吃粮,在你家梁上筑个巢!”这是与我们最为亲近的鸟了。
瞧啊,故乡的山冈丛林,家家的屋前屋后的林子,都是鸟儿的家园。
那时,小小的我们曾爬上树梢掏鸟窝,摸鸟蛋儿,捉幼鸟儿。大人见了,会吓唬说,当心下雨雷打人哟——,吓得我们将红嘴嫩鸟仔细地放回巢里。我们也曾拿自制的弹弓偷偷地袭击鸟儿。大人们便指着空中盘旋着的鹰,教训我们:“老鹰瞅见了,会下来叼走娃子的!”唬得我们将弹弓藏了起来。乡下人用朴素的近乎迷信的伦理来关爱着鸟儿们。
尤为享受的,是放牛的我们躺在青草上,看头上的鸟儿忽高忽低地跳着舞,听鸟儿们时断时续的歌唱。哎呀,云雀子在空中弹射着,撒下满坡的欢笑;钓鱼郎穿行于河畔的水竹、水草间,清亮的甚至有些尖利的叫声,仿佛在告诉同伴有怎样的敌情;“长脖老儿”就显得低调得多,寡言少语,像个隐士,时而也会独奏些很古的曲调……
在草丛里打着滚儿。嗅着淡淡的花香,我们想象着自己要是一只小小鸟儿该多好,那样就可以在蓝天白云中飞翔。
事实上,和现在我的背着沉重书包的孩子比来,那时乡下孩子的童年,幸福得就像那鸟儿一样,自自在在地飞舞!
后来,我们陆续长大,外地求学,离开了故乡。
世事更迭,故乡也在发生着巨变。土地联产承包后,家家可以作主,对大自然的攫取就难免过度了,顾不得生态环保,拼命地向土地索取。于是,曾经郁郁葱葱的山冈成了庄稼地,远远地看去,仿佛头上的癞痢;绕着村子的清亮亮的乡河,被村人拦截成了几处,建成了用于灌溉和养殖的蓄水坝,微生物过剩的绿腥腥的水里,小虫子乱窜,连衣服也不敢洗了。村子里的老树被砍伐了,两百、三百元地卖给了小贩们,就地加工成粘合板材。就像人没有了房屋一样,没有了可以栖息的家,鸟儿们惊惶失措,四处逃窜。其间,不时有猎枪“啪啪——”地围追堵截:还有,在城里人指导下由乡下人独创的“粘网”,这些别样的“陷阱”就是专门为单纯的鸟儿们准备的。非死即伤的鸟儿们,以环保的野味被城里有身份的人高价吃掉了。
多年后,城里人的我逃也似的回到故乡。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鸟儿,在故乡一时竟成了稀罕之物,连那些招人嫌的碎嘴子麻雀儿也不多见,虫害也多了起来。没有了鸟语的乡下,似乎不再是乡下了。新生代的乡下孩子,只有在教科书寻找故乡曾经的鸟儿了。出生在城里的孩子,看到的几种鸟儿,也是在公园里结识的。他们回到了父亲儿时的乡下,却没有见到父亲眉飞色舞鼓吹的那些啁啾的鸟儿们。
真的,我不知道怎样向城里的孩子们解释。我只能说,我万分地怀想故乡曾经的鸟语;我只能说,那时的鸟语才是大自然除了人类的最优美的音乐,它们,那些可爱的鸟儿们,才是最具天赋的歌唱家。
夜月清辉中的温馨的鸟儿的呢喃,只能在梦里闻见!
突然想到一些有关鸟儿的故事。没有了生态文明意识的乡下,终将“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景致留在了古书上了。想想啊,没有了鹤,没有了蚌,哪里还有渔翁!
“大鹏展翅九万里”,“凤凰涅槃”,“鹰击长空”,“鹦雀安知鸿鹄之志”,“鹤立鸡群”,“鹊桥相会”的故事,成为没有了实物诠释的传说了。那些永远的有关鸟的掌故里,没有了活生生的鸟语!
物极必反。鸟的日渐遁迹,也曾引起了地方政府的关注。于是,终于“亡羊补牢”,下令收缴火铳,严禁捕食。
慢慢地,今天的乡下似乎有了新的迹象,曾经的鸟儿来了,曾经的鸟语开始萦绕耳际。
呵呵,“咕咕”叫的鹧鸪,淘气的“毛炸子”,“喳喳”报喜的喜鹊……四处漂泊的游子,相继归去复来兮!
可是,它们依然没有栖息的安全的家。村子里,只有乡下人种植的经济树木,那些速生的白杨,大了,便被贩子收购剥皮了。那些山冈,没有了树木,在水土的流失中,生长着低产的庄稼。乡河,也不再像河了,淤泥几乎填平原来的河道;清灵灵的低头张口就可以解渴的水,变成了绿嘟嘟的秽浊,里面生长着土腥臭气的激素鱼。是的,无论是山冈上,还是村子里,还是乡河里,都生长着乡下人的没有环保色彩的希望!
更为可怕的是,在城里人腹欲的唆使下,故伎重演,乡下人又开始悄悄地铺开了“粘网”,一个又一个的看不见的“陷阱”在等待着归来的鸟儿们!
是啊,我们可以逃离,逃离曾经贫瘠的乡下,跻身到城里生活,筑巢繁衍后代。可那些鸟儿们,它们能逃离乡下到城里吗?城里的建筑森林,透露着硬邦邦的杀气;城里人的嘴巴,一直在望着野味吞咽着口水。
鸟儿们,真的无路可逃了?
城市在重污中开始呐喊了。而曾经的乡下,若不再革命,去徹底改变,鸟儿们真的死路一条!
真的!
古书上记载有“凤”与“凰”,你见过吗?没有!于是,我们总会自我安慰:那是传说中的一种鸟,一种古人想象的鸟!因为,现实中早已经没有了这种鸟迹啊!
无论是什么样的谎言和掩饰,不管是谁的,总归见不得太阳。这是我回到乡下和父亲聊天说到鸟们的命运时,父亲望着光秃秃的山冈时说的一句话。
我的父亲是一个布衣文人,亲近着鸟儿们,听到“啪”的枪声,看到城里人来收购鸟儿,他老人家就会恨恨地骂“个舅子的——”。
我总以为我儿时的鸟语令人怀恋,可父亲说及他印象中的家乡鸟语,那才叫“了得哟——”。父亲说,那时的鸟儿几多的,多到曾与人们过不去,村里每一棵大树上都盘结着鸟窝,叽喳喳地集会,或争吵,或打斗,或调情,或戏耍。最和人闹不快的,是它们憋不住地随时随地大小便,夏天聚在大树阴下乘凉的村人,有时候不得不戴顶草帽。一个关于鸟屎的故事,父亲讲了几遍,我忍不住前仰后合乐了几遍。故事是关于一个本家老辈人的,那是在一棵老皂角树下,忙里偷闲的村人说着家常,便有人提醒说小心树上鸟的屎巴巴,本家老辈人边说“不会吧”边抬头仰望,偏偏不巧,一坨鸟屎从天而降,正好落人老辈人微张着的口里。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老辈人一惊,不好,“啊哟——”,连声“呸呸——”,村里人知道老爷子“中彩”了,都不由捧腹喷饭。老辈人羞愧难当,又气又恼,嚯地起身,在地上摸起一块土坷垃,朝着大树梢撂了过去:“叫你们使坏——”突然来袭的土坷垃,吓坏了大树上的集会者们,先是猛地鸦雀无声,接着“哄”地四处逃散。“戏弄我?有你狗日的好受!”老辈人仰看着大树,复仇成功后的满足可想而知。于是,大树下的家常继续热闹着。可不久,上面的集会重新开始。不过,大家不再理会,有前车之鉴啊,教训中积累了经验,千万别抬头哟!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兮,雨雪霏霏。当年,大树下的聚会者中,随着我的父亲二○○九年底的驾鹤西去,几乎都不在人世了!我不知道,大树上的集会者中,它们和它们的后代而今尚有几许!
生命是一个过程,在这个无法把握的过程中,总会有许多的不可预知的变故。所以,我总在想,故乡的鸟儿,故乡的鸟语,也是大自然生命中的一个过程。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形式和内容。往先前无疑是越来越肥美丰富,往日后无疑是越来越贫瘠枯竭。难道这是自然的不可逆转和违背的法则吗!我不知道,现在故乡的鸟儿、我儿时故乡的鸟儿、父亲年轻时的鸟儿,以及父亲的父亲时的鸟儿,这种不同时段的变化,是不是在印证着诉说着什么?是的,很多的人听不懂,却也有很多人装着听不懂啊!大自然的法则,是人定不可胜天!
仰望灰蒙蒙的长天,我也只能在心里歇斯底里:归来吧,故乡曾经的鸟语!
小河
老家门前的小河,宛若一条长长的白丝绸,缠绵绵地将村子绕了大半圈儿,而后,曲曲折折、闪闪亮亮一荡而过。
小河的南岸是青青的山冈,北岸是一洼洼的良畴。很有些“一折青山一扇屏,一弯碧水一条琴”的意境。
小河源于桐柏山余脉,逶迤百里融入襄江。村里风水仙儿巴爷掐着手指说,没有小河,就没有我们这村子哟——
远离老家二十余年,小河的清流在心间依然那么温柔和甜美,汩汩的水声依然那么撩人心弦,浮动的暗香依然那么迷人魂魄。感念得久了,揪心的时候,免不了梦落小河。
是啊,无论怎样的岁岁年年人不同,小河都会生生不息地在我心地里流淌,时时刻刻游荡在我的眼前。
小河淙淙地流着,也留着我孩提时的美好时光。
春雨一落,积水划向小河的哪儿一处豁口,不待用网,随手拿了箩筐,朝生水下猛地一捞,就会捕上扑棱棱、白花花的鲫鱼。这时节的小河,处处酝酿着鱼儿们的爱情。河套里的花儿,媚眼一样地忽闪、顾盼,悄然地吐出芳香,将小河彻底地女性化了。随了梅雨的绵密、紧凑,水竹绰约起来,尖着长嘴的叼鱼郎奔走相告着,在一片片的或疏或密的翠绿中忙来忙去。
而缓流宽处积淤的白的小沙滩,成了我们的游乐场,裸脚走在细软的沙粒里,便有种被什么东西密密地舔吮的感觉。小小的我们忘我地撒起欢来,鹰啄兔子,摔绊子,抱鼓碌。野性十足的游戏,滚爬得浑身是沙儿,不必慌的,跳进清亮的潭里,一个鱼跃,便一身清白。即便入了学,小河的夏天依然是属于我们的,精光光的我们会爬上老柳树,从蔓开的侧枝上“咚”地弹进潭里,扎猛子,捉猫儿,摸鱼儿。再不,骑在窄窄的天蓝色的石板上,双脚伸进亮亮的柔柔的水里,由那些作乐的鱼儿梭子样地游来啃啮脚丫、脚心,那种酥痒时的满足无与伦比。受不住这美妙的逗弄,一缩脚,或禁不住“吃”地一笑,这些水中尤物就忙不择路地一窜,不见了踪影。戏水的快乐,美丽了我们的童年,甚至让我们忘却了开学在即。
随着“唯有读书高”的呼声春水一样高涨,我们不得不疏远了小河。然而,星期天的小河里又爆起了我们的喧闹声,无忧的流水总能流去课堂上积下的重压。于我们的眼里,小河的上游遥迢,下游深远。站在南畔最突出的松树冈上远望,小河就是一条绿白相间的带子,深情地依冈绕田,弯弯地伸向远方。我们总没有依据地猜想小河流到夕阳的地方才住的脚,夕照下熠熠的河坝,或许就是小河的家吧。
有些神秘色彩的,当数雨后天晴去河里捕鱼。下网须在子夜时分。父亲说雨后的水营养厚,供鱼可食的水草油嫩。等到天擦黑,鱼儿们就逆水而上,觅食、嘻戏或寻找爱情。待夜里零点前后饱了肚子,鱼儿们就顺水而下。父亲常在这时带我们下网,堵住鱼的回路。怕错过下网的最佳时机,我们便在院里打坐,听父亲摆他的“封神榜”。
待月亮、星子移动到一定位置,父亲打住古话,站起身说声“拿网”,我们便连一丝的睡意也没有了。于是,水乳一样且柔且亮的月光下,我们向着小河走去。此时的村庄、田野都安详地入梦了。萤火虫儿们在稻田间舞蹈着,编织着属于他们的奇妙童话。而不肯缄默的虫子们,热闹了白昼,又热闹了梦一样的夜晚,像是开家庭晚会。
而当走进小河的怀里,陡然感受到它温爱的鲜活的呼吸,流水的弹奏声时疾时缓地倾诉着怎样温馨的故事。下网的地方是有讲究的,选在河面狭小、落差大、水流急的地方。
第二日一早,从床上跳下来直奔小河的我们,就看到长长的网袋子里挤满了只能动弹的鲫鱼、鲤鱼、财鱼,有时还有团鱼、“咯呀”鱼。也有夜间知晓同伴落网而长一智“逃脫”的鱼,却只能躲在水深且缓、草密的地方。不用急的,只将上游坝口封了,待流水小了、浅了,这些自作聪明的鱼不得不顺水入网,或者卧在潭里待擒了。这些肥美的水鲜,往往成了我们的学费。真正到碗里的鱼,总是些卖不起价的“窜条儿”、“石鼓郎片”、“浪里狗”们……
昔我往矣,河水清清,绿柳依依。这便是从前的梦一样的小河了。
再次认真地面对小河时,村子里竖起了一幢幢的小二楼,以及上游介日地“哐啷”作响的小企业。
岸边的一处处百年曲柳不见了,初夏盛开的一团团香雪的槐林不见了,南岸的青松冈仿佛秃了头。黄鹂、“布谷”、“脱脚过河”、“哥哥苦”们,那曾经鲜亮的叫声绝耳了。几人深的潭被淤成了泥坑,缓水面的地方被村人营造成了稻田,河套因开垦,水土流失,而褴褛不堪了。河里的鱼,也只有生命力极强的“窜条”了。令人痛惜的是鲤、鲫尚未长成,便被人投药捕捉了。僵硬的、灰脱脱的小河,从冈坡脚儿、田野襟儿下忧忧伤伤七扭八拐地远去了。
无可奈何花落去。小河的春天就这么过去了。我无法考据小河的历史,只听村里老人说,六十年前,小河的上、下游还有原始森林。
于是,每次回老家,我都会执著地独自一人在朝霞灿烂时分。站在南岸冈顶上,看炊烟缠绵的村镇,感受日出一样的生命不可阻挡地到来。也在残照时分,走进小河的襟怀,面对尚有几许碎银闪动的下游河坝,体悟生命的无限沧桑,生出不尽的感伤来。久久不散的情绪,总使我想及那句不可言传的诗句: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小河的没落,只能让我更为珍惜地去寻找那些久远的感觉和记忆来。
我对它的思念,不只是无名花草的芬芳对我永远的迷惑,不只是对潭里翻跟头无愁的儿童和柳下苦读有虑的少年的追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