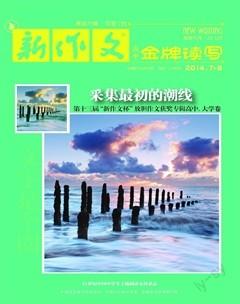逆时针
王雅洁
评委意见:青春期的任性、叛逆好像是雨季里不由自主的感冒,来时让人预料不及,好像一下子就完全变了个人,变得那么执拗,那么封闭,那么不近人情。这篇文章,以两个女孩在异国他乡相遇,然后彼此交流为故事核心,把原本看似无解的叛逆的心,慢慢打通,融化了。文章在舒缓的笔调中,让人体味人生深处的各种况味,有深入浅出之感。文章整体的基调,还是予人以希望,就如一束慢慢开放的花,一瓣一瓣地慢慢开,然后花香逐渐弥漫了我们的心。
(浩风)
星辰交错,塞纳河在一城的繁华中从容流淌,生生不息。
我逆着风在街上疾走,错过了一路的奢华与浪漫。
当淡黄灯光笼罩住双眼,我停下脚步。
Together。
我回来了。
我拖着沉重的行李箱在巴黎街头游荡。看天色渐晚,身旁是一群群金发碧眼的人。站在这样的人潮中,我典型的东方面孔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皮质箱的滚轮在地上划出冗长而沉闷的声音,与夜晚游走在耳畔的风交织成没有任何节奏的乐章。我抬起手,扣住了风衣最上端的那粒纽扣。
因为一个人,所以更要照顾好自己。
不知道走了多远,双腿越发酸困,我索性就这样停在了路边。有一些人走过来问我是否需要帮助,我都一一摇头。
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因为这本就是一场逃避现实的旅行。
我理了理鬓角的碎发,把他们别在耳后,心里有轻轻叹气的声音。
“吱——”尖锐而短暂的开门声。我扭过头,身后的花店里走出一位素净淡雅的女子,纤瘦高挑的身上穿着一条波西米亚风情的碎花长裙。而令我最为惊异的是,她有着和我一样的黑色眼睛。
“你从哪儿来?”她看着我,用法语问。
“中国。”我回答。
她的眼底閃出一丝惊喜,于是接下来我便听到了一句地道的中文。
“方便进来坐会儿吗?”
不想拒绝,似乎也没办法拒绝。
暖黄色的灯光。干净明亮的落地窗两边是用丝带束起的米白色窗帘。窗前随意摆放着木制的桌椅,精心插配的花在地上摆了一圈又一圈,只留下了一条小小的过道。枝条编成的花篮堆在墙角,大束大束的玫瑰艳丽地开放。
我站在店里,有些不知所措。
她接过我的行李箱,靠在桌边,让我坐下。然后又去冲了一杯热奶茶递给我。
“谢谢。”我说。
“没关系。”她微笑着,拉开另一张椅子坐下。
“你叫什么?”她问。
“纪含。你呢?”
“唐羽。”
“真好听的名字。”我说。
她笑,然后说:“你来这儿做什么?我看见你一直站在门口。”
我端着奶茶的手突然顿住了。长时间的沉默。我扭头望向窗外,天空已合上了眼,地上正是华灯璀璨之时,家中是否也如此呢?
“你怎么了?”
我从思绪中惊醒:“哦,没事儿。”
我抱歉地笑笑,然后看到她眼底掠过的一丝担心。
我突然想起来什么,问:“我能在你店里待一晚上么?明天一早我就去酒店。”
她愣了一下,环顾四周:“可是这里没有睡的地方。”
我笑:“没关系,我在桌上趴一会儿就行,白天喝了好多咖啡呢。”
她终于还是点点头。
我趴在桌上,看着窗外的浓郁夜色,视野渐渐模糊。
次日清晨。
“谢谢你。”我努力睁着因为一晚没睡而红肿的双眼,对着唐羽微笑说。
她点点头,然后像是想起了什么,急忙转身跑到小木桌旁,拿出纸和笔,写了一会儿之后递给我。
我接过来,上面有她简单的联系方式。
我的鼻子突然酸了一下,想说什么,却无法开口,只是回报性地点头,然后转身。
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善于表达感情的人,即使接受的是暖如冬阳的无尽关怀,所以请你原谅。
扭过头的一刹那,我看见唐羽张了张嘴,却终究没有说出什么。我不想再问,只是推开门头也不回地离去,像当初离开家那样,坚定而决绝。
辗转到达酒店后,服务员带着我找到房间。
单人床,壁灯,咖啡色的窗帘。
我把行李箱扔在床上,开始从里面掏东西。抖衣服的时候,一张小纸条从里面掉了出来。我拿起来看,是唐羽的联系方式,只有短短几行。
她也很忙,没必要麻烦人家了吧?
我抬手准备丢进纸篓,突然想起电话号码是不应该直接扔掉的,于是我抬起手把纸撕成碎片,扔了进去。
白色的纸片在空中飞舞飘旋,然后静静落入纸篓,那一刻我好像看到纸片上有密密麻麻的字。
等等。密密麻麻的字?
我拾起一块碎纸,翻到背面,果然看到了我不曾见过的字眼。我从纸篓里捡回了所有的碎纸,拼拼图一样把它们重新组合。几分钟后,我看到了一段用生硬的汉字写下的话:
“我在法国待了也有好几年了。可是很少有在你这个年龄孤身一人来到这里的。我只是希望尽我所能帮助你。”
我突然想起之前我转身离开时唐羽欲言又止的表情。
我慢慢蹲下,趴在床沿。这时有阳光透过大玻璃倾泻而下,把房间分成了明暗两块。
而我正被阳光包围着。
眼前那张支离破碎的纸被照得发亮。
这么多天我第一次感到了温暖,真好。
我静静站在街边,头顶是写有Together的招牌。
没错,就是那家花店。
唐羽看到我进来,眼里流露出深深的惊讶。
“你……”
“以后我在你这当义工吧。”
她稍稍愣了一下,随即扬起嘴角。笑靥如她身边绽放的花。
这一段时光算是我几年来度过的最安定的日子。
我和她每天坐着小木椅,用不同颜色的丝带束好一捧捧花,递给客人,然后看着他们微笑地走出店门。我见过热恋中的情侣,见过拿着零花钱给母亲买花的小男孩,见过成熟稳重的中年男子,甚至见过满头白发的老人。
一段时间后,我从酒店退了房间,搬进了唐羽的公寓。休息的日子,我们常常跑去塞纳河左岸,在咖啡屋里一待就是一整天。亦或是流连于行行色色的画廊,再或者是坐进放映有老电影的小剧院。
那个晚上我和她坐在街边的咖啡馆里。桌上摆着白色的杯盘,里面有着冒热气的香浓咖啡。她穿着素雅的白色长裙,静静地坐在对面,大波浪的栗色头发柔软地垂在腰间,旁边不时有英俊的法国男子回过头来看她。
她确实很美。
我暗暗笑,突然想起我还不怎么了解唐羽的故事。
“嘿。”我轻轻叫她。
她回过头。
“你从小就在法国吗?”
“不是,我十八岁的时候来的这里。”
“那你小时候是在哪里长大的?”
坐在对面的她突然沉默了。短短的几分钟,却像是几个世纪那样漫长。
“都过去了。”良久,她轻轻说。
我看着她低垂的眼,不再作声。
只是心中疑惑。
后来回到公寓,我非要跟唐羽挤在一张床上。她只得无奈同意。
我沉沉睡去。
梦中是大片金色的麦田,我拉着父母的手奔跑,他们的脸上是藏不住的笑。突然间母亲转身走了,走得那样快,我大声地叫,却发不出声。我扑到父亲身边,哭着喊着要他把妈妈找回来,可他只是摇头,只是摇头……
在梦里我哭着,直到双腿瘫软在地上。
我迷迷糊糊地梦着,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只记得自己身上全是汗。
慌乱之中似乎有一双手握紧了我,是那样地温暖有力。
我突然很心安。
哦,忘记说我的故事了。
董事长的女儿,身份应该算是尊贵吧?可是我不快乐,也从没有觉得快乐。
你们或许会反驳我,说你都拥有这么多了,你还想要什么?
我拥有的多么?我怎么感觉我一无所有。
你们知道么?他们好像很爱吵架。
那些日子,我看着父母的面容在争吵中衰老,却无能为力。我感觉自己是那么渺小。当家里又一次爆发了剧烈的争吵时,我作出了离开的决定。他们当然不同意,可是在我那样坚决的态度下他们还是妥协了。爸爸坐在偌大的沙发上,说:“什么时候想回来了,给我们打电话。”
于是我就来到了这里。
我的故事很简单。
而唐羽的故事,我并不是很清楚。
“纪含,我出去买点东西,你帮我看一下店。“
“嗯。“
“嗡嗡……”震动声打断了我手中的工作,是唐羽的手机。我拿起来,按下接听键。
“羽儿?“
“请问您是?”
“我是……”她顿了顿,犹豫许久,才轻轻说:“我是她妈妈。”
“我知道了,等她回来我会转告她的。”
“不必了,谢谢你。”
“啊……”耳边已是一阵忙音,我放下手机,心中诧异。
“纪含?”
我扭过头,“刚刚你妈妈打电话来 。”
“给我手机。”
我遞给她。她翻开通讯记录。我看到她的手在微微颤抖。
“怎么了?”她不回答,只是摇头。
许久,我听到她轻轻的叹气声,带着她这个年纪不该有的沉重。
夜已深,我抱着被子准备回房间睡觉,忽然看到唐羽房间门缝里透出微弱的光。
我悄悄推门进去,唐羽半靠在床上,一动不动。
“唐羽。”我轻声叫。她扭过头,眼角的泪折射出晶莹的光。
我愣住。“你怎么了?”
沉默,还是沉默。
空气似乎凝滞了,世界寂静无声,仿佛只剩下我和她这样相互看着,窗外是无边的黑暗。“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纪含,”唐羽颤抖着拉住我的手,“你听我慢慢跟你说。”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就那样听着她用微颤的声音讲述她的过去。时光好像静止了,在这个时空里,过去那些无法忽视、无法忘却的东西,就那样横亘在眼前,带着撕扯心头般的疼痛。
她是孤儿。或许现在这样说不太准确,因为她在十岁那年被一对夫妇收养,过着还算安定的生活。后来,一个女人,也就是上午打来电话的人,闯进了她的生活。她哭着喊着叫唐羽的小名,把她抱在怀里,带她去游乐场公园商店。可是唐羽根本无法接受。
“如果是你,会让一个抛弃了你十几年,对你不闻不问的女人当你妈妈吗?”
我扭过头,无言以对。
当初唐羽知道我的经历时,她很惊讶,她说纪含你不懂幸福。那时候我并不明白她的话,可是当我光鲜的生活与她刻骨的磨难形成鲜明对比的时侯,我终于明白了。
那一晚,她靠在我肩上讲了很多。我心里隐隐地疼。我从来没有,从来没有这些痛苦的记忆。
“纪含,我觉得你真的很幸福,起码你有那么爱你的父母。”
这是那晚她说的最后一句话。
凌晨时,她睡着了,脸颊上还残留着泪痕。我将被子盖在她身上,然后拿起她的手机,拨通了我这几个月来的第一个跨国电话。
如果我算得没错的话,那里应该刚到晚上。
“喂?”
淡淡的一个字,听起来是那样苍老无力。
是妈妈。我的眼睛突然模糊一片,我想叫她,却哽咽着说不出话。
“是含儿吗?是你吗?”她好像感觉到了我。
“是我,妈。”
“真的是你啊含儿。”她一下子哭了,“她爸,快,快,是含儿的电话。”
我听到了急切奔跑的声音。
“含儿,”他接过电话,声音颤抖,“在那边……怎么样?”他小心翼翼地问着,全然没有曾经那高高在上的王者风范。而此刻,我却更像王者。
多可笑。
“还好。”我简短回应。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诉说思念亦或是痛哭一场?
“回来吧,孩子,我和你妈再也不吵了。”
“是啊是啊,回来吧孩子,求你了。”
我的泪水突然决堤而下。
“我对不起你们!”
他们把几十年的爱全部给了我,我却一再任性地逃开。我怎么可以这样自私?怎么可以这样幼稚?
我沿着墙壁缓缓滑坐到地上,泪水流满了脸庞。
“爸,妈,等我,我过几天就回去。”
转身之际,我看见唐羽微微动了一下。
跟唐羽道别的那天,天空飘着小雨。她眼里有不舍,却还是拍着我的肩,说回去以后好好过。
我说:“你不打算找你妈妈去吗?”她只是笑,像我們当初见面一样。
“记得回来看我。”她说。
终于,飞机载着我飞回了故乡。
我回家了。
半年后。
我风尘仆仆地重新回到法国,一下飞机就直奔目的地。
我推门而入,却撞上了一个法国男子。他有着同唐羽一样温暖人心的微笑。
“请问这家店的女主人呢?”我用法语问他。
“你是找唐羽吧?她去找她妈妈了。”
我愣了一下。
那男子看着我,像是想起了什么?“哦对,她好像给你留了一封信。”他跑到柜前,拿出一封信递给我。
米黄色的信封弥漫着淡淡的香气。
纪含,我去找我的妈妈了。
其实之前,我根本没有这个想法,直到那晚听到你给你父母打电话,又想起之前你梦中的哭泣,我突然明白,再风光的人也有他自己的苦衷,再幸福的人也有他自己的喜怒哀乐,我们不能以自己片面的眼光去判断他人,甚至为他人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我的母亲固然抛弃了我,但我们毕竟血脉相连,我相信当年她定有什么难言之隐,我不想再继续恨下去了。
我们都在朝着与正常轨道相反的方向行走,我们都在抗拒生活。我们自以为是地认为我们是正确的,可是兜转一圈,却发现自己费尽力气逆时针一样行走的结果,还是回到了起点。
但至少,一切还来得及。
以后记得常来玩,我和妈妈,在这里等你。
最后,谢谢你。
真正要说谢谢的,应该是我吧。
沉默中,有几滴泪悄然坠落。
(本文获第十三届“新作文杯”放胆作文大赛高中组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