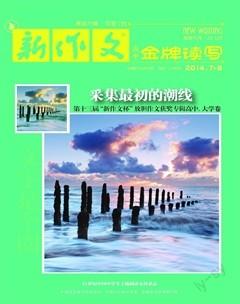尽双欢
苏念菡
评委意见:看到作者说『我是第一次写这个年代的故事』时,我确实感到了惊讶。无论从老练的笔法,还是对时代的稔熟来看,作者都不像第一次涉及这种题材。由此我们也能看出作者在背后下的苦功。如果说文章有什么缺陷,过于巧合让人意料之中无疑削弱了文章的神秘感。
就主题来说,文章并不算是弘扬正能量。这与我们平时所说的『文以载道』似乎并不相符。那么如何在文学与道义之间取得平衡?其实这个问题太大了,一个时代最杰出的作家应有铁肩担道义的觉悟,但作为个人来说,如张爱玲般对人性细致入微的洞察勾勒出时代背后的荒诞,也同样可以获得成功。创作的时候知道方向,心中明晰就好。
(明灯)
一
张爱玲说过一段话: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窗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粘在衣服上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而她说,
她不要做其中的任何之一。
她要的是全部。
二
一九四六年。上海的春天,一如每一个沪上的好季节,温软的风夹带着潮湿的气流,贴着肌肤,升起熏人的暖意来。
弄堂里乱得有些不堪,破碎的白菜叶子和滴落着蛋黄的鸡蛋壳随意丢在巷角。西家的奶妈领着主人家生了红疹哭闹不已的孩子,一边咒骂着一边大大咧咧地走过。而那边,外面正晾晒着女子私物的筒子楼里,响起了日复一日的麻将声。白鸽从弄堂顶的天空飞过,落在了堆积着树叶的檐头。
于子叔穿着西洋款式的白色洋裙,美丽的蕾丝边在裙裾堆折成精巧的模样。那白不是渗人的青白色,也不是太素了的苦白,而是淡淡的,恍若开着香气的丁香花,那一种温温婉婉,是盛在手心里的一抹月白。女子的面容一同这不淡不浓的月白色,清婉而柔美,纤长的眉眼勾勒着沪上的风情和艳丽。这风情也不是咋咋呼呼的风情,而是居家的、日常的,你一转身便能在那巷子口发觉,可一颦一笑又是不能模仿的,裙裾摇曳生姿,更是无法忘怀。
这样的姑娘,拎着光亮的小箱包,站在这样凌乱的弄堂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像是了解了这一份格格不入似的,她并没有等待多久。很快就有一个穿着小旗袍的姑娘从楼里“叮叮咚咚”跑了出来,喘着气凑到于子叔身边,微微愧疚地说:“让你久等了。”
“没关系。”于子叔笑了笑,酒窝像花瓣一样在脸颊盛开着,“我们走吧。”
说罢,很熟稔地挽上了那姑娘的手臂。
两个看上去同样处在妙龄的少女,手牵手亲昵地走远了。
那从弄堂里走出来的姑娘,叫吴小雾,名字有点拗口。比起于子叔,吴小雾就活像个荣国府的粗使丫鬟,她的粗疏,就衬着于子叔的精巧;她的卑陋,衬着于子叔的温美。在旁人眼里,她简直就是笑话一样的角色。
可是吴小雾不在意,简直是一颗心都扑在于子叔身上。两个人关系很好,但又不是特别地好,虽是常常一起走的,但于子叔对旁人都是这样的,不冷不热,可吴小雾却是懵懂的,总想着各种方法投于子叔的好。
那是欢喜的,入了世还难以改变的少女的热情。
她们上了金亚酒楼,大厅里贴满了喜庆的红纸,鞭炮刚在门口放过了,浓重的炮鸣味道依然有些冲鼻。
两个姑娘是挨在一起坐着的。
这是她们在女校的女老师的婚礼宴席,她们是为数不多被宴请的学生。说来毕业也有些年了,女校里的关系也是稀稀疏疏的,所以吃起喜酒来也是敷敷衍衍。
中途没什么话讲,于子叔向来是安静的,她的面庞在阳光照射下恍若是透明的一般,甚至能看见那青色的经脉。她略略用了食,放下了筷子,侧过脸看向窗外,窗口正摆着一小束婚礼玫瑰。
宴席的男主角和女主角走过来祝酒了,平日里不苟言笑的女老师穿着鲜红的旗袍,而她身后的男人却是身形笔挺,黑色的西装下露出立领的白色衬衣,红色的领结无意间被扯得有些歪了,唇线抿得很紧,英挺的鼻梁上架着薄薄的金丝眼镜,遮住了压抑得如星空般动人的眼睛,没有一点婚礼的喜悦。
这男人姓楚,是刚刚留洋回来的金融生,现在在上海开了几家银行。和同是书香门第的女老师,十分般配。
吴小雾见两人端着酒杯朝她们走来,连忙放下了筷子,站了起来,扬起一个笑:“恭喜你们。”
女老师眼睛一弯,目光却留在吴小雾身边的姑娘身上,她正怅然地凝视着窗台上的一束玫瑰花。
吴小雾会意过来,忙扯了扯于子叔的手臂,示意让她回神。
没想心急之下这么一拉扯,一下子弄疼了于子叔,少女下意识地微微蹙了眉頭,轻声嘶痛。她的面庞是极小巧的,像扣在手心里的一枚碧玉,温温凉凉的,并不艳,而画着轻轻的愁。这么不经意的一蹙眉,映雪的眉眼间就添了如纱似月的朦胧,还有落落寡合的清心与隐约的哀伤。
恍若纯白色的月光,落在心上,发凉。
就是这么一眼。
端着酒杯的楚先生,长指紧了一紧。
宴席没有持续太久,宾客们鱼贯走出酒楼的时候,上海的街道上已经燃起了街灯,电车“当当”的声响停顿在了白昼。夜色微寒,春风料峭。
吴小雾用力和送出楼外的新婚夫妇挥手告别,于子叔只是安静地轻笑,点了点头。
二人在送别的目光中没有走太远,只在金亚酒楼的街口,就彼此再见走上了不同方向。
于子叔的白裙子像开了一日的栀子花,到了夜晚,也有些倦了。
肩头突然被轻拍了一下,她惊了一跳,回脸过去,却是方才酒席上的新郎官。
于子叔有些不知所以,但出于礼貌,仍然浮上了微笑:“楚先生,有什么事吗?”
楚先生眼波微动,唇角的笑意俊逸而有礼。“于小姐,我想你会喜欢。”说着,从背后伸出了一束玫瑰。香气还是正好的,花瓣微微卷着,像藏着一夜的好梦,那像是她方才在酒席上愣神看的那一束,可仔细一瞧,露水还是新挂上的,分明是才准备好的。
于子叔仰起脸看他,那人身材高颀,身后的街灯光线微醺,勾勒着他稍显冷漠的眉眼,却十分地合适,让人生出些旖旎的遐想来。
但于子叔只是微微垂下了眼,眼角坠着小巧的泪痣,整张面庞就显得媚了起来。可媚是藏着的、收着的、不被开发的,像潘多拉的盒子,一揭开就是惊喜,可惊喜,是个秘密。
她十分礼貌地后退了一步,没有收下,也没有回绝的意思,只是静静地说:“楚先生是个细心人,夜深了,一定还有人在等你。”
楚先生也是在繁弦急管的上海滩游戏过的人,见过的女子更不在少数,她们要么有着娇媚的容颜,要么是窈窕的身段,说起话来永远都是软糯的上海话,发起嗔是要人命的腻。可于子叔不一样,她本应该平凡得一眼就被埋没在人群中,可那清心玉映的芳华,就是那一朵最平常不过的栀子,远远地路过了,可若有若无的香还盈满了鼻端,握不住,抓不着。她是聪慧的,也是知礼的,无须什么暧昧,纯白干净得像月光。
他主动示好,对方也不是刚出学校的女学生,其中意味彼此都心知肚明。
楚先生这才是真正地笑了,金丝眼镜后的眸子星光熠熠。他收回手中的玫瑰,径直拉过她的手,声音低醇却好听:“于小姐,我们一定会再见的。”薄淡的唇瓣落下一个吻,楚先生优雅而风流,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而后转身离开。
于子叔低垂著螓首,面容隐在黑暗中,可她竟也是笑的。
无声的笑意要融进夜色里。那男子在她手背映下的吻,恍若还留着温热的烟草气息。
她毫不在意地放下了手,拦下一辆黄包车,坐了上去。
夜上海,风花雪月,笙歌未歇。
三
她回来的时候已有些晚了,月影悬挂在三层洋楼的顶上。
房间里没有亮灯,只能说明应该回来的人,比她回来得还要晚。
她简单地梳洗了一番,打开了唱片机,梅兰芳细长而缱绻的嗓音便通过小小的喇叭孔流淌了出来。男旦的温情与哀婉,一点点洇染着这无星的夜色。
她穿着曳地的睡衣,宽松地挂在身上,细细的腰带随意地折在了腰间,刚刚解下发髻的头发尽数垂在了后背上,清芬的水汽缠绕着曼妙的幽香。女子坐在镜前,纤长的指尖抚上了眼端,蹁跹的寂寞便随之跳跃起来。
身后突然传来了脚步声,她知道是谁回来了,却并不回头。
那人打开房门,走到她身侧,弯下身子,从背后环住了她,下巴在她的颈窝摩挲着,像是要汲取温暖。
她从镜子里看着那男人的脸,极其硬朗的面容,立体的五官,眉边有着一道浅浅的伤痕。她轻笑,扬起下巴来,整张面容像猫一样慵懒,美得惊心。
转过身,单手抚上他的胸膛。
男人穿着墨绿色的军装,左胸上的勋章温度冰凉。
“怎么这么晚?”她问,却不像是担心的样子,反而有些勾人的痒。
男人没有解释,低下头,想要亲吻她的眉角,反被她侧脸避开。
“子叔。”他皱着眉唤着她的名字,不满她的回避。
于子叔笑意柔媚而迷离,让人恍惚觉得身在梦中。她慢慢站起身,单手推开他,走到了床边坐下。男人亦步亦趋,居高临下地等待着她。
从枕下取出一盒烟,夹在漂亮的指缝间,伸到他的面前。
男人即刻意会,为她点燃。
摇曳的火苗一瞬间点亮他们彼此的面容,女子笑得更加肆意了。漫不经心的,如同不休的霓虹,融在暗黑的夜幕中,缠绕着暧昧的形状,燃着熏人面的女人香,变成点在心头的一颗朱砂痣。
于子叔轻轻地吐纳着烟圈,缭绕的烟雾间,她眉目如猫,美得张扬。
随意蹬开玉足上的高跟鞋,她蜷着身子向床后退去,松散的睡衣已有些散开,露出凝脂的锁骨,像一环冰凉的镯,藏匿着欲罢不能的毒药。
男人顿时眼色有些变了,声音也粗重了起来,顺着她的动作就要攀上去。
于子叔轻轻扬眉,玉足抵上他的胸膛,抿起了唇角:“不许。”
“子叔!”男人有些不愿了,一把握住她的脚踝。
女子佯怒,眉眼里全然是媚而醇的娇意:“回来晚了,我要罚你。”
说着,迅速弹落手中的烟头,翻身就盖上了薄被。
“今晚你去书房睡。”她说,然后闭上了眼睛。
男人有些不甘心,虽然无奈,但也不得不自认理亏。
这女人,个性倔得很,又如媚如丝。
轻轻叹气,他整了整方才被解开的衣领。走到唱机旁,挪开了唱针,“咿咿呀呀”的梅兰芳的长腔便戛然而止。
转身离开,最后还为她掩上了门。
楼下大厅里,宋嫂还在最后检查着门窗,见男人下楼,连忙低下头问:“老爷有什么事吗?”
那人说:“收拾一下书房,我等下过去。”
“是。”宋嫂回答着。心里清楚,老爷这是又被夫人赶出来了。
老爷姓张名秉安,国统军的少将,年轻有为。夫人呢,则是大户人家的小姐,生来一副倾城貌,又媚得死人。两个人结婚一年多,感情说好不好,说坏不坏。
反正她宋嫂是见过老爷在车上怀抱着不一样的女人,而夫人却好像全不在意,哪怕有一次出门就撞见了,还是不恼不怒地回了个身,就又进了屋。这不像是寻常夫妻的样子。但宋嫂也明白,浮华如梦的上海滩,又有几分真心?尤其是在这风光旖旎的洋房里,阁楼里锁着的究竟是怎样污秽的情事,说也说不完,也说不清。
但她也忍不住想说夫人做得好。
对老爷始终不冷不热,若即若离,哪怕实为夫妻,夫人仍然常常给老爷吃闭门羹。说来也是,男人就是这样,得不到的就永远想要握在手里,如此一来,本是媒妁之言的婚姻,因了这,更加生动起来。
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
偷不着的,就是那心上的朱砂痣,泛着恼人的痒。
四
数天后,苦苦找遍了整个上海,都不见于子叔的楚先生,居然就在电影院门前,看到了穿着米黄色碎花旗袍的于子叔。
她头发随意地侧挽在了脑后,刚刚烫染过的发丝带着细小的波浪,面容上点着一点朱红的妆,整张脸庞一下子就被点亮了。明眸丹唇,美妙得像春天里探出墙头的梨花。
楚先生走上前去,问好:“小于。”去掉了于小姐这样公事公办的称呼,他念起来是理所应当。
于子叔眸中轻愣,听出了是他的声音,转脸,笑得温婉,带一点点的怯:“楚先生。”
就是这一点点的怯,柔美得刚好,总让他忍不住心头一跳。
楚先生开了口:“小于,看电影吗?”
于子叔迟疑着点点头。
楚先生抬眼看了看张贴着的海报,画中的女子不及眼前的一分。他顺势牵过她的手,径直就往电影院里走:“一起吧。”
她微微挣扎了一下,没挣脱,就带着些小小的羞赧和哀怨,随了他去。
楚先生见她不再挣扎,勾起唇角。
电影不是什么新片子,黑白画面上的男女演着上好的情戏。于子叔看得很认真,楚先生看她,也看得很认真。银幕的光亮一点点洒在她的面庞上,姣好如月,安安静静,不动声色,却绵长而婉约,细长得如同流水,更如她今日衣裙上洁白的小碎花,并不唐突,更无突兀,不能再合适。
电影终了,响起片尾曲,是周璇的《四季歌》。
于子叔眼波如春水,微微波澜着。
影院里灯光乍明的瞬间,皓臂一下子被身边的男子抓住。楚先生动作优雅而含着隐隐的霸道,长指扬起她的下颚,径直就吻了上去,攫取她的呼吸,全然把所有的主动权都揽入怀中。
于子叔只感觉男人的唇齿带着淡淡的烟草味,一遍遍洗刷着她的气息。这样暧昧的亲昵,像上海滩上任何一种春风一度一生的游戏。多少人作乐其中,享受,缠绵,片刻温柔,而她,是他以为在他游乐生涯中,最单纯的月光。
她垂着眼睫,任凭影院已亮起的灯影从中穿梭而过,赤色的碟蹁跹而起。
楚先生笑得冰凉而风流,放开她被吻得鲜红的唇瓣,低声说:“很甜。”
不知是胭脂甜,还是说人甜。
于子叔倒是被这一句话讲得真心羞涩起来,安静地垂下脸去,一句话都说不出口,耳朵却红得诱人。
男人见状,又笑,揽住她的肩头。
这一次,她连假意的挣脱,都没有了。
如此反复了好几天,他们见面,约会,电影院,咖啡馆。
楚先生是留过洋的人,说起话来也是有趣得紧,样样都惹得佳人直笑。最后有一次,他们吃完饭,楚先生握住她的手,只是说派人租了一间房,让她搬过去住。
她点了点头。
可是没人忘得了,于子叔与楚先生的第一次相遇,是在楚先生的结婚典礼上。
他们在小巧却装潢精致的公寓间里彻夜缠绵,刻骨的欢乐让彼此贴着心地记忆着。她始终是退却的、羞缅的、展不开眉头的,干净得像一张纸,被他烙上属于他一个人的印迹。
而更多时候,楚先生也是不常来的,他有家庭,有银行的事要忙,时局依然动荡。小小的公寓间里放了一台唱片机,没有人声的时候,就听着梅兰芳“咿咿呀呀”地唱。
楚先生好不容易得了空,白天了回到公寓里去找她,可是奇怪,于子叔也是不在的。问了娘姨才知道,原来于子叔和他一样,也是不常回来的。
这时他还不明白,白月光是温婉的凉,美得人心中泛上孤独。
但这美不是他一个人的,他想要,也留不住。
五
张家的花园洋楼里,始终都是那个样子。
那个张扬的女人喜欢听梅兰芳的曲儿,烫着上海滩上流行的发卷,有时候松松垮垮地盘起来,有时候干脆就垂下来,穿曳地的红睡衣,勾勒着姣好的身形。随意系着的前襟,总是动不动就露出她如玉的锁骨。
她出门后,会一整天都不回来。
张秉安是很忙的,国共内战打得响亮,各大战役悉数登场,他穿着墨绿色的军装,时不时就去了她不知道的地方。不过,不知道,她也不在乎。
日子过的是她的,有时候去楚先生的公寓里听曲,有时候回到家里听曲,在哪里,都是一样的。
今天有些不同了,因为来了客人。
宋嫂去开的门,见到门后的姑娘,神情有点愣。那人只说是于子叔的朋友。宋嫂犹豫了一下,还是让她进来,毕竟她也未听说过,原来夫人是有朋友的。
于子叔从楼下走下来,略略换了一件旗袍,改良过的,腰身很贴,大花朵锦绣团簇的点缀,生生让人觉得堂皇。
看见坐在长沙发上坐立不是的吴小雾,她笑了笑,走到她身前坐下,一边招呼着宋嫂上茶。
吴小雾的目光有些复杂,停在于子叔媚得滴水的面容上。
于子叔却是先开口了,想打趣一般:“你倒是厉害,找到这里来了。”
吴小雾是她同学,她们若是相邀,一定是于子叔去巷弄里找她,吴小雾是完全不了解于子叔的细谨的,甚至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已作他嫁。
她没有笑,她顿了顿,还是说:“你知道吗?楚先生又出国了。”
于子叔摩挲着手中茶杯的手停了停,那是一只花纹高贵复古的欧式茶杯。
“出國?”毫不在意地扬眉,添了些风情的意味,“他忙呀,那是常事。”
“不,”吴小雾难得皱起眉,“楚家一家都迁走了,金价大涨股价又狂跌,国内金融市场太不景气了。楚先生的银行倒闭了好几家。”
听着从吴小雾口中蹦出一个个在于子叔耳里有些陌生的词汇,她突然觉得眼前的吴小雾有些变了。
“楚先生本来是想告诉你一声的,但是找不到你,才找到我的。也是他托我告知你的。”吴小雾的神情有些冷漠,就像公事公办那样冷漠。
“哦?”于子叔双眸微眯,有一些丝丝缕缕的情绪就流淌了出来,褐色的泪痣在眼底熠熠生辉着,不再像在楚先生面前那般收着、藏着,她尽数的媚娇和隐约的悲戚,都在那一颦一眼中流露着,“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问的。”吴小雾只是简单说了这两个字。这年头,上海滩的谣言传得比风还快,张秉安这样的人物,家里有什么事儿不是一清二楚?不过是一个不知姓名的神秘的张夫人,从附近人家的娘姨奶妈口里,挑三拣四地问问,也就出来了。
她停了停,看着于子叔的面容,目光有些奇怪。
“应当让楚先生看一看你现在的样子。”她平静地说,也没有什么讥讽的意思。
但是都明白,若不是讥讽,吴小雾全不会这般。
什么月光,什么纯白,那都是这个女人做给他看的好戏啊!
吴小雾觉得自己心底简直都要尖叫了。
于子叔没有理会她,只是垂下了眼睫,没有什么别的神情。
这时,门外又传来了急慌慌的敲门声。
这次是于子叔开的门。
门后却是穿着墨绿色军装的军人,军帽下的面容有些生。见了她,正礼而言:“张夫人!”
于子叔蹙了蹙眉:“什么事?”
那人就把一封信交到她的手里,随即很快离开。
她有些狐疑地坐回了沙发上,当即就撕开了信封口,抖落出薄薄的一张纸来。
展开,白纸黑字,末端盖上了鲜红的官方的印章。
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了一遍,然后又是一遍。
最后把那张纸,放回了桌面上。中指有些颤抖,手腕也有些不稳,想要重新端起桌上的茶杯。一个手软,茶杯就碎在了地上。
温热的红茶,洒了一地。
这杯子,是张秉安从欧洲带回来的。红茶叶子,是军队里有人送给他的。
于子叔愣了愣,下意识就要弯下身子去捡拾碎片。
吴小雾有些看不下去了,连忙拉住了她的手臂:“你怎么了?”
她只能感觉到于子叔浑身都在微微地颤抖。
于子叔仰起脸看她,褐色的泪痣在光影的缭绕中,生成了朱砂。
却是骇了吴小雾一跳。
于子叔哭了。
她的哭是很安静的,不是那种走到绝望的痛彻心扉的哭,也不是声嘶力竭的哀嚎。她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只有晶莹的泪水从眼角悄然滑落,顺着她弧度优美的下颌,垂在衣衫上。
吴小雾愣了,又问了一遍:“你怎么了?”
“他们说,张秉安死了。”
国民军的张少将,死在了内战的战场上。
她的声音里没有一点哭腔,还是那软糯的上海话,能念出点风情。
可这风情,也是哀怨的风情,艳丽不起来的。
吴小雾甚至觉得,于子叔不是在为张秉安难过,而是在为她自己。
她默默地叹了一口气:“你何必如此。”
自己分明是正房,反過来要去做别人的情人,一场游戏,如梦一般。
于子叔顺着柔软的皮沙发,身子慢慢地下滑,一直到坐在地上,抱住了膝头。她没有看吴小雾。
“张爱玲说过一段话。”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窗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粘在衣服上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我不要做其中之一。”
不论是白月光,还是朱砂痣。
她要的是全部。
不被遗忘的,不被丢弃的,不被日常的琐碎而埋没的。她可以是楚姓男人的月光,也可以是张秉安的砂痣,她在彼此的角色转换中尽享着双重欢愉。但她永不是蚊子血,不是饭粒子,她不想。
爱是不能老去和枯萎的,就算死,也要紧紧地攥在手心里。
吴小雾站了起来,她的神情恢复了初来时的冷漠。
“可现在,你什么都不是。”
她说完,然后离开。
空空荡荡的洋楼里,二楼房间里的唱片声传了下来。
梅兰芳在戏里低声地抽泣起来。
(本文获第十三届“新作文杯”放胆作文大赛高中组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