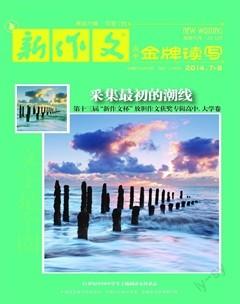来不及铭刻的盛宴
刘雅玄
评委意见:青春期的伤疤和疼痛,宛如小树枝头开花之际,花朵钻出来时树木的疤痕和阵痛,这也是人生必经的一种转变。人和树木一样,在淋过青春时的小雨之后,才能慢慢地进入人生丰盛的年华,才能逐渐花绽果熟。这篇小说给人一种青春期的深深疼痛感,就像你我年轻时一样的感觉,消极颓唐,对任何事都提不起精神,感觉一切都是在演戏。这种青春期的苍凉感,有其独特一面,但也有其脆弱的一面。还好,我们都会越来越强韧,越过那些疼痛,越来越懂得珍惜人生中的美好。
(浩风)
1.铁轨
铁轨,浮漾着湿湿的流光。我默默地望着那延伸至地平线的轨道,什么也不想。银白色的火车开动了,响亮的鸣笛声,拉动了黄昏的盛宴。雨点轻轻落在唇边,是冷的,但没有泪水的咸。
然后爸爸就消失在我的视线里。格尔木,这个承载着冰原梦想的名字,把爸爸的时光藏匿在那里。我望着天上那被夜雾遮住的月牙,就会想,此刻的爸爸是不是也仰头,念着小女我的乳名,轻轻道声晚安?
夏天的时候,聒噪的蝉鸣让夜晚很充实,小小的我坐在窗台上,不吵也不闹。我不喜欢明灭的星,因为它们太迷离,就像爸爸,总是捉不到踪迹。子夜,整座城笼罩在安静里,我的头埋在双膝里,短短地梦一个与爸爸相会的夜晚。
梦里,有凉亭,有蒲扇,有梦幻的萤火虫,有倾斜的月光,还有爸爸那不软也不硬的胡须。梦里的我企求梦的长久,抑或是贪恋简单的幸福。
你第一次去格尔木的时候,我不相信。
“宝贝,爸爸很快就回来。”
“哦。”
“很快哦。”你的眉目里有星的光芒。
“哦……”
我怔怔地望着你,只会“嗯、啊、哦”地应答。可是当你在我眼中只剩下背影的时候,我才突然发现你真的走了。银色的车厢隐没了你的身影,我像个发疯的小兽一样冲上火车。列车员轻而易举地擒住我,我“哇哇”大哭引来了你。你蹲下身子对我说:“宝贝乖。”“爸爸别走别走。”我含糊地哭着说。我忘了最后为什么是我一个人蹲在安全线以外,银色的火车早已开往地平线。
火车拉走了那么多旅客,却载不动我对你的留恋。
我哭得像个花猫,或者一个受伤的布娃娃,跌坐在阴影里,忘了怎么去说话,怎么去表达。
从此我就从一个疯丫头变成了一个似乎腼腆其实落寞的孩子。
我收起了所有华丽丽的连衣裙,穿起一件件朴素的格子衬衫,在一群幼儿园小朋友中间礼貌却格格不入地笑着。黄昏的余晖给世界镀上一层金碧辉煌,火云像血一样,只是,时光的雨已经冲淡了当时的伤痕。
爸爸归来的时间很少。我常常看着爸爸在格尔木的照片发呆。蓝得不真实的天空,蓝得不像话的湖水,爸爸穿了一件浅蓝色的衬衫,笑得很爽朗。与那个苍茫浩渺的高原相比,我觉得我生存的空间很狭窄,窄得盛不下我对你的思念。
那次你坐车路过家乡,顺便来看我。临走时,我望着你微蓝的眼瞳,很平静地说:“爸爸,你回家待了整整四小时。”
你随之一愣,然后是一行泪,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你流泪。
第二天,妈妈告诉我,你辞职了。
青春让我褪去了娇嗔的语气。我渐渐在你说完“路上小心”后不再粲然一笑。我不再是那个你俯身才可以吻到额头的小女孩。我把梦想折成纸鸢,而比我高一点点的你为我助风飞翔。
可你很忙。
疲惫地备考。归家,温馨的灯映出一片晕黄。你很随意地坐在沙发上,笔记本电脑放在膝上。“啪啪”的键盘敲击声让慵懒的家庭多了一份工作气息,我有种置于你的写字楼的错觉。
“爸,陪我玩玩好么?”我的声音很小。
键盘依旧“啪啪”地响。我的目光由期冀,转为犹豫,直到冰凉。
良久,你重重地敲击了一下回车键,抬起头,问我:“你说什么?”
我落寞地笑了。雾气涌上眼眸,我努力克制住嗓音的颤抖,说:“没……什么。”
你只盯我几眼,便把视线挪开了。
我第一次觉得我们两人之间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我静静回到卧室,像个落魄的布偶一般盘膝坐在墙角,让泪无声滴落。夜已深,我什么都没有说,在你的追问下走出家门。
铁轨。
尘埃安静地在空气里蹁跹,舞一场圆舞曲,然后谢幕。枕木道出绵长的岁月,而它早已麻木。金属泛着银色的冷光,晃了眼。时光的气息在这里落定,蝉鸣诉说着昔日的传奇。
终究是什么,隔开了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2.冰花
雪落下。
落在腐朽的老船上。落在红色敞篷车里。落在北斗星上。落在十二点的钟声里。
雾气氤氲在车窗玻璃上。
“嘿,你,在,思,念,我,么。”
我写给咫尺之遥的阿梨。
“才,没,有。我,在,爱,着,远,方,那,只,烤,鸭。”
她认真地用手指在车窗上写道。
我扭头瞪了一眼,被赠给一个白眼。
公交车颠簸在雪路上。洁白的雪铺成了整个空城的梦境,却有一点静静的寂寞。我壞笑着撩了撩她的头帘,她第N次吼我,我第N次假装生气地别过脸去。
我总喜欢笑你和可爱的小狐狸阿狸同名,眼神同样狡黠,发呆的神情都那么相似。你总是气鼓鼓地瞪着我,说你是堂堂美少女。于是,我理所当然地回一句:
“生气的时候更像小狐狸。”
你气得直跺脚。
城。银装。
我们两个人穿着松糕鞋,凭空拔高了二十厘米。很不想提起的就是摔了不少跤。
我们手挽手走过一条条街、一个个商铺,看到喜欢的东西就会一起手舞足蹈,毫不犹豫地拍单,结果钱包一点点瘪下去。
雪很厚,纷扬飘落,我以为友谊也是这样积淀得越来越深,却忘了有一天所有梦幻的积雪会在刺目的阳光中消亡。
毕业后,友谊就像断线的风筝。
我疯了一样给她打电话。我不知道我曾经做错什么,只是从其他朋友那里听出我好像伤害了她。彩铃是散发着淡淡忧伤的歌曲,绵长、微冷。曲终,机械的女声告知我“电话无人接听”,于是残忍挂断。那悲怆的彩铃一次次响起,又一次次落幕,如同凄美的童话里,在子夜时分,南瓜车倾翻,水晶鞋遗落,星星藏起了光辉,夜闪着冷寂而忧伤的微光。
我把期冀织成一段段破碎的话语,浅浅地印在日记本里,或者发给你。日记无言,你也是。
记忆冲撞着我的理智。
再也没有你的回眸一笑,阳光落在你的额上恍若晶莹的梦境。
再也没有你陪我在草丛中并肩躺下,将黄昏看成深夜。
再也没有你抱着我的肩对我说:“哭一哭吧,我陪你。”
再也没有你。
再也。没有你。
喑哑的歌声飘忽而过。那是情感的绝唱么?
厮守长夜。我第一次意识到,阿“梨”的同音字还有“离”。
我喝了整整一大瓶可乐然后胃痛了整晚,我第一次看到夜是怎样一点点漆黑得吓人,然后怎样一点点泛出微光却迟迟等不到曙光迎不来黎明。当我昏昏沉沉睡去醒来已日上三竿,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拿起手机却没看到你的短信。
我长叹了一口气,合上眼眸。
眼前是火热的血红色,阳光透过树叶投下斑驳的影。那棵苍老的杨树换上夏装,抖擞了许多,我竟毫无来由地想到了回光返照,而后自嘲地一笑。树叶有的枯萎有的新生,墨绿、浅绿、淡绿、浓绿夹杂在一起,就像杂陈的心情。
我只有叹气。
原来,有你的爱可以让冬天不太冷,而没有你的夏天却这样凉。
3.孤灯
宴席。
觥筹交错,光影交叠。我礼貌地笑着举杯,再无声无息地放下笑容。
我觉得很假。
伪装的人,就像人格分裂。明明上一秒还在笑着调侃,而此刻却已说着客套的话举起葡萄酒杯。
杯中泛出深紫色的光,像一个近乎窒息的梦。
杯酒下肚,心跳就没来由地加速。像是无数交错的线条,横冲直撞。酒可以麻醉,但不可能治愈。也许醉后可以躲避记忆,但内心那无法治愈的伤口就那样乌溜溜地淌着血,很怪异、很茫然。
餐后,爸数落我,说我不懂得乖巧地敬酒,不懂得说一些冠冕堂皇却耐听的话。我木然地听着,垂着头,走神。曾经的我还会反驳,但多次重复后有两种可能,要么心悦诚服,要么彻底麻木。我属后者。
餐布有金色的装饰,富丽堂皇却很冰冷。透明的转盘托着鸡鸭鱼肉,却不如一盘亲切的青菜让人舒适。我只关照素菜,却有人问起我为什么不吃肉,我愣了一下,说“都吃啊”,不情愿地夹了很多油腻的肉。肥肉的质感让我想吐,但还要强忍。
饭局总是很吵,这时候我觉得我是家长的附属品,被赋予未来的傀儡。孩子是大人的话题。有时问起,我礼貌地笑笑,虽然我知道饭后会被质问为什么話这么少。
“不想说。”这是我的回答。
一顿骂。
最喧嚣的外界,往往衬出最空虚的内心。
匆匆行于城市的轨迹上,千篇一律,却逃脱不掉。前方是领路的灵魂,身后是推挤的人群,这条拥挤的城市河流不允许停留或登岸。行尸走肉,汇成了这座古城。我以为挣脱便是释放,却发现时代的笼没有解锁,岁月的毒没有解药。
于是,默默行走。
哪怕百般不愿。
哪怕精疲力竭。
我们学会微笑着武装,学会披上盔甲却口口声称袒露着纯洁的心。
我忍不住想起乡下那宁静的夜空,营造一个海洋般的梦境。萤火星星点点,穿梭在你我的鼻息间。花草树木皆已安眠,夜空隐约呈现着星座的笔画。
我忍不住想,有哪些远方的心正在酷寒之地等待极光,为了那一刹那的窒息久久坚持?
我忍不住想:在浩瀚的大草原上,有哪些马在驰骋,哪些草在织梦?
……
4.旧城
人不在了,旧城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
奶奶的姐姐去世了——家里称之为大奶奶。那夜我正酣睡,电话铃刺破了宁静。我听见妈妈急急地跑去接电话,却在一声“喂”后没了声响。
我从没见过妈妈这般失神。
夜车。星星眨着诡异的眼睛,月亮隐匿。偶尔遇上对面的车,刺目的车头灯晃得眼痛,随后重归黑漆。有的大厦亮着一两点光明,有的霓虹还不知疲倦地变幻七彩。夜里,有的安眠如大海,有的清醒如白昼。
走上颠簸的土路。我渐渐睡着了,忘了那个阴森的午夜,悲痛的无言的午夜。
当我们终于抵达老家时,彻夜的灯火,号啕的哭声。
我愣住了,我不敢走近,那不是我认识的家。
那不是我该去的地方。
陌生人穿梭,我怔怔地,缓缓地走入那个熟悉却陌生的房间。白色的布单浅浅勾勒着人形,我不敢相信那苍白的布罩着我爱的亲人。
我跪下了。
周围哭声阵阵,而我什么都听不到。如同一部哑声电影,周围的一切都在快进,而我是时光遗忘的棋子。我茫然失措地目睹一切的一切都卷入岁月的旋涡里,或者向着未来的方向奔流,或者逆流成暗淡的河流。
只有我,只有我原地不动。
我伸出手,想要抓住空气中的什么。可是,什么都没有。
一行清冷的泪滑过面颊。我舔了舔,竟没有味道。
下雨了吧?
呵,可是我是在房间里面呢……
我跪了很久。好像有人拉过我。我的膝上落了几行干涸的泪痕,新的泪水叠加在上面,湿润的凉。
恍然间,我看到大奶奶出现在我的面前。
她笑盈盈地看着我,怀揣一本《安徒生童话》,手中端着一碗甜甜的米粥。她笑着笑着,面容就变得透明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那是元旦的前一天。
当凌晨有鞭炮响起的时候,我虚弱地倒在墙上,望着夜空中绚烂的花火,什么都不想说,只是觉得彻骨地寒。墙上的白屑擦了一身,像是怪异的孝服。
仰首,看见那张熟悉的面容。只不过,是在黑色的相框里,而且,笑靥也是黑白的。
后来,屋里屋外少了一个忙碌的身影。印象里大奶奶总是笑的,经历过几十年的沧桑却依然纯朴地笑着,甚至带些天真。
那时,我恨透了命运。
每逢极寒的冬日,枯禿的杨树枝直指苍穹。树影纵横,写满相思。望着那不圆的月,我总会想起逝去的人。
和不曾失去的爱。
后来,我在书上看到一句话:
感谢那些爱我们的人和我们爱的人,因为他们让我们的人生不再寂寞。
我悄悄地对命运说了句抱歉。
但是,每当花火妖娆,我的眼底总是有层极深的伤。
5.隧道
毕业了么?
典礼上,无数红色的毕业证书抛向空中。耳畔回荡着骊歌。每个人都虔诚地仰头,望着天,抑或未来。
画面凝固。雾气氤氲了我们的双眼。
遥远的钟声,恍若在悠悠鸣响。
夏日终年。
三年弹指间。
最后一次踏出中学校门时,我轻轻地道了声“再见”。
可我一次次回首,我要记住每个人的笑容,记住每一隅尘埃的名字,每一首我们一起唱过的歌,每一场我们一起狂奔的雨。
手已不是三年前的婴儿肥,女生多了纤细,男生多了骨感。手掌相叠,那沉沉的力量代替了无数加油的言辞。
阴雨绵绵中,中考结束了。
斜雨密织的初夏,透明的雨伞,迷失的轨迹,即将奔赴光明的隧道尽头。
我一次次问自己:离开了么?
真的离开了么?
樱花在空中舞一曲霓裳羽衣,恍若放慢节拍的飘零,终于化作清香的泥土,埋藏樱花的记忆。
校园里,树与花,绿得欲滴,红得张扬。
我如同捡拾落叶的女子,静默地在走廊、在树丛里穿行。音乐教室的窗飘出轻灵的钢琴伴奏和唱诗般的合唱,悠长的曲调,歌词很少。我默默地立在窗前。室内背光,隐约看见起伏的黑白琴键和诚然的面孔。那是一首忧伤的歌曲,是凋零的碎片,映着冰蓝色的梦境,绵延一世的留恋。
我的中学。爱的音符洒在每一个角落,默默生根、繁茂。而今,对母校的留恋像藤蔓一般缠住我的喉咙。
我抱着好友哭了。
有句话说母校就是你骂了千百次却不许别人骂的地方。这话真好。
我回首望着那金碧辉煌的校名。穿透尘埃,阳光的碎屑落在我们上课疯狂的地方。教室已然空了。墙上精心设置的班级板块被粗野地撕扯下来。油漆笔在课桌上写下一个个“我爱你”“我会永远记得你”。墙壁重新刷上了漆。全班集资买的空调的遥控器已不归我们保管。哄堂大笑的声音已落入了岁月底层。鲜活的面孔、整齐的座位都不在曾经的轨道里了。
我透过门上小小的窗子看过去,陌生的姿态,甚至尘埃都不是我记忆里的那一丛。
粉红色的黄昏,不真实的收尾。
那些来不及续写的感情,就这样分道扬镳。
我立在黄昏的尽头,任风穿堂。
发丝凌乱,弄乱了昔日的面容。
粉红。金黄。火红。黛青。暗蓝。
星辰落入初夜,那一闪即逝的绚烂,仿佛在述说着来不及道出的似水流年。
(本文获第十三届“新作文杯”放胆作文大赛高中组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