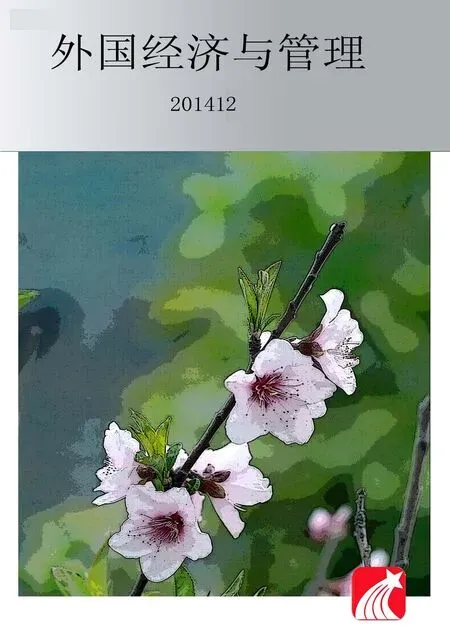网络权力理论研究前沿综述及展望
孙国强,张宝建,徐俪凤
(山西财经大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山西 太原 030031)
一、引 言
网络权力是指在网络交换和协调过程中不同网络节点的控制和影响能力。网络权力作为影响网络组织运行绩效和治理效果的重要因素,以及解释和预测合作节点的经济和社会行为的重要依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但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并逐渐演化为一个热点问题。已有的研究认为,区别于层级组织中的权威,信任是网络组织的典型特征。但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在网络组织中权力权威并未淡化或消除,在一定程度上仍发挥着独特的功能,因此网络组织中的权力非对称性问题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经济实践中,网络节点的行为受到其权力的直接影响,网络节点的竞争力和市场地位直接影响其在整个网络中的作用和地位。从理论上讲,正是由于网络中各节点的经济权力不对等或者在网络中地位有差别,因而引导和影响着它们的经济和社会行为,进而影响网络组织的运行绩效和治理效果。那么,权力在网络组织中是怎样配置的?其决定因素是什么?配置效率如何?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会为网络组织治理提供有力的参考依据。通过研究网络权力的来源、属性及其度量,可以探讨权力对网络组织运行绩效和治理效果的影响,解释和预测网络节点的行为以及网络的转型升级。因此,网络权力研究是网络治理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鉴于学者们对企业网络权力的研究肇始于社会网络权力,本文沿着由理论到实践、由表及里的研究思路,对网络权力研究前沿进行综述与展望。第二部分追溯了网络权力研究的理论渊源,第三部分总结了网络权力配置的度量模型,第四部分从4个不同角度梳理决定网络权力的基本观点,第五部分将网络权力拓展到企业网络的应用范畴,第六部分分析了网络权力配置对企业合作行为的多层面影响,最后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为后续深入研究提供方向性导引。
二、网络权力的理论渊源: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研究可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社会学家,他们以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为基础,用网络结构来描述和分析社会结构,探讨和总结一定社会群体中的人类的行为及其规律。权力是一个人类生活中经常使用的概念,凡是有序的组织活动都有权力的作用。“权力”一词最早由Emerson(1972)提出,主要应用于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从渊源来看,网络权力最早起源于社会学领域的人际网络研究,即内嵌于社会网络中的个体拥有影响他人的权力。综观社会网络权力文献,有3种观点得到了比较普遍的认同,即关系观、能力观和依赖观。
1.关系观。关系观认为,权力是一种社会关系。例如,Foucault(2000)将权力视为“关系”、“网络”或“场”,认为权力并不是一种从上到下的单向性的控制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交错的复杂网络。在此网络中,有的人被权力所控制,有的人用权力去控制别人,而每个人又都充当着实施权力和受权力支配的双重角色。从本质上讲,这种权力来源于个体在社会网络中所处的位置。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权力是社会位置及其占据者的一种结构属性;或者像Martin(2000)所指出的,权力是某种关系的属性,而不是处于这种关系中的个人的属性。社会嵌入理论的典型分析框架是Granovetter(1985)提出的“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两个维度。关系嵌入的研究集中于网络行动者之间直接联系的二元关系,侧重于分析二元关系的强弱程度。结构嵌入的研究集中于网络行动者之间联系的多层次结构问题,它一方面强调网络的整体功能与结构,另一方面关注行动者在网络中的结构位置。
2.能力观。该观点认为权力是社会中某些人对其他人产生预期或预见效果的能力,或者能够聚合行为者以及联结知识与生产的能力(Bridge,1997)。但学者们的观点不尽一致。Weber(1906)将权力定义为“在社会交往中一个行为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其他行为者之上的能力”。Parsons(1988)在对Weber的定义进行拓展后指出,权力不仅是权力主体的属性,还是一个关系系统中主体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属性。他认为权力是系统中的一个单位在其他单位的对立面实现其目的的能力。Blau(1964)提出,不对等性交换产生社会的权力差异和社会分层现象。他对权力的理解与Weber基本一致,认为权力是“个人或群体通过威慑力量、不顾反对而把其意志强加到他人的能力”。Krackhardt(1990)从更普遍的意义上对权力进行定义,认为权力是消除一切障碍而完成自己想做的事的能力。Markovsky(1992)发展出更为正式的网络交换理论,认为权力代表来自网络中某一位置排除其他位置的能力。与这几种观点不同,英国著名社会学家Giddens(1998)认为,权力就是行动者能够对一系列事件进行干预以改变事态进程的能力,这其实是将权力视为一种协调和指挥能力,强调的是对工作任务的协调。
3.依赖观。它认为,权力关系产生于相互依赖之中。社会中的行动者为了生存,需要将资源作为生存的手段和基础,但是由于地理位置不同、自然资源分布不均、行动者对社会资源的占有不平等,导致依赖程度高的行动者为了得到自身所需的资源而服从于依赖程度低的行动者。一个组织对另一个组织的依赖程度与其对后者提供的资源或服务的需要呈正比,而与可替代的其他组织提供相同的资源或服务的能力呈反比(Hoskisson等,1994)。一个行动者或组织机构利用某种方式控制了另一个行动者或组织机构所需要的资源,就有可能获取对另一个行动者或组织机构的权力。不同组织所拥有的资源呈现异质性特征(Penrose,1959; Barney,1991),必然会造成组织间因资源禀赋不同而相互依赖,那些拥有对方关键资源的组织显然具有较高的权力。越是对方急需而又难以替代的资源,越是能够形成对对方较大的权力。换言之,权力就是资源匮乏者对资源富有者的依赖。资源依赖是理论界的主流阐释。然而除资源依赖之外,心理依赖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权力是社会中的个体或组织影响另一个体或组织的能力,它既指施动者对受动者进行命令和控制等实际行为,也指受动者对施动者的认可、敬慕和遵从等心理行为(Emerson,1972),这种认可与遵从就产生了受动者对施动者的心理依赖。
三、网络权力的度量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将个体和组织及其间的社会关系看成是一种可视化的网络,通过图论、数学模型及软件分析等方法对网络的关系数据进行分析,进而揭示网络结构的特性。从社会网络角度对权力的界定进一步体现在网络研究者对权力的各种定量表述上。换言之,网络分析者是从“关系”的角度出发定量地界定权力,并给出多种关于社会权力的具体的指标化定义,包括各种中心度(centrality)和中心势(centralization)指标。中心度是针对网络中节点而言的,中心势针对的则是网络图,即整体整合度或一致性。这是网络分析者在方法上的独特贡献。Bavelas对中心度进行了开创性研究,验证了“行动者越处于网络中心位置其影响力越大”的理论假设。中心度反映了网络节点在网络组织中的重要程度(Denooy,2005 ),描述了整个网络围绕一个中心的程度。中心度越高,说明企业越接近于网络的核心位置,企业在网络中的地位越重要。具体体现在度数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几个方面(Brass和Burkhardt,1993)。居于高度数、高接近性和高中间性的中心企业,由于与其他节点之间存在更多的联系,访问其他节点的路径相对较短,能够快速地到达其他节点来获取知识和接收信息,从而表现出显著的结构优势。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中心度指标是特征向量中心度(eigenvector centrality),它是测度一个网络节点在多大程度上位于网络的核心位置,并考虑到与特定节点相连结的其他节点的中心性进而度量一个节点的中心性。这些指标的开发为量化识别网络权力及其配置提供了便利。
根据刘军(2004)的整理,中心度与中心势的计量模型如表1所示。

表1网络中心度与中心势计量模型
特征向量中心度的计量模型为:λmax=max{λ1,λ2,λ3,…,λn}。其中,λ是η·ω=ω·λ的特征值,η是网络节点之间的关系矩阵,ω是一个n×n矩阵,其各列是矩阵η的n个特征向量。*Bonacich认为,矩阵的最大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能得到一个好的网络中心度。
在变量度量中,概念化是操作化的前提与基础。Jones和Search(2009)提出了一个通过不同接近性来理解权力空间性(spatiality)的方法,主张采用包括物理的、文化的、虚拟的、组织的等多维角度来概念化接近性,而不同方式的接近性均可塑造网络权力。网络权力大小也可以用权力指数(power index)和权力序阶(power order)表示,前者可用基数表示,求某节点与其他节点关联数目的总和并用所有节点的中心度进行加权(Bonacich,1987)*Bonacich注意到,如果一个节点与高中心度的节点相连,该节点的中心度也会提高,并提高与自己相连的其他节点的中心度。;后者用序阶表示,如第一、第二,代表权力水平的大小排序。衡量权力大小既要比较拥有资源的数量,还要比较拥有资源的质量。一般来说,可以通过资源的稀缺程度、重要性和可替代性等进行衡量,资源越稀缺、资源越重要、资源越不可替代,资源拥有者的权力就越大。
根据(Bonacich,1987)的研究,网络权力指数的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rij是连接点i和点j之间关系的赋值(测地线距离或点度数);cj是点j的中心度,即点i的中心度等于它与其他点的关系数目的总和,且用所有其他点的中心度进行加权;α、β是两个修正参数,α是一个标准化的常数,是一个附加的参数,它不影响相对中心度,若β=0,α=1,则i点的权力指数就为i点的度数;β是一个衰减因素,β值的大小体现了某节点的权力对其他节点的权力的依赖程度。
尽管Bonacich所开发的权力指数模型具有开创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网络权力的量化研究,但系统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尚未建立,评价方法也仅限于社会网络分析工具的借用,网络权力配置效率评价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仍留有较大的探索空间。
四、决定网络权力的基本判断
网络权力究竟由什么决定的?这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展开研究,形成了结构决定论、知识决定论、能力决定论、策略决定论等截然不同的观点。
1.结构决定论。结构决定论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它认为网络结构或节点在网络中的位置决定合作企业的权力大小,以至于地位权力(position power)成为权力的代名词。这与社会网络权力研究中的关系观如出一辙。在网络组织中,一个处于网络中心地位的节点被认为可以享有更多更有效的资产流、信息流和权力流,而这些都将成为竞争优势的资源来源。占据良好网络位置的节点在收集与处理信息方面将更具优势(Bell,2005),网络中心位置不仅可以带来“接近”价值信息的优势,还可以为组织带来基于从属关系的优势(Podoly,2001),从而成为网络权力的“集中营”。从属性角度分析,权力不仅是权力主体的属性,而且是一个关系系统中不同主体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属性(Parsons,1988)。权力来源于个体在社会网络中所处的位置,权力是一种社会位置及其占据者的结构属性,各网络节点凭借其在网络组织中所处的位置而获得大小不等的权力。位置决定了参与者在网络中的权力(Brass和Burkhardt,1993;Wasserman和Galaskiewicz,1994),这种因位置而产生的权力源于成员间相互作用的结构特征而不是“占有者的知识”(Yamagishi等,1988)。因此,从网络结构的角度分析,权力应该是网络中不同位置的属性(Emerson,1972),角色与地位决定权力的特性(Kahkonen,2014)。对权力的更有意义的讨论应该站在网络位置而非参与主体的角度(Parsons,1988)。因此,网络位置的主要变量是中心度与结构洞(Powell等,1996),网络权力是网络节点间位置关系的函数。
2.知识决定论。决策权是网络合作中节点拥有的关键权力之一,诸节点合作中谁拥有最终决策权?由谁行使决策权最有效率?最早对社会中各种知识予以关注的是Hayek,他在1945年发表的经典论文《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中提出决策权必须与知识分布相匹配,即决策权应赋予拥有知识的人。Hayek也区分了科学知识与“特定时间与地点环境下的知识”,前者是通用知识,后者是专用知识,两类知识的分布会对决策权的安排产生影响。Jensen和Meckling(1976)继续了Hayek的研究,他们提出了两种决策权配置的路径:一种是将知识传递给拥有决策权的人,另一种是把决策权配置给拥有知识的人。虽然他们并未否定第一种方式的可能性,但认为“如果转移知识的成本高于转移决策权的成本,那么,知识的拥有者将……倾向于购买它们”。由此,通过决策权的买卖将决策权配置给拥有知识的人,可以提高决策的效率与科学性。有效的分权是为了实现最理想的合作,网络组织中的分散决策协调是对以往决策模式的超越,使专业化分工所导致知识的分裂(division of knowledge)以及相应的分散决策重新在整体网络的框架内整合到一起,它是分散与集中的辨证统一,由此网络可能成为解决集中化—分散化困境(centralization-decentralization dilemma)的一种方法(Limerick,1992)。
3.能力决定论。该理论认为,权力是一种被意识化了的能力,存在于权力对象的感知中,以致会出现权力与权力运用的背离。网络节点能力是改善其网络位置和处理网络关系的能力(Hakansson,1995),是网络节点通过识别网络价值与机会、塑造网络结构、开发维护与利用网络关系以获取稀缺资源和引导网络变化的动态能力(Bullinger,2004)。因此,网络能力对网络节点的网络嵌入关系有深刻的影响,进而决定网络节点所拥有的权力。随着行动者在社会群体中阅历的增加,他辨别社会群体和社会关系的能力也在不断进化(Freeman等,1988),行动者对社会结构精准认知的能力关系到他是社群的核心成员还是暂时的边界成员(Freeman等,1987),网络节点对网络的精准认知会促进其朝着有利于自身的网络位置迈进,权力不仅属于那些占据中心位置的行动者,而且属于那些对他们所在的网络有精准认知的行动者(Krackhardt,1990)。
4.策略决定论。在20世纪70年代,以Crozier等为代表的法国组织社会学开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组织理论的决策分析范式。在他们看来,组织与制度变迁在本质上是一种微观政治过程。在此过程中,行动领域的复杂权力关系与权力游戏构成其深层次的影响机制与动力来源。组织内的行动者从来都不可能完全受制于某种外在结构;相反,为了解决组织中的某一问题,不同组织基于各自掌握的或多或少的不确定性领域,在对环境与他方的可能决策进行权衡判断的基础上构建起某种权力游戏。在这种权力游戏中,每个行动者都试图影响和控制组织与制度变迁的规则与方向,并从中实现各自的目标(Crozier,2007)。受Parsons等关于社会行动、社会系统,以及Baranard、Simon等关于组织中成员及其决策行为等观点的影响,以Crozier等为代表的法国社会学决策分析学派的推论方式包括这些逻辑上紧密联系的推论要素:参与到特定权力游戏中的行动者都具有有限理性,都具有其相对模糊和不明言的行动目标(经常是差异性目标),行动者总是在判断特定游戏环境的条件下,对其自身行动能力与关键资源,以及其他行动者的行动能力与可能的行动策略做出权衡与判断,进而采取策略性行动,使得权力关系的重构、权力游戏的运行能够尽可能地有利于自身目标的实现(Crozier,2007)。
五、网络权力观的应用:企业网络
企业网络权力由社会网络权力演化而来,学术界对企业网络权力的研究始于对企业网络非均衡性特征的关注。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借鉴网络分析方法并将其应用于经济领域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企业网络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网络理论不仅被经济学家运用于企业家行为和中小企业的研究,而且渗透到市场理论和组织理论研究领域。新政治经济学派主张,企业是由行为者治理的网络关系的集合。他们重视企业之间不对称的权力关系,提出从权力关系的视角讨论生产网络,认为企业间关系的本质是权力依赖。
企业网络权力是一个相对复杂的概念,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行为者不是一般的社会单元,而是以企业为主,权力是企业在开展经济实践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权力跨越企业边界演变成网络权力;二是网络权力只有相对于其他行为者才能存在,离开合作对方权力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三是企业网络权力需要从多维的视角去认识,例如,Brown等(1995)以及Maloni和Benton(2000)把企业网路权力划分为报酬权、强迫权、专家权、指导权、合法权等,张巍和党兴华(2011)根据不同配置依据把企业网络权力划分为知识权力和结构权力。
Granovetter(1985)的研究表明,在一定条件下,只有具备等级差异的网络结构才能较好地协调网络内部各经济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但是由于这种权力在结构上存在较大的风险,很可能会因为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而导致错误的决策,因此在面临重大决策时只能依赖少数几个大的经济体的决断。在经济生活中,由垂直关系派生的权力和服从与由水平关系派生的信任和合作都发挥着巨大的影响(Granovetter,2005)。Wasserman(1994)指出,网络内存在一定的权力,当一个企业拥有其他网络成员赖以生存的关键资源,亦即当某个企业取得对网络中的资源流向的支配权的时候,探讨这种类型企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深远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权力在一定组织群体中对其他单元的影响力一直是学者们热衷的研究对象,目前学者们多从网络治理角度对企业网络权力加以分析。例如,Gereffi(1999)等学者以资源依赖论为基础,将权力的概念引入到企业网络分析中,侧重于探讨权力在网络演化过程中的治理作用。Turker(2014)通过投资者关系管理的视角对调解彼此利益的民主决策进行了研究,发现权力的非对称性可能会阻碍这种平衡决策,同时,组织间互动频率与信任水平会影响权力的应用。
也有学者探讨了网络权力对行为主体的合作行为产生的影响。例如,权力主体是存在于权力关系极差的网络中的强有力的、能驱动网络的企业(Taylor,2000);网络权力是网络行动者位置的体现,体现在价值链环节的占据与价值的分割行为之中(Smith,2003);网络权力是基于权力及其配置的组织之间的关系,它是行动主体在参与、互动、协调过程中相互博弈的结果。企业网络权力关系往往不对称,核心企业或者领导型企业常常具有更大的资源获取能力。因此,核心企业或者领导型企业的权力作用所体现的控制力更大,这使得核心企业在网络交换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并有权决定网络中其他企业的空间决策。网络组织作为松散的联合体,相互依赖是参与者之间的基本特征,这意味着网络合作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权力分配结构的影响和修正。Kahkonen(2014)通过考察网络中供求双方的权力关系与合作关系,分析了权力对合作深度的影响,发现网络中行动者的权力影响合作关系的形成及合作的深度,这一发现有助于提高管理者对网络权力与合作行为关系的认识。
六、网络权力配置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如前所述,网络权力是网络交换和协调过程中的影响和控制能力。中心度与中介性(brokerage)决定网络地位,而地位意识强烈的企业则会运用其由网络地位所带来的权力去谋取利益(Sozen,2012)。权力较大的企业可以协调组织间关系,统一网络成员思想,有利于网络中共识、惯例的产生。例如,跨国公司往往在产业集群网络中设立研发中心,以期有效地借助当地的技术信息开发出高等级产品,从技术和生产上获得对整个产业网络的控制权(Hall和Petroulas,2008)。权力较大的企业一般拥有较强的实力,其行为模式被认为具有较高的效率,可以节约交易成本,并被合作伙伴模仿,也会促进网络中惯例的形成。Kahkonen(2014)对网络定位与合作深度关系的研究也得出了相近的结论,认为合作深度受行为者权力定位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占主导地位的行为者可能不愿意与其他行为者建立关系而导致权力失衡进而阻碍深入合作;另一方面,权力较大的行为者可能渴望维护其权力位置而避免深入合作。
但是,有学者指出权力的运用是一把“双刃剑”(Ahituv和Carmi,2007),网络权力与网络惯例之间存在阈值效应。当网络中核心企业拥有绝对权力时,确实有助于避免冲突,协调网络运行,但是也可能令网络成员产生逆反、抵触心理,不利于网络惯例的形成。在网络组织中,边缘节点有突破生产、技术、市场权力等级的强烈愿望,而核心节点则竭尽全力维持已有权力关系(Dicken,2007)。权力现象因市场失灵或路径依赖等的不同,会使不同地区的企业或产业发展出现差异。如Lall 等(2001)认为,市场失灵、路径依赖等问题会使权力治理过程中企业学习和产业升级过程延长和充满风险,因此需要国家和政府干预来应对这些市场失灵。
学术界也开始关注网络权力对网络升级的影响。常见的升级路径包括技术升级、产品升级、过程升级、功能升级等,但关于网络升级的正确路径似乎并无共识。虽然个体行为会对网络产生影响,但不同研究表明,真正推动网络演进并决定其结构的是网络内所有企业的“行为合力”(Albino,2005),即网络内部企业所呈现的共同行为特征。Humphrey和Schimtz(2000)的研究表明,区域企业网络嵌入具有显著层级特征,其生产链可能对过程升级和产品升级是有利的,但会阻碍网络的功能升级。Gereffi(1996)则通过对购买者驱动的价值链和生产者驱动的价值链的权力关系的比较,强调了全球生产体系中只有核心治理者才能控制价值链。Dicken(2007)也指出,尽管地方企业网络中的核心节点并不拥有一个国家,却有着超越国家的统治力,通过技术、生产、市场等手段控制着整个价值链,而核心节点对核心技术的控制和对技术权力*技术权力是网络权力的一种,是网络结构非均衡性的体现。此概念由曾刚于2008年提出,其后张云逸(2009)进行了拓展。的维护,则直接影响到本地企业网络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攀升。但是在另一方面,层级明显、技术权力具有优势的企业网络,其发展存在着显著的路径依赖(Hess,2004),这种基于权力关系的路径依赖可能导致出现区域锁定或僵化,并导致地方企业网络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网络升级。值得注意的是,网络组织演进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大样本连续时间序列数据的获取难度较大,限制了此类研究的深入。
从实证研究来看,学者们较多地关注了发展中国家的外生型网络技术权力现象(林兰和曾刚,2010)。Gereffi等(2005)、Giuliani(2005,2007)等从技术创新的角度出发,研究了掌握关键技术的核心企业对企业网络等级结构的影响。Giuliani等在分析拉丁美洲国家企业网络升级过程后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往往通过压缩工资和利润来维持企业网络的存在,而不是通过本地技术创新来实现网络的升级。究其原因,当地企业技术力量薄弱、在技术上受制于网络核心节点是症结所在。技术领先企业有着强烈的兴趣去吸引、获得、使用创新技术,并将其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对于转型经济国家网络权力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Ratjargal(2001)以俄罗斯转型经济为例,列举了12种网络成员,通过问卷测量网络规模、联系强度与多样性,探索网络权力配置对企业绩效的影响。Peng和Luo(2000)通过考察宏微观联系(micro-macro link)研究转型经济中管理联接(网络权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转型经济与成熟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制度体系的发达程度不同(Welter,2004),在成熟市场经济下,制度信任较为发达,通常能够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市场交易成本较低,网络关系只是对正式制度的一种补充;而在转型经济国家中,制度信任水平较低,市场交易成本较高,网络关系起主导作用,成为不健全的正式制度的一种替代(朱秀梅和李明芳,2011)。因此,虽然网络合作关系在两种制度信任程度不同的环境下对企业行为都有积极促进作用,但其重要程度却存在本质差异。由此可见,网络权力在转型经济国家中的配置具有其特殊性,对企业行为的作用机理、影响结果也具有差异性。Harrison(1992)研究意大利的中小企业网络后认为,网络权力的演变可能存在三种不同的结果:(1)被外部财团所控制,成为财团的全球生产组织的一部分;(2)发展壮大成为等级组织的大型企业;(3)区域内部发展分化,导致地方生产系统破碎而逐步衰落。也有学者另辟蹊径,以风险资本辛迪加为案例,研究权力与地位的错配对组织间关系效能的影响。例如Ma等人(2013)的研究发现,权力与地位二者相匹配可提高组织间关系效能,以权力为导向的错配因保留了权力的合法性会增强正效应,以地位为导向的错配因无序互动会削弱正效应。Hingley(2005)探讨了作为破坏力的权力滥用问题,如果权力被用于统治与控制,则可能降低双方的信任,破坏合作的基础,缺少信任就会影响沟通与信息分享。
七、结论和未来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网络权力进行了多维度的研究,也取得了显著进展,尤其是把社会网络理论引入到企业网络研究之中,形成了丰硕成果,为后续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本文通过对既有的网络权力文献的进一步分析后发现,目前的研究仍存在如下缺陷:
第一,对网络权力的来源与决定因素的研究仍停留在思辨层面,尚缺乏深入分析。除网络结构、节点行为、资源禀赋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决定网络权力,学者们尚未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一些定量分析工具的应用也较为鲜见。
第二,网络权力配置的效率及其评价的研究进展仍然有限,尚处于“黑箱”状态,权力配置的方式、动力、结果等研究的系统性仍显不足,仅有的权力指数模型还难以刻画网络权力配置效率这一深刻命题。
第三,虽然学者开始关注权力配置对企业合作行为的影响,但网络中企业行为倾向和结构决定了企业间的联系方式及类型,影响着网络的演进,而现有研究仍未能找出一条清晰的分析路径,也未能对合作行为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第四,未能很好地诠释个体企业行为与网络升级演化之间的关系,鲜有从动态演化的视角对网络升级路径开展更为深入的探讨,对网络权力的演变以及对网络升级的影响关注不够,因此深层次挖掘其应用价值受到限制。
第五,微观层面探讨多而宏观层面探讨少。在全球生产网络化的大背景下,嵌入其中的地方产业网络权力的形成与运行机制、全球网络与地方网络的互动机理,以及网络权变对地方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等内容有待深入探讨。
第六,在企业组织网络与信息技术网络日益融合的大背景下,互联网对人的思维、企业的行为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因此,互联网的普及与应用对网络权力分布结构、功能发挥与系统演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无疑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研究方向,但现有研究仍显薄弱。
网络权力作为影响网络组织运行绩效和治理效果的重要因素,作为解释和预测网络节点经济和社会行为的重要依据,未来需要研究者做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只有深入探索网络权力的决定因素,客观评价其配置效率,才能更准确地解释和预测网络节点的经济和社会行为,为网络升级优化提供新的洞察。如何突破上述研究中的不足,打开网络权力的“黑箱”,开启禁锢网络组织健康运行的“枷锁”,探索网络权力制衡机理与网络升级路径,成为网络组织理论工作者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
[1]Ahituv N and Carmi N. Measuring the power of information in organizations [J]. Human Systems Management, 2007,26(4):231-246.
[2]Albino V, et al. Industrial districts as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Agent-based model of emergent phenomena[A].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Inter-firm Networks[C].Northampton: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05:73-82.
[3]Bonacich P B. Power and centrality:A family of measure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7,(92):1170-1180.
[4]Brass D J and Burkhardt M E. Potential power and power use:An investigation of structure and behavior[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3,(36):465-490.
[5]Bridge G. Mapping the terrain of time-space compression:Power networks in everyday life[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Society and Space, 1997, 15(5):92-112.
[6]Dicken P. Global shift:Mapping the changing contours of the word economy, 5th ed.[M]. New York:Guilford, 2007.
[7]Emerson R M. Exchange theory:A psychological basis for sociological exchange[A]. Berger J, et al(eds.).Sociological Theories in Progress[C].Houghton-Mifflin,1972:121-143.
[8]Foucault M. Power:The essential works of Michel Foucault 1954-1984[M]. Volume Two.London:Allen lane, 2000.
[9]Freeman L C, et al. On human social intelligence[J].Journal of Social and Biological Structures,1988,(11):950-979.
[10]Gereffi G. Global commodity chains:New forms of coordination and control among nations and firms in international industries[J].Competition and Change, 1996,(1):427-439.
[11]Giddens A. The third way: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M]. Cambridge:Polity,1998.
[12]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 (91):62-76.
[13]Granovetter M. The impact of social structure on economic outcomes[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5, 19:33-50.
[14]Hall S G and Petroulas P. Spatial interdependencies of FDI locations:A lessening of the tyranny of distance?[R]. Discussion Papers in Economics,2008.
[15]Harrison B. Industrial districts:Old wine in new bottles [J].Regional Studies, 1992,(26):469-483.
[16]Hayek F A.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ⅩⅩⅩⅤ, September, 1945, 4:519-530.
[17]Hingley M. Power imbalanced relationships:Cases from UK fresh food suppl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tail &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2005,33(8):487-514.
[18]Kahkonen A. The influence of power position on the depth of collaboration[J]. Supply Chain Management: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14,19(1):17-30.
[19]Krackhardt D. Assessing the political landscape:Structure, cognition, and power in organization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0,(35):342-369.
[20]Limerick D. The shape of new organization:Implications for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1992,30(1):38-52.
[21]Ma D, et al. Power source mismatch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The case of venture capital syndicat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3, 56(3):711-734.
[22]Maloni M and Benton W C. Power influence in the supply chain[J]. Journal of Business Logistics, 2000, 21(1):49-73.
[23]Markovsky B. Network exchange outcomes:Limits of predictability[J]. Social Networks, 1992,14(3-4).
[24]Martin R.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in economic geography[A].Sheppard E and Barnes T(eds.). A Companion to Economic Geography[C].Blackwell Publishing,2000:75-92.
[25]Parsons M D. Power and powerlessness in industry:An analysis of the social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J].Labor Studies Journal, 1988,13(3):231-256.
[26]Smith A. Power relations,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regional transformations:Pan-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outward processing in the Slovak clothing industry[J]. Economic Geography, 2003,79(1):17-40.
[27]Sozen H C. Social networks and power in organizations:A research on the roles and positions of the junior level secretaries in an organizational network[J]. Personnel Review, 2012,41(4):487-512.
[28]Turker D. Analyzing relational sources of power at the inter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system[J].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2014, 32 (3):509-517.
[29]Yamagishi T, et al. Network connection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in exchange network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8,(93):2103-2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