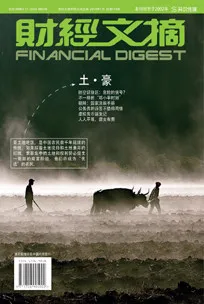英拉的“泰囧”时刻


“英拉滚出来!”
伴随着口号的高呼,示威者挥舞着泰国国旗涌进曼谷,并导致曼谷中心区一度瘫痪。尽管英拉解散国会下议院,并决定在2014年2月2日举行大选,但泰国已经更深地滑向危机。
反对派希望泰国摆脱英拉的控制以及流亡者他信对泰国政局的影响,但英拉作为泰国总理,也作为他信的妹妹,无论是从政治关联上还是血缘上,她都不可能让反对派予取予求。
英拉·西那瓦的“原罪”
反对派抨击执政者,无可厚非。在泰国,总理的昵称是可以被拿来开涮的。
“螃蟹”,是英拉的昵称,她本人也不拒绝将这个昵称公开化,在推特上,她账号就叫“螃蟹英拉”。在2011年英拉当选泰国总理以来,“螃蟹”已经开始特指英拉,《关闭铁路,推翻那只螃蟹》《那只螃蟹又去香港看她哥哥啦》等标题随处可见。
反对者批评英拉不仅因为政治关联,更因为英拉身上的“原罪”——他信的妹妹。曾经他信是泰国历史上首位任满四年并成功连任的总理,即便他现在流亡海外,但他所建立的政党依旧“掌控着泰国政局”。
事实上,无论谁接替他信上台,都会被认为是他信的“代理人”。他信在国内代表穷人阶级,在泰国6300万人口中,70%是农民和城市草根,这些人念念不忘他信的福利政策,比如约合人民币10元的廉价医疗,这些都坚定撑起他的票仓。尽管在2006年那场不流血的政变中,他信流亡海外,泰国在他信流亡后的6年里换了6位总理,他信的政党也从泰爱泰党改为人民力量党,后又改为为泰党,但这个屡次“变脸”的政党一次次地在议会中获胜,然后一次次地被解散,然后改头换面再重来。
英拉所在的为泰党在2011年推出英拉作为总理候选人时,竞选的口号竟然是“他信想什么,为泰党就做什么”。也无怪乎,在英拉试图与反对派达成和解,并企图通过大赦法案时,被反对派强烈抵制。
在2004年—2011年,泰国政治曾陷入街头抗议的混乱年代,其中在2010年,时任总理阿披实甚至动用武力镇压“红衫军”,造成90多人死亡,400多人受伤,阿披实也以谋杀罪被起诉。
在无数次的对抗中,双方仇恨的种子早已埋下,且生根发芽。大赦法案意在赦免2004年—2011年间因政治更迭而受到指控的政客,以此达到政府与反对派的和解,但反对派依旧不能接受他信也被包含在赦免范围内。于是,冲突再次激发。
民主路漫漫
多年的动荡,让泰国人心有余悸,但双方并未达成真正的和解。
2010年,因为武力镇压“红衫军”,阿披实下台了,泰国人选了一位女总理上台。“妇女比男人小心谨慎。”在2011年英拉当选之后,路透社采访的一位曼谷太阳镜商店老板娘说,“双方打打闹闹若干年,换个女总理上台,也许会平静一点?”
事实也是如此,在微妙的平衡中,泰国度过了平静的两年。即使英拉触动了反对派眼中的地雷——他信,但她也并未将泰国带入暴力的深渊。
面对示威者冲击总理府、警察局、电视台等机构,英拉并没有下令采取强硬手段,这固然有不愿重蹈2010年民主党政权覆辙的考量,不过也不排除英拉主动选择了非暴力。
在政治僵局中,她仍与阿披实以及素贴保持接触,不断谈判,甚至许诺以辞职来换取和解。她甚至可以眼含热泪对着摄影机,请求反对派放过她10岁的儿子。
“求求你们,如果你们有孩子,就会知道母亲的心情。如果你们有怨气,请向我发泄,我是他的母亲。请不要给我的儿子压力。”因为有反政府示威者在她儿子就读的学校放哨骚扰孩子,英拉哽咽地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
可以预见的是,历史漫长的势力缠斗仍然会不停休,在民主这条道路上,泰国依旧要“上下而求索”。
宪法的缺失或者得不到尊重,也许是泰国动乱的根源,在宪法没有得到充分完善的情况下,选举机制被引进,于是原本只该发生在议会,用口水仗、公平竞选就能完成的斗争,转移到了街头。
Fiona根据《经济学人》《卫报》《周末画报》路透社等综合编译。
本栏目责任编辑: 张菲菲(fionazhangfeifei@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