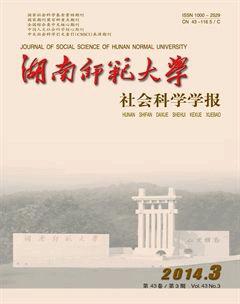现代社会以身体进行个体认同的哲学反思
尹岩
摘 要:以身体进行个体认同是现代社会最普遍的个体认同现象。身体对于个体的本体作用以及与个体的对象性关系使身体在个体的自我确证和体认中处于重要地位。个体认同对于“安身立命”的意义、身体在社会生活中的符号化和资本化,使身体成为个体“自我”的核心要素。以身体进行个体认同使个体意识发展和完善,但是现代社会的历史局限性以及个体的有限性也使它可能对个体产生负面作用。以个体的尺度处理好三种基本关系可以使以身体进行的个体认同朝着有利于个体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个体;个体认同;个体与身体的关系;身体的社会属性
作者简介:尹 岩,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学院研究生院博士(上海 200444)
克里斯·希林指出,在高度现代性的境况下,“身体会越来越成为现代人的自我认同感中的核心要素”,“人们倾向于更加重视身体作为自我的构成要素”。{1}以身体进行个体认同正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这意味着个体以身体为视角对自己、周围世界以及与它们的关系新的理解方式的确立以及这一认同方式对个体的存在和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以身体进行个体认同,身体必然被关注、被“善待”、被建构、被消费、被规制,身体的标准会变成个体生活的重要尺度,身体与社会的互构也会凸显。以身体进行的个体认同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社会问题,对这一社会现象应持何种态度,需要我们从哲学的高度对其进行审视。
一、现代社会中的个体与其身体的关系
在这里,个体不是指“单个的人或生物”{2},也不是指“具有社会的、精神的和自然的生理特征的单个存在物”{3},而是指独立为自己生活负责、自主把握自己人生命运的个人。
不同社会形态下个人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特性不同。个人从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享有人生自由是现代社会才有的事情。也就是说,个体只是反映现代社会个人存在特性、生存方式的特有范畴。现代社会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市场经济是以社会化大生产、分工劳动和生产资料、劳动产品属于不同的所有者为前提、以工业为主导产业、以厂商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经济形式。市场经济使每个人的生产都以交换为目的,每个人通过市场向厂商提供生产要素形成个人收入,个人再以其收入按等价交换的原则向厂商购买各种消费品,于是,“人们之间内在的劳动关系颠倒地表现为劳动产品—商品之间的关系;个人对社会劳动的依赖性表现为人们对劳动产品的共同代表货币的依赖性”{4}。马克思把这种以商品交换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普遍的劳动关系称为“物的依赖关系”。
“物的依赖关系”本质上是一个由于人相互需要而形成的以交换价值为基础、以等价交换为原则的物质交换体系,黑格尔称之为“需要体系”{5}。每个人在这个“需要体系”中以自己为目的以他人为手段,通过成为他人的手段而实现自己的目的。这确定了个人自由。马克思说:“从交换行为本身出发,个人,每一个人,都自身反映为排他的并占支配地位的(具有决定作用的)交换主体。因而,这就确立了个人的完全自由:自愿的交易;任何一方都不使用暴力;把自己当作手段,或者说当作提供服务的人,只不过是当作使自己成为自我目的、使自己占支配地位和主宰地位的手段。”{6}“物的依赖关系”对个人自由的肯定作用,首先表现为个人以其劳动为中介对自身自由的肯定。尽管个人作为个别生产者的劳动内容由社会联系所决定,他只是作为社会联系的一环而劳动,但他的劳动却是依据他自己的选择和能力展开的。其次表现为商品交换过程中个人平等地位和权利的实现。每一个交换价值的实现,都是商品所有者以自己的劳动对社会总财富的享用和支配,每一个交换行为都是商品所有者按照自愿的原则通过互相转让而实现互相占有,这意味着他们互相承认对方是所有者、是享有同等权利和责任的交换主体。再次表现为政治的民主化和社会管理的法治化对于个人自由的根本保障。“物的依赖关系”重构了社会结构,它不仅使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相分离,而且形成了“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和“该阶段上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7}的新型社会组织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中每一个人相互需要的利益关系以不可抗拒的力量使每个人进入到交换制度中,并按照商品交换原则发生基本的社会关系,这“使群的存在成为不必要,并使之解体”,“作为孤立个人的人便只有依靠自己了”{8}。个人特殊利益的存在,产生了个人参与社会管理、社会决策的必要性,即进入政治社会的需求。个人既是市民社会中的一员,又是政治社会中的一员,意味着社会管理的法治原则的确立。{9}此外,还表现为对货币的依赖性对个人自由的促进。西美尔指出,“货币是人与人之间不涉个人的关系的载体,且是个体自由的载体”,“货币无动于衷的、客观的本质有助于从人际关系中去除个人的因素”,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以货币来表现,使得“人更多地依赖社会的整体但却特别地不依赖社会的任何一个确定的成员”,这“最有利于产生内在的不依赖性和个体的独立性感觉”{10}。“物的依赖关系”下个人自由的获得,确立了个人对于自己生活、整个人生的主体地位和能动性、创造性,个人由此变成个体。
个体本质上是主体性的实体。个体要通过某个事物确证自己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性质,这个事物与个体之间至少存在两种关系中的一种。其一是主客体关系。主体即对象性活动的行为者,是与客体相对应的实体性要素。人的对象性活动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以主体的身份根据自己的尺度,从物质和概念上接触、影响和改造客体,在客体身上体现自己的本质力量,客体因此成为映现主体自身的存在。正如马克思所说:“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这就是说,对象成为他自身。”{11}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2}由此可见,与个体构成主客体关系、成为个体作用的客体具有确证个体的意义和作用。其二是本体关系。个体作为实体性存在,有它实际的物质存在形式。个体与其物质存在形式之间的关系就是本体关系。个体具有主体性,即在对象性关系中自主、有目的、能动、自由地活动的特性。个体的主体性要通过个体的物质存在形式的确定性运动才能传达和体现出来。因此,与个体具有本体关系的事物也可以确证个体。
通过身体进行个体认同,说明个体与其身体之间存在着上述关系。主客体关系是个体与其身体之间的最重要关系。人是通过以身体和身体的活动存在着的,身体从来都是受人支配、被人改造和塑造的对象。虽然身体是个人的身体,但这不意味着对于身体的权利和责任属于或者完全属于个人。因为个人是社会性存在,身体的权益是社会关系的内容之一。个体的实质意义之一是个人享有人身自由,现代社会法律中的身体权、健康权和生命权就是明证。人身自由是个体对待自己身体的自由,即个体在法律的界限内按照自己的尺度把身体作为客体对其自由地施加作用。本体关系是个体与其身体之间的基本关系。身体是个体的物质存在形式,这把身体和个体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一方面,个体以身体存在于世,身体为其存在和发展提供目的;个体以身体面对和作用于世界,身体为其提供意识、行为、活动的能力;身体是个体巨大的感受器官,以各种体验为其选择提供依据;身体是一个开放系统,具有以自身的变化适应环境的巨大潜力,这使个体的存在和发展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个体以自己本质力量作用于身体,满足身体存在和发展的各种需要使其更享受、更愉悦;积极地发展身体的体质使其更健康、更长久、更有活力;努力地改变身体的外观和约束其活动使其更符合真善美的标准。
个体与其身体之间的这两种关系确立了身体在个体生活中的根本地位以及身体在个体认同中的核心地位。个人成为个体意味着个人的实存方式发生了两个根本改变:一是个体享有自由,同时失去共同体对其生活的根本保障,劳动的社会联系和物质生产的总过程成为个体命运之神,它们用看不见的手分配着世俗的福祸,使个体生活在充满风险的境况之中;二是个体自己确立生活的意义和生活方式,按照“为我”原则构建生活价值体系,生活的直接和最终的目的是使自己“活着”并且“活得好”。这两个根本变化把身体在个体生活中的地位凸显出来。个体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没有什么是确定不变的,相比其他事物,身体是个体唯一能够直接确定和把握的存在。如克里斯·希林所言:“有些人丧失了对宗教权威和宏大政治叙事的信仰,不再从这些超人身的意义结构那里得到清晰的世界观或自我认同。对这些人来说,身体至少开始像是能够提供一个牢靠的基础,在现代世界中重新构建一种可以仰赖的自我感。”{13}个体生活的“为我”原则即以个体内在尺度为尺度生活的原则,“为我”必然“贵身”,即如老子所言:“吾所以有大患者,惟吾有身。”{14}由于“人们与其身体之间的关联方式越来越具有反思性”,在身体被赋予本体意义的时代,“自我”中必然融进更多身体的内容。
二、个体认同中的“安身立命”与身体
个人成为个体,倚赖于精神上对于个体的“自觉”,也就是说,为了保持个体的独立性和自由意识,个体需要一种明晰和强烈的个体认同意识。从哲学的意义来理解,个体认同是个体以其主体地位、性质、现实规定性、现实能力等为对象设问、以主体身份作答而形成的较为稳定而统一的自我意识的过程。吉登斯认为,个体认同“是一个不断整合个人经历与基本信念的历程”{15},是“反思性的组织起来的活动”和“首尾一贯又持续修正的个人经历的维护”{16}。从吉登斯的论述可以推断,个体认同的过程和结果关联着一个核心,那就是“自我”的形成、维持和发展。“自我”形成于“我”对“我”的思维中。“我”是个体的反身自指。个体是一个总体性范畴,反映一个人完整生命过程中每时每刻“主体”之“共性”。于此相应,“自我”也是一个总体性范畴,反映个体每一个生命活动中主体“我”之“共性”。因此,“自我”是整合性质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个体认同又常常被理解为“同一性”——我们把现在的自己与从前的自己如何看成是同一个主体。
个体认同本质上是个体的自我定位、归类或体认,其成果是个体对“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的社会地位和人生使命是什么”,“我与他人是什么关系”等问题有明确的认识,形成个体的历史方位感,对于生命和存在、权利和责任、归属和独立、角色与位置等关系问题有系统的观念,形成个体的现实方位感。这些方位感,成为个体评价社会和他人、对自己人生做出选择的根本出发点,维系着人格的统一性和一贯性,因而它们给个体存在以稳固的核心和定力,帮助个体在生活世界找到“立足之地”,个体认同发生的时候,“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声音在说,这才是真正的自我”{17}。个体身份和地位的确立意味着个人把自己与现实世界区别开来,把各种事物当作自己的对象,与之建立主客体关系,使自己“活着”,即“安身”,而且要“活得好”,即“立命”。因此说,个体认同的真正意义就是个体实现在现实世界“安身立命”的目的。
“安身”即使身体“安在”,既是指满足身体的基本需要以维持个体的生命存在,也是指使身体的行为、活动以及存在方式社会化以实现身体的社会认同。“立命”即确立人生意义和目的,即以身体的力量创造价值、发展身体的素质和能力,同时满足身体存在和发展的需要。由此可见,身体对于个体的“安身立命”具有根本的意义。这一意义突出地表现为身体给个体以存在感、安全感和归属感。存在感是个体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肯定性评价,体现为个体对自己存在状态的满意和社会对个体的尊重。“物的依赖关系”下,社会的价值标准、宗教权威不再对个体人生普遍起作用,个体对自身存在状态的满意,一定和身体基本需要的满足、身体的美好感受联系在一起。而社会对个体的尊重一定是对包括身体权、健康权和生命权在内的个人身体权益的维护和保障。安全感是个体对其重要权益得到保证或保障的精神反映。最深刻的安全是生命的安全,其中身体安全是个体的本体安全。身体安全是个体最原初的和最后的安全感来源,剥夺身体存在的权利,才是对个体的真正惩罚。归属感是个体在精神上产生的从属感和依赖感,它来自于个体对对其存在和发展至关重要的事物或关系的把握。对于个体而言,除了他的身体没有什么是绝对确实可靠、可以托付的,即使他失去了所有的财富,他的精神仍能保持着对其身体的拥有和支配;即使他被全世界嫌弃和抛弃,其身体也还是会欢迎精神回家与之同甘共苦,有朝一日若精神重振,也一定是身体的鼎力支持。正是身体给个体带来的这种存在感、安全感和归属感,才建立了身体与个体认同之间的关系。
三、身体的社会属性对于个体认同的意义
个体是现实的个人,既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个人{18},也是构成社会有机体的细胞。个体作为“现实的个人”,既从现实的生产、社会关系中获得具体的规定性,也是社会有机体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第一个和基本前提。身体作为个体的物质存在形式与个体一道从社会的生产和生活中以及整个社会关系中获得各种社会规定性,同时参与到社会有机体的构建中。社会是通过社会关系构成的人群共同体,社会关系既是社会结构也是社会规范。个体存在于社会中,就要被社会关系规训和塑造。社会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还创造了把握世界和自己的独特方式,这些方式通常表现为一整套符号系统、话语体系和解释系统,它们一同构成了社会文化体系的核心内容。每个个体都面临着进入社会文化体系、接受社会的知识、价值观、行为模式、习惯传统、社会角色进而发展自己社会本质、按照社会的标准成为现实的个人的任务。个体进入到社会关系之中,接受社会的同化和教化是其在思想上和行为上“向社会而化”的成人过程,也是社会对其身体及其行为、活动进行干预和赋予意义的过程。福柯就研究了“支配身体的那些制度/机构”和“话语”对身体的“生成”作用{19},戈夫曼则发现,“对于维护日常接触、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来说,对于身体的管理至关重要”{20}。个体以其身体进入到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活动中,既为社会关系的构筑奠定了基础,也直接构筑了诸多社会关系。比如,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夫妻关系、家庭关系要仰仗身体之间各种照看和互赖关系;男女的身体结构、功能、特性的差异产生了两性的基本关系,其中也包括两性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语言能力、工具使用能力、性别、年龄、相貌等身体状况直接影响到社会分工、社会地位等,某些社会区分或定位就以身体的状况为标准,直接把具有某种身体特征的人划归到某种社会关系中;身体的行为方式也会对社会阶层的流动产生作用。
身体与社会的互构、互动关系表明:社会必须要对个体的身体进行规划,社会关系、社会文化必然对个体的身体产生影响;个体对身体有意识、有目的的改造和规划,有助于个体改变自己的社会关系、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这两种力量使个体的身体向着现代社会的本质发生变化,主要体现为身体的符号化和身体的资本化。
身体的符号化是指身体“向符号而化”的趋势。符号是指包含或表示某种意义的可感形式。这里的意义包括个人的、社会的全部精神内容。符号是人的精神外化的呈现,它的生成在于人是受意识支配改造对象的存在。接受人的意识的作用的事物是“意识化”的事物,因而是承载意义的符号。人的意识最直接最经常支配的对象是人的身体。身体是人类社会的主要符号之一,人的体质、面部表情、动作、行为等都是人的精神的代表或表达。现代社会,个体社会关系多方位展开与复杂化、个体自由、生活自主、身体权益向个体回归、个体意识全面发展、社会文化日益丰富,它们使身体在更大范围内、更广泛意义上成为社会和个体作用的对象,这提高了身体的“意识化”水平,提升了身体的符号化程度。随着个体社会生活的展开,其身体成为社会作用的对象。这一过程要通过个体的身体来加以实体化、有形化和可视化,个体身体由此成为社会符号,在社会意义坐标系中占有一席之地。身体作为个体的物质存在形式、生理组织,既是个体满足自己需要的工具,也是生活活动的目的,因此身体也是个体意识作用的对象。个体的身体不仅承担着使个体成为主体的任务,而且还承担着把个体与他者区别开来、表达个体意志、体现个体人生价值的任务,这使得个体更加重视和致力于身体的符号化。现代社会高度配合了身体的符号化需要。吉登斯指出,现代性“将个体从自然中解放出来”,“身体不再是某种外在‘给定的东西,在现代性的内在指涉系统之外运作”,而是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融入社会生活的反思性组织”,乃至于我们“要负责设计自己的身体”{21}。首先,突飞猛进的现代技术“促进了个体选择和社会技术对身体的殖民化”{22},“从生物繁殖、基金工程、整形手术到运动科学,在五花八门的领域的发展趋势的作用之下,身体正越来越成为一种包含多种选择可能和选择权利的现象”{23}。其次,现代消费文化动用了现代视觉和传播技术制作的广告和创造的时尚,制造了统一的身体美学标准,引诱人们进入到身体创造之中,它们总是让人们产生一种信念和信心,即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身体对于某些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而变得更加赏心悦目。
身体的资本化是指身体变成带来利益的价值。身体的资本化标志着身体的普遍商品化趋势。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的生存法则是,要实现自己的目的价值,就要同时把自己作为手段实现交换价值。这其中就包括以身体为手段实现交换价值的各种情形。身体因能够满足人的诸多需要而具有诸多价值,这使身体有可能成为其所有者在商品交换关系中获利的资本,包括个体支配其身体创造产品或提供服务通过市场实现交换价值、身体以附带价值的形式为个体获得利益和身体直接作为商品用于获得各种好处。择偶、婚姻关系、友情、交际活动,虽然本质上不是身体之间的关系,但是身体的状况却对这些关系产生极大影响,符合审美标准的身材和相貌、气质、行为对人的吸引是不言而喻的,它们给拥有者带来更多的机遇、机会以及好处,卖淫、性贿赂、代孕、器官买卖就是以身体交换利益的表现。由此身体被称为个体的第二竞争力。
身体的符号化和资本化对个体认同产生了深刻影响。意识对身体的支配作用使身体不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生命存在,而是具有意义的符号、一个和人的“想要”、“意志”相关的“为我”之物。身体的符号化在身体与“自我”之间建立了关联:身体在意识的支配下发生的变化是“自我”的对象化;身体对意识支配自己的活动的感受是生命状态的“自我”的体验。身体在社会生活中的资本化是人与人之间建立社会关系的反映,体现的是身体的所有者对于他人的占有和支配关系。因此,在身体符号化和资本化的境况下,个体必然以身体作为确证和体认自我的“材料”,个体认同就会越来越联系着身体、联系着社会、他人对身体的价值判断而进行。
四、通过身体进行个体认同的双重效应
如同尼采的身体哲学给整个现代哲学带来人文主义气息一样,个体认同在身体维度上展开、把身体作为自我的构成要素,这种状况带来了个体从身体角度对个体及其生活的解释性意义,其结果是:与身体相关的感受,由身体形成的态度,与身体的改变联系在一起的体验,与身体的面貌、特性、行为、活动相关的奖赏或惩罚,都会使个体把“我是谁”、“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的问题置于醒目位置,引发他对其存在状况的“人道主义”反思。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算不算人?生活不能自理是不是人?被规训、虐待是不是人?笑贫不笑娼说明了什么?除了工作没有任何享乐的人生值不值得过?吃喝玩乐是否是真正的人生幸福?等等。
把身体放到个体认同的核心位置,把身体作为自我的要素,使个体把身体与他“成为什么样人”紧密联系起来,这将推动个体意识在三个方面的进步:其一,“身体意识”。以身体实现个体认同,身体就要具备确证个体、表征自我所需要的各种素质、规定性、现实能力和外貌等。为此,个体就会自觉地把身体当作对象,在观念中形成关于身体的“理想图景”,并制定实施方案,对其进行有意识、有目的的塑造、改造和规制,使其成为“为我而在”的身体。对身体的塑造、改造和规制会使身体受益和精神面貌改善,比如适当的控制体重,既可以避免与肥胖相关的疾病的发生,也可使身体看起来更有美感,这无疑会提高个体的自我评价、自信心和对美好生活的感受力,这将成为个体身体意识发展的强大动力。其二,与身体紧密相关的“生命意识”、“人权意识”。个体从身体的角度理解自己,重构了生命意识的核心。现代社会,与身体在个体认同中的醒目地位相对应,对个体的尊重延伸或具体到对个体身体的尊重,个体的生命意识加进了与身体相关的内容,如安全意识、死亡意识、健康意识、幸福意识等等。与此同时,个体的人权意识开始觉醒,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等各项人身权受到关注。这标志着个体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自我认识。其三,生活价值意识。个体生活价值意识指的是个体以自己的需要、规定性和现实能力在满足自己生活需要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价值意识,包括生活价值心理和生活价值观念。个体从身体出发,身体成为个体从事生活活动的尺度、标准和出发点,这使得个体生活人性化。有学者指出:“生活以身体为目标,身体的力量和意志创造了生活,生活与身体的关系就此发生了置换:生活成为身体的结果,生活被身体的权力意志锻造和锤炼,在身体的激发下,生活成为一件艺术品。”{24}不仅身体的需要成为个体需要的重要内容,满足身体需要的活动也成为个体生活的基本的和主要的活动。这些活动改变和塑造了个体的生活理念、生活规划、生活制度和生活风格等生活价值意识的核心内容,不仅使个体生活价值意识向着人本化的方向发展,还推动了个体对与身体相关的社会性价值的追求,如健康、运动、休闲、爱情、友谊、卫生、舒适、高雅、享乐、仪表、风度、气质,等等。
以身体进行个体认同也存在着否定个体自身的倾向。这一倾向首先产生于个体与身体的主客体关系中身体的客体性对个体认同的限制。个体以身体认同自我,必然把身体当作客体,与之构成主客体关系。身体成为客体,其自身的结构和规律对于个体来说具有外在独立性,身体的存在和变化对于个体的“为我”和“自为”的活动保持异向的趋势,即身体不是这一主客体关系中与个体天然一致的力量,而是个体所要驾驭和改造的对象。身体不满足个体,个体才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身体,这表明在个体与身体的主客体关系中存在着主观化和随意性的可能,存在着个体对身体的作用超越身体限度的可能性。身体的符号化、资本化以及消费社会的性质大大增加了这一超越的可能性。在利益面前和“无知”的状态下,恰当地对待身体已是困难的事情。身体自身的结构和规律不能给个体的行为划定界限,它就以否定自身的方式回应个体的不当行为。其次,这一倾向来自身体的必然性对个体认同的约束。身体的必然性是指由身体的自然特性和社会特性决定的确定不移的性质和发展趋势。身体自然特性决定了人生注定要它要经历几个以身体的生理性变化为标志的阶段,这将使以每一个阶段的身体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个体认同最终要面临困境,比如,个体在青春期发生的认同危机,生养和哺育期、更年期、衰老期发生的个体认同危机,而死亡的前景又何尝不让个体陷入生存悖论的困扰之中。个体身体的社会特性决定了身体必定要接受和承受社会以自身为目的以及个体以社会生命为目的对它的各种作用。倘若个体的身体始终不能产生对于某种社会关系的适应性,他便无法找到自我和确证自我。再次,这一倾向来自现代社会个体存在特性对个体认同的制约。个体存在的基本特性之一是个体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自己养活自己,他必须以自己为目的的同时以自己为工具,这有可能使个体陷入两难境地。以身体为目的,满足身体的一切需求,就要把个体更多地当工具,才能把个体劳动更多地转化为社会劳动以换取更多的货币,才能在市场上购买更加如意的商品以满足身体的更多需求。在以劳动为谋生手段的现代社会里,劳动不仅损耗身体,占用身体的休息时间,还对身体具有强制性,对身体产生各种不良后果。在一个“自力更生”的社会里,失去身体健康,就是失去“安身立命”之本。个体存在的基本特性之二是个体获得了人身自由,但是比任何时代都更加依赖社会。“物质交换体系”形成了人与人之间根本利益基础上的依赖关系,没有个体能把自己、自己的生活置于这个体系之外。社会分工和身体技术的专业化使任何个体不可能具备重构身体和赋予身体意义的能力,个体必须借助现代科技的力量和专门生产部门、专家提供的技术及产品来实现对于身体的真正改造。这种状况“增进了许多人控制自己身体的潜力,但也增加了他们的身体受别人控制的可能”{25}。此外,对身体真正有效的改造本质上是由市场化的消费控制的。对身体的改造本身是要实现个体对身体的美好期待,但是,这一改造一旦进入到技术和消费领域,这一期待能否如愿以偿就由不得自己了。
五、以身体进行个体认同的三点启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以身体进行个体认同需要处理好三个基本关系:
其一,身体的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关系。个体以身体确证和体认自我,通过有意识的自觉活动对身体进行改造,这是身体的合目的性。身体无论是作为自然存在还是社会存在,它的存在和发展总是受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受各种规律的支配,这是身体的合规律性。因此,以认同为目的对身体随心所欲的改造或者以消极的态度对待身体,都将不利于个体认同的实现,只有在身体的规律性所提供的可能的范围内对身体进行有目的的改造,才会使身体在个体认同活动中发挥作用。
其二,身体的工具性和目的性的关系。身体是个体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满足个体存在和发展需要的最重要手段,这是身体的工具性。身体的工具价值几乎在个体生活的所有方面表现出来,个体的日常生活、社会生活、劳动活动、交往活动、娱乐活动等都离不开身体的作用。但是身体并非外在于个体,身体对于个体的意义还有内在的方面,比如,身体的存在和发展本身就是个体存在和发展的一个标志,身体既是“真、善、美”的载体,也是个体自由全面发展的一种形式,这是身体的目的性。身体的目的性和工具性都可以成为个体认同的依据,但是,对一方的过度依赖而对另一方面不以为然,都将引起个体认同的困境。
其三,身体的社会性和自然性的关系。身体进入社会关系、参与社会生活必然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和社会文化的同化而获得社会性。身体作为生命有机系统具有自然性。身体的社会性是从个体社会生活中生成的必然性,身体的自然性是个体生命有机体固有的必然性。物的依赖关系下,社会对于高效率和不断进步有巨大的需求,劳动力是生产要素,社会以能力为本位,这些社会条件使身体社会性中的大多数内容是对身体自然性的限制,而身体的自然性同样也对身体社会性起限制作用。因此,在以身体进行的个体认同中,对身体的自然性与身体的社会性及其关系持何种态度直接关系到个体的生活活动、生存方式和人生意义的选择,进而关系到个体认同的性质和内容以及个体认同的状况。
总之,只有从个体的本质、特性、现实能力和认同需要出发,以个体的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为目的,正确处理好上述三种关系,恰当地对待自己的身体,摆正身体在个体认同中的位置,才能使以身体进行的个体认同成为促进和推动个体的存在、发展的力量,从而避免由这一认同导致的自我否定的发生。
注 释:
{1}{13}{19}{20}{23}克里斯·希林:《身体与社会理论》,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页,第3页,第72页,第72页,第3页。
{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26页。
{3}黄楠森、夏甄陶、陈志尚主编:《人学词典》,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0年,第16页。
{4}刘佑成:《社会发展三形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0页。
{5}参见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03页。
{6}{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96-197页,第197页。
{7}{1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11页,第71-72页。
{9}参见王南湜:《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32页。
{10}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224-225页。
{11}{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4页,第274页。
{14}《道德经》,第十三章。
{15}沙莲香:《社会心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7页。
{16}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王铭铭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5页。
{17}转引自沙莲香:《社会心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01页。
{21}克里斯·希林:《文化、技术与社会中的身体》,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0页。
{22}转引自克里斯·希林:《文化、技术与社会中的身体》,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1页。
{24}汪民安:《尼采与身体》,汪民安主编:《身体的文化政治学》,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