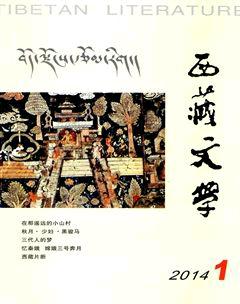这一场青春(短篇小说)
永基卓玛
一
年幼的时候,我经常在梦里听到一首女人唱的热巴,伴随着鼓点,脆生生的,却很甜美。像风一样,只是隐约,从来不曾真切过,就那么萦绕在我的梦中。
一直以来,我是个自卑的孩子,没有话语,没有朋友,一个人呆在屋子里,所以我以为,梦中的这个歌声是个梦魇,甚至是个不好的符号,像魔鬼的声音一样。我想摆脱她。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慢慢长大,参加工作,很多事情的顺序发生,在我没留意的时候,那个歌声离开了我。某一天,我想好好记录那个音符的时候,觉得有种懊悔,那个热巴女声去哪里了。
或者没有了这个魔鬼的符号,我的生活开始趋于平淡,上班,下班。每天吃饭,睡觉,依然不是很喜欢说话。只是这样的日子长久一点,就开始感到有点乏味。
当看到雍宗的时候,我知道乏味的人,不光是我一个人吧。已经二十八岁的雍宗在自己的烟店里,安静地在手中伺候着一些小玩意。
雍宗是我的死党,我们认识已经有十多年的时光,十多年来,我一直在歌舞团从事我的音乐编剧,而她,从藏北到藏南,又从藏南到藏东。我的生活每天都是音符,创作,而遇到她,总是给我一片风的感觉,每当我的创作没灵感的时候。这阵风总能给我无限的灵感。
可2009年的冬天,她却安静地回到永格,开了一个烟店,很多我们过去感兴趣的话题,她从不对我说起,偶尔,我想对她说点什么时候,她那长满雀斑的脸才从那些小玩意中抬起来,用眼睛瞟了瞟我,活着就是活着,你想那些子做什么。
每次,离开她的烟店时,我总感觉一种绝望。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夕阳暗淡。总有一种绝望的悲凉在心里迂回,我总在心里想到以前那个激情飞扬,像一股风的雍宗,那时的雍宗,连那些脸上的雀斑都伴随着她的语气嚣张地做着表情。我甚至以为,面前的这个人不是雍宗,可雍宗不是她,又能是谁呢。
这个春天,一直没下雨,说来永格并没有春天,当山头的雪快消融完的时候,草坝上才开始露出零星的绿色,这个时候,雨季来了。而夏天也来临了。
在雨来临之前,永格的城外一片苍黄,黄色的大地,黄色的山,黄色的房子。天也被染上了黄色。荒漠一般,毫无生机。
正如我渴望雍宗和我说话一样,我心开始渴望夏天,渴望着一场好大的雨,把这些黄色的大地好好滋润,我怕再这样下去,我的心已经慢慢在变为苍黄色。
可雨总不来。雍宗也不和我说话。每天的时间依然流逝。我坐在办公室里,咬着铅笔,在一张五线谱上画了一个音符,又画了一个音符。七零八落的音符之间连接不起来。我已经创作不了美妙的音乐了。在雍宗如风的日子里,我总有用不完的创作激情,每天不停地在五线纸上画来画去,那样的日子真让人怀念。
在写了几个不和谐的和弦后,我重重地把铅笔甩在五线纸上,走出了门。又开始走向雍宗的烟店。
现在是2010年的夏天。我又来到雍宗的烟店。她那长满雀斑的脸依然凑在那些小玩意上。隔着一张桌子,我们都没说话,我不知道说什么。
那些小玩意十元钱一个,只需用针线在一张布上绣些小点,然后把海螺式样的剪布缝到一起,一个小玩意就完工了。十分钟,她绣好一个红色的海螺。她又拿起两张绿色的布片,一分钟过去,我们没说话,她认真地绣着,两分钟过去了,她认真地绣着,我们还是没说话,三分钟,四分钟,漫长而短暂的十分钟过去了。又一个绿色的海螺在她的手中成型了。
就这样无言的十分钟一次又一次过去了。我手里拨弄着雍宗刚刚做好的海螺,对雍宗说,我们来聊点什么吧。
雍宗依然专心地对付着那些小玩意,眼皮都没抬。
我和雍宗在2010年到来的时候,都进入了同样的二十八岁,可我们都还没结婚。
我清了清嗓子。说说爱情吧。
雍宗头都没抬,只是一句。关于爱情,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凑到雍宗的耳边,那说说我们的青春,我在心里是多么想念雍宗像风的日子里。可雍宗更是冷淡,青春,青春已经完结了,你还想说什么。你是个莫名其妙的人。
可我还是不甘心,我想等下去,虽然从冬天已经等到春天,永格还没有一丝绿色,这个高原小城,春天总是到来的晚,所以我以为,雍宗给我的等待,也会晚点。
一个又一个的小玩意被雍宗做了出来,这中间,有人来买烟的时候,我帮她打点,有了我的帮忙,她更是脸都不抬专心地做着小玩意。
天色慢慢暗了下来,街上的各种灯光开始亮了起来。雍宗也没叫我吃晚饭的意思。我知道我该离开了。
永格,这个高原的小城正在以飞速的步伐发展着。只是我对永格却越来越陌生。我来到这个小城工作已经快有十多年,可好像越来越找不到故乡的感觉,曾经的环城河如今每天发着臭气缓缓前行,空中不时飘着被风吹起的垃圾。
我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街上喧哗的声响飞进我的耳朵里,落在我心里却是空空荡荡。
咩咩的车在我旁边停了下来。
“你去哪里?”
咩咩是我和雍宗共同的好朋友。我们三人曾经笑称我们是三剑客,可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不和我还有雍宗在一起玩。今天遇到他,我不免觉得很是意外。
“我去找了雍宗。”
咩咩哦了一声,对我的去向他并没有留意。他让我上车,说是带我去一个地方。
开了车门,我就闻到一股酒味。
咩咩是个酒鬼。以前我们在一起玩的时候,他就喜欢喝酒。雍宗也喜欢喝。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总有喝不完的酒,唱不完的歌,还有说不完的笑话。
“你又去找雍宗了。我都好久没见她了。”咩咩好像是在自言自语。却又好像是对着我说话。
关于咩咩,其实我也是好几个月没见到他。这个曾经被大多数女孩子称为高原黑皮肤美男子的男孩,好像离我越来越远,偶尔的电话联系,我们都没有了交谈的欲望。
这个晚上,咩咩和我的意外相遇,他好像想对我说点什么。我带你去一个地方。说完这个话,他的车呼啸着驶出永格。
风在车窗外呼呼直响,音乐被咩咩开到了最大声。我有些不安。这样的嚣张,好久没有过的事情了。车子驶到城外的白塔边时,咩咩关掉了音乐,大声地念着我们转山时经常念的咒语“哦……咩……咩公撒落……”。绕着白塔三圈,车子继续向前驶去。
在我们的身后,永格被一片暧昧的红色笼罩着,永格上空的黑夜,也是暧昧的紫色。咩咩不停地说着话。
我一直在期待着雍宗对我说点什么,可雍宗一直没开口,却是遇到咩咩,面对咩咩,我却不知道说点什么。
咩咩说,永格在变。你感受到了么。咩咩还说。我们的青春都在那些记忆中。
车子在离开永格很远的地方停住了。咩咩说。让我看样东西。
我们下了车,咩咩用手指着遥远的星空,认真地对我说,你看星星,再过几年,你和我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都看不到这样的星空了。
我抬起头,清冽的暗黑中,一闪一闪的星星起起伏伏。就在这片不远的星空旁边,永格城上空暧昧的紫红色已经虎视眈眈地挤压过来。
只有那么几分钟认真的咩咩忽然大笑起来,指着星空对我说,你要记着这星空啊。
笑声中,我感觉到他的异样。这个时候,我发现,星空的余光已经反射在他眼角的泪光中。
咩咩酒醉了。我对他说,我想回家。
咩咩斜视着我,他眼中能倒映星光的泪光已经没在了。剩下的,只是冷漠,他从怀里掏出烟点上,双手交叉怀抱着胸,我感到他要对我说点什么了。
“卡西,你真不是东西。”说完就上车了。把我一个人丢在星空下。
看着扬尘而去的咩咩,我竟然没有慌乱。我拨通了噶太的电话,电话一接通,喧哗声从电话里挤出来,我很不容易地辨认着噶太的声音,他在接待。
“噶太,来接我一下。好不好。”
噶太在电话里大声地说着,你在哪里,我听不清。
“你来接我好么。我在城外。”噶太好像一直没听清我的声音。费力地在电话里大声地说着,你在哪里,我听不清。
我把电话挂了。发信息给他。“我在城外,来接我。”
半天没有回信。我坐在地上耐心地等着。看着星空,想到咩咩,想到我,也想到雍宗,还有我那些写不出的音符。终于,我的耐心一点一点消失,可噶太还是没回信。我拍了拍屁股上的灰,往永格的方向走去。
偶尔有车从我的身边呼啸着飞过,这个夜晚,没有月亮,漫天的星星。我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烦躁。这个时候,噶太的电话打来了。“你在哪里。”
我说了方向,很快,噶太开着他的车来了。他已经喝了不少酒,见到我,他很奇怪,我怎么一个人跑到城外来。但我不想说话,我感觉累了。歪着头靠在座位上,看着离我越来越近的永格。
车子慢慢进入永格,又见到了路灯,车流,人群,热闹的永格,晚上也是这般的热闹。噶太对我很不满意。从上车开始,我就一个句话也没说,到了城里,我还是没说。他用手摸摸我的额头,我打开他的手,他带着诧异的神情问我,你是不是发烧了,烧昏了头。
噶太带着我来到永格最好的音乐屋,他的朋友在那里等他。可我不想进去。我还是想回家。噶太拉着我手,说,去和他坐会儿吧,我摇着头。
终于,噶太的耐心也没了。他自己往音乐屋里走去,对我甩下了一句话,你这个装模作样的家伙。
这就是我的生活,我是永格歌舞团的音乐编剧,2010年,我和雍宗一样到了二十八岁,但我也没结婚,有个男朋友,叫噶太,噶太是个本地人,和我一般大,当我焦躁地在雍宗的烟店与单位里来回奔跑时,噶太总没在我身边。
噶太不知道我心里想的事情。噶太开着一辆好车,生活从来对他是宠爱,我甚至怀疑他会不会忧愁,好像什么都不用他担心,他家里已经为他做好了一切,我甚至以为,他家里还为他安排了一个媳妇。
在他心里,他不明白我,正如我不明白他,他弄不懂为什么我每天那么执着地去看雍宗,而我也不明白噶太为什么每天的事情就是和朋友喝酒玩乐。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怎么就要走到一起。所以,我一直在期待下雨,我希望雨季来临时,和他分手,我想结束这一切。
可雨一直没来临,日子依然乏味地进行着。我依然写不出音符来。
我越来越烦躁。只是对一切都感到无能为力。
二
夏天快来临的时候,卡西变得越来越烦躁,她没日没夜地把自己关在宿舍里,谁也不见,偶尔她只去一下单位里的资料室。
在一个炎热的傍晚,卡西在资料室里发现了一盏煤油灯,那个煤油灯静静地待在保管室的角落,当看到这个煤油灯的时候,卡西没留意,她关心的是那些音符,卡西在资料室里走来走去,像个潜伏的野兽。
卡西把资料全摆放在地上摊开,自己光脚坐在那些资料上,其实卡西根本看不进去任何音符,但她就是不想离开有音符的地方。当然,这一切都是等保管员下班后,卡西借了钥匙,一个人偷偷溜进去,顶上门后才开始的。
卡西总是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一米七的身子瘦长瘦长的。
那个炎热的傍晚和往日并没有什么不同,小狗的叫声,还有小号声。该死的小号。小号应该对着朝阳吹。卡西总这样理解小号。
对于乐器,卡西有着自己的理解方式,小号是属于朝阳呢,如果是傍晚,应该来点小提琴或者钢琴。
卡西一个人在保管室里念念叨叨,保管室里忽明忽暗的灯光闪了几下,彻底熄灭了。这个时候,卡西想到先前见到的煤油灯,她小心地把煤油灯拿起来,她还要借个灯光把她摊开的资料全部都收回去,不然第二天肯定要被保管员数落。
卡西并没有打着煤油灯,她没有火柴,可是借着傍晚微弱的亮光,煤油灯散发着一股煤油味,卡西的心里忽然被打开一扇门,好像风雨快来临的前兆。她小心地拿起它,用衣服擦拭着上面的灰尘。
卡西心里说不出什么缘故,忽然就认定了这个煤油灯是个好东西。说着她带着煤油灯溜出了保管室。
在自己的宿舍里,卡西自己端详着煤油灯,上面写着一个标记,雨村。
好容易等到第二天,卡西又钻进资料室,这一次,她规规矩矩地在资料室的那些木柜边认真地站着,仔细吸吮着关于雨村的资料。桂花树,女土司,情歌,一串串平时很不见的字眼如同风一般在卡西的心里吹来吹去。
三
我是在一个早上突发奇想想去雨村的。
在雍宗不和我说话的日子里,我一个人在歌舞团的资料室里打发时间,在乏味的等待中,我看到一个雨村。我不知道这个雨村与我渴望的大雨有什么关系。但我决定前往雨村。
这次出门,我没对雍宗说,也没对噶太说。我背着一个大包,对歌舞团的团长说,我要去采风,就离开了永格。
客车在盘旋的山路上艰难地喘息着,偶尔我探出头去看山路下的悬崖,感到一股凉气从脚底一阵一阵地袭来。
我没向司机问雨村是什么模样的,我凭借着想象,一个有着女土司,有着桂花树,有着好听的歌谣的雨村。我心里总有些躁动不安的。
车子一路颠簸,走过土黄色的一座又一座的大山上,偶尔,有翘着尖屁股的山羊在路边缩头探脑地看着我们。雨村终于在傍晚来临的时候到了。
司机把我丢在路边,就扬尘而去。我一个人站在路边看着这个雨村。藏在山坳中的雨村也是灰不溜秋的,铺天盖地的黄色,村头到村尾,只有屈指可数的几颗树,上面的枝条还没抽绿,这样的村子还叫雨村。
四
雍宗有个名字叫乌鸦。这个名字很少人知道。
雍宗用乌鸦这个名字来写诗歌。当然,乌鸦并不是呱呱叫的意思,我也搞不明白,雍宗为什么会用乌鸦这么个名字来做自己的笔名。永格水葬的曲河旁边,乌鸦经常成群结队地,呆头呆脑地站在没有绿叶的枝头。待有人走近的时候,哄的一片翅膀拍打声,又呆头呆脑地站在另一颗没有绿叶的枝头上。
不过,雍宗写的诗歌真是棒极了。比如“生命在暗淡中,落日在辉煌中。”“飘落,是飞翔最好的姿势。”诸如此类的诗歌,我几乎全都会背诵了。我不敢对雍宗说,其实一些诗句我根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就是觉得棒极了。每次看到这些诗句,我总是很快地把他们背诵下来,一个人在心里默念的时候,越念越喜欢,心里好像有些说不清的东西,在心底痒痒的,但又很舒坦。
每次雍宗从远门回来,总有特别过瘾的诗句给我。
雍宗是属风的,咩咩也是属风的。
咩咩身边总不缺漂亮女孩,更多时候,我好像一个跟班的,跟着他去泡妞,跟着他去应酬,也跟着他去酒醉。咩咩有种天生的气度,能把周边的事情处理好,而咩咩总有那么多哲理,让我听得服服帖帖。
“虽然我很绝望,但我会表现得很满意。”这就是咩咩说的话。
我也不记得我们三个人是怎么走到一起来的,但好像就天生是好朋友一样,在两个人如风的日子里,我只需等待他们来找我,在这两股风的带动下,我的音符也总能不断在五线纸上哗哗流动。
五
卡西目瞪口呆地站在雨村的村口时,夕阳把她瘦长的身影拉得好长。一只尾巴上没有毛的狗远远地站着看她。客车喘息的时候过后,村子更显得寂寥。
关于雨村的种种想象,在卡西的心里出现了无数次,可眼前的景象从不是一千种想象中的任何一种。十多户人家七零八落的,没有绿色的大山,没有绿色的村子,苍黄的一片。
正在卡西费力地把雨村与眼前这个黄色的村庄联系到一起时,一位老人赶着一群羊,远远地走来。羊跑到很快,卡西被热闹的山羊叫声充斥着,尖屁股的山羊都不靠近卡西,卡西被山羊离开出一个圈子。这个时候,那个赶羊的老人慢慢靠近了,卡西在打量着老人的同时,老人也在打量着卡西。
看不出老人的年纪,大概有六七十岁了,花白的头发乱七八糟地被老人顶在头上,一套黄军装已经被老人穿得看不出颜色。
“阿爸拉。(注一)”卡西对着老人喊到。
老人在路的对面站了下来,也同羊群一样,不靠近卡西。
卡西思量着,走到老人跟前。“这里是雨村么。”
走近了老人,卡西忽然觉得有点怕眼前的这位老人,老人的眼珠是淡黄的,很犀利地看着卡西。
“嗯。”老人好像并不想和卡西多说什么。答应了一声后,并没有过多的言语。只是吆喝着羊群继续向村子里走去。
卡西背着大包跟在老人的后面。多次的采风经验中,卡西知道,要想知道一个村子的历史和传说,那就要和村里的老人多沟通,别看村里的一些老人一个个其貌不扬,可都是一部部活字典呢。只要有耐心,一个个传说会在老人身上生动地再现。
可这位老人并不想与卡西多交谈。又是一个乏味的老家伙,卡西在心里不无恶意地说着,可还是加快了脚步,紧跟着这位老人,还有这群羊。
在羊群搅起的灰尘中,卡西跟随着老人走进村子。
“哎,这里有个土司庄园吧。”总得找点话题,在羊群的热闹声中,卡西大声对老人喊到。
老人的步伐停了下来,卡西心里暗暗高兴,看来是问对话了。
可老人没立刻回答卡西,只是冷冷地盯着卡西看着。卡西被这淡黄的目光看着有点发麻。老人的下巴扬了一下,对卡西说。“你身后就是。”
卡西转过身。庄园?土司?卡西又一次目瞪口呆,虽然知道随着时间河流的冲刷,好多事物都会变得面目全非,可眼前的老屋,木板横七竖八,墙头的茅草丛生,卡西怎么也不能把这个老屋与土司庄园联系到一起。
“哎。这就是土司庄园?”卡西还想从老人的身上再一次得到准确答案,可转身一看,老人已经走到了离她很远的地方。
六
经常,我的脑子会处于一种发蒙的状态,比如现在。我不知道老人为什么要那么冷淡,完全一点都没有永格人的淳朴热情好客。老人很快随着路面沉淀的灰尘一样,没踪影了。
我在村里逛荡着,时间不找了。要找个地方吃饭睡觉。
“香巴拉大饭店”,走了会儿,我看到一个小食店,我弯腰走进那窄小的店门,眼睛慢慢才适应屋子里的黑暗。一个女人在唯一的一张桌子上打盹。屋子里,灶台就在桌子旁边,还有酒缸,不知道是放着水还是酒。
我走过去,用指头嗑了嗑桌面,那瞌睡的女人抬起了头。很迷糊地看着我。看来,发蒙的人并不是我一个人。
“可以吃饭吗?”“想吃啥子。”这个四十左右的女人边打着哈欠边问我。
“随便,能吃饱就好。”并不是很高的女人站了起来,边用手抹着脸边向灶台走去。
一会儿的时间里,女人做好了饭菜给我端了上来,她好像还是没睡醒的样子,头发凌乱地被盘在头上,脸上的皱纹也是同屋子里的光线一般,黑乎乎的。她给我做了一个洋芋汤,一盘羊肉冷片。给我放在桌子上后,她继续回到原来坐的凳子上盯着我。
羊肉味道很好。我饿坏了。大口地就着饭吃下去。我感到这个女人的目光一直盯着我,我猜想可能是因为她要睡觉的桌子放着菜饭,她不能继续爬着睡觉了。
女人还是哈欠连连不断。一边捶捶腿,一边看着我。
“这里能住宿么。”“啊哈,你今天要住在雨村。”女人的声音开始有了温度。
我已经确定了。这里真是雨村。“那你是找对地方了。雨村就我这里可以住人。除非……”
女人还卖关子。“除非什么呢。”我问道。
“除非你这里有亲戚了。”
“噶噶,我第一次来呢”我对女人说了。
“难不成你是为了看土司庄园。”我再无心吃饭了。女人已经说中了我的心事。
“呀,你真是厉害。”
“啊呀,来这里的人都是来看庄园的。几间烂房子,有什么好看呢,还叫庄园。”扑哧的一声,女人笑了起来。
“哈,如果要说是庄园,那你现在吃饭的地方以前也是庄园的一部分呢。”这个女人边对我说,边自言自语着,那么多的人来看什么庄园,村里的人往外跑,外面的人往村子里跑,看来不光我一个人对雨村感兴趣。“这里的确是住过一个土司的小老婆,土司为她建了房子,有些人就叫她女土司,不过,因为她没生孩子,在她离开世道后,房子这些也很快就破损了。”
“啊,这个村子为什么要雨村呢。”
“还不是因为缺水呗,缺什么就要什么了。”女人嘲笑着我。
“那村子里有桂花么。”
“有过,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些桂花呢,都是女土司在世的时候从其他地方带来的,她去世后,就全都死光光了。这里海拔那么高,怎么能长桂花呢。”
我被这女人的话语说得哭笑不得,雨村,也是像我一样渴望大雨的一个地方。
“不过呢,还有个女土司的情人,你看看呗。”女人的话语勾起了我的希望。“晚上,那老家伙会来喝酒呢。你等着吧。”
七
天色慢慢暗淡了下来,黑腻腻的桌上,女人点起来煤油灯,这和卡西在歌舞团的保管室里看的煤油灯一样,小火苗慢慢地摇晃着。
在和女人的聊天过程中,卡西慢慢知道了关于女土司的一些情况,女土司叫桂花,是个外地人,土司不能把桂花带回家,就在这里建了房子,把桂花放在这里。
村里的男人陆续来到这里,原来,这里还是村里的酒馆。
当这些男人得知卡西是来寻找土司庄园时,那表情无疑是看到一个笑话一般。有人在打牌,有人在喝酒,有人在听,有人在说,暗淡的酒馆里显得挺热闹的。
这个时候,一个人弯腰进了酒馆,他进来后,就地在门口的地上坐了下来,酒馆老板给他端了一碗酒过去,顺势把那个人放在地上的羊肉收了起来。
在他进来的时候,喧闹的酒馆顿时安静下来,安静了几秒钟,一阵轰然大笑。“土司的情人来了。你看看你名气多大。又有人来看你啰。”
卡西今天第二次见到那位老人,老人好像对那些调侃的话语听不见一样,自己坐在地上,喝着酒,根本就不理会那些人的笑话。那些人对着老人调侃了会儿,也觉得无意思,就转话题了。老人自己在自己的角落里喝着酒,酒馆的空间变得有点怪异,卡西说不出为什么。
老人坐在那里并没有说话,但他的存在却显出一个气场,包围在他的身边,把那些笑话都隔在了气场之外,
卡西静静地观望着这一切。老人自己喝着酒,周围发生的一切与他都没关系一样,酒馆女人在老人的酒喝光后,很快就去给他添酒,在喝了三碗酒后,老人站了起来。
“不唱歌了噶。”不知道谁喊出来的,又一次哄堂大笑。在笑声中,老人弯腰走出了酒馆的小门,门外,只是一片寂寥的黑色。
这个晚上,卡西知道了这个老人就是土司的情人,名字叫扎西。
八
早晨的村庄很安静,却处处蕴含生机。
卡西站在被称为土司庄园的那个破房子里。阳光从支离破碎的瓦片中漏进来,卡西小心翼翼地走着,地上铺着青砖显现着它的年代。
“那个时候,女土司喜欢村里人来这里聚会,她准备了好多酒和肉。”酒馆老板的话语在卡西耳边出现着,可现在,安静得连灰尘在那些阳光的漏缝中飞翔的声音也能听到。
“女土司从来不参加这些晚会,她手下的人自然把一切都安排好,女土司只是在楼上看着,而她只是藏在柱子后听着歌,一个人喝酒。”看着古屋,卡西感到一个叫桂花的女人的寂寞。卡西一会儿在这里摆个姿势,一会儿又弓腰藏到柱子后,她在感受着几十年前一个女人的光影。
“那个时候,扎西是晚会中最出风头的人,他的歌声啊,阿啧啧,任何一个女人听了都动心。什么东西都被他唱活了。”酒馆女人头天晚上对卡西说的话语不断在卡西耳边响起。
“但是啊,两个可怜的人了。都说女土司开晚会其实就是为了看扎西。”
卡西的脑海中不断飞影掠过,她在想象着。门外,有羊群的声音,卡西想到了昨天见到老头,他是不是要去放羊了。卡西跳出门外,看到赶着羊群的扎西老人已经走出好远。
卡西撒腿就跑,跟在老人和羊群的后面。
老人也不理卡西,自己挑着赶羊鞭轻快地走着。上山路了,卡西在后面跟得气喘吁吁,扎西老人像个猴子一般灵巧。那些山羊到了山路上,也更是显得神气,尖屁股在卡西的眼前晃来晃去。
九
我心里一直有个喜欢的人。但不是噶太。
咩咩总是嘲笑我,说我是爱情白痴。我不是很喜欢噶太,我喜欢那个对我笑一下,我就想哭的人,可我从来不敢和他说话。咩咩给我制定了无数个计划,计划中的男女主人公,总是欢喜地十指相扣,开始了甜蜜的生活。可现实里,面对那个笑容,我只是眼泪打了会儿转转,又来到咩咩的眼前,咩咩一看我的表情,就知道计划又失败了。
噶太说,第一次见我的时候,我正骑着一辆自行车飞快地从他面前驶过,我一手把着自行车,一手擦着眼泪,他第一次见到一个女孩子会这样哭泣,他开车跟着我,看我骑到歌舞团里,居然眼泪就流光了,跳下单车后,我竟然能和单位的人有说有笑,他觉得这个女孩子肯定是疯了。
后来,我使劲地回忆,也想不起我有着骑自行车大哭的场景。只是想,是不是我又遇到那个喜欢多年的家伙,那个人对着我笑了一下,我就难受得想哭泣,好像心里觉得很委屈一样。那个家伙出现的时候,我肯定没注意过噶太,因为啊,那个时候,世界都停止了转动。
“最多是掉了一点点眼泪。”我打死也不承认我会骑着自行车大哭。可噶太就是认定,他说,“那就一点点眼泪么,可以说是泪洒长征路。”
很多事情,同样噶太和我一起遭遇,可他描述起来就换了个样子。我也搞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再比如,我记得是他先喜欢我的,可他总是说我先喜欢他的。“那个晚上啊,月亮很美好,然后你看着我,觉得我好美丽。一下你就爱上了我,从此觉得终生要与我在一起。”我总是认为噶太是某个瞬间,一下子爱上我的。
但噶太并没有这么想过,“我没有一瞬间爱上过你,也没有和你看月亮,是某天在街上,太阳底下,我们都被晒得快晕死过去,可你在广场里说你没有男朋友,让我做你男朋友,我不答应,你就不让我离开。我是被太阳晒怕了。”
“那,为什么我们要到广场。”
“我怎么知道,怎么和你去的广场。”噶太并不想对这件事情探讨,他认为太阳下,或者月亮下,都是一样的。但我却认为不同。
我不知道是噶太出了问题,还是我出了问题,可我们还是走到一起,开始不温不热的恋爱。
十
站在上坡上,卡西开始懊悔,为什么要来这个雨村,根本没有土司庄园,也没有桂花,只是一个不理人的老家伙。但她还是气喘吁吁地跟在扎西老人的后面费力地爬着山路。
很多地方根本没有路的痕迹,太阳出来了,晃在头顶上,卡西觉得自己都快被晒得脱皮了,太阳高高地挂在天心,如同老人一样,那么远。
很快,扎西老人离卡西的距离越来越远,羊群也一样,他们在卡西的视线里翻越了一个小山包,就消失了。
卡西的倔脾气上来了,明晃晃的阳光下,她费力地爬着山路,偶尔,脚底的石头被她踩滑,咕噜噜就滚下山去了,卡西小心地向前走着。
山下的村庄越来越小,卡西在山上越爬越高,终于翻越了一个小山头时,他看到一抹绿色,这个山包里藏着一块绿地,绿地上还有个牛棚。羊群惬意地在草地上吃草,她看到扎西老人则在一个树下,安逸地烧起了火,火上,砖茶已经烧开了。老扎西的旁边还有个年轻人,老人从随身的包里拿出酥油、糌粑,看来老人每天都来这个放羊。
卡西走了过去,老人已经把酥油和盐巴放进一个小白瓷口缸,用一支筷子双手搓动着,那筷子很快就把茶水、酥油和盐巴搅合成白白的酥油茶。那筷子的头上有个小竹片,白色的香香的酥油茶就在老人的双手搓动中不停翻滚。卡西坐了半天,老扎西和年轻人都没和她说话,倒茶的时候,老扎西给卡西也放上了一个碗,卡西早就渴得嗓子都冒烟了,毫不客气地拿起碗就喝起了飘香的酥油茶。
卡西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她才发现,老扎西旁边的年轻人显得有点痴呆,卡西从来到这里开始,一直没听到年轻人说过一句话,老扎西也没说。
喝过茶,老扎西开始忙活了。在牛棚里,年轻人把早上挤到的牛奶都放在一个大木桶里,扎西老人走过去,开始用木棍搅拌牛奶,要提炼酥油和做酸奶渣呢。
扎西老人一上一下地搅拌着牛奶,一首好听的歌谣在他的嘴里轻轻流动,卡西听不出来扎西老人在唱什么,那歌谣随着扎西老人搅拌牛奶的节奏变换着,老人的眼帘也半闭着,卡西为这个场面感动着,她觉得扎西老人好像在哄一个婴儿一样搅拌着牛奶。
十一
曾经有次,我差点爱上噶太了。那天,噶太来歌舞团找我,我们两个在宿舍里百无聊赖地烤着电炉。
噶太的目光被我放在一个角落的手风琴所吸引,他想让我给他拉手风琴听听。平时说话大咧咧的噶太说,哎,我从来不懂音符,手风琴原来就是这个东西。
噶太是个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的藏族人,都说藏族人天生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可噶太的歌声,能把一个七度高音拉到小三,当然了,他也能把小三度唱到增七度或者减七度,就是不能在和谐的那个纯七度之间。
噶太并没有见到我给他表演乐器,来歌舞团工作以前,我在艺校里学过好多乐器,琵琶、钢琴、小提琴、架子鼓,还有手风琴,因为要配乐,所以我这段时间又开始练习手风琴。
我坐到床边,一本正经地对噶太说,我要演奏了哦,你不准喧哗。
噶太叼着一只烟,身子斜靠在门上,说:“你怎么还那么多讲究的。快点吧。”
一个小三和弦拉开了节奏,我把手风琴的风箱拉开了。“67171222112……”我弹起了《天使爱美丽》,这首我在学校里最喜欢演奏的曲目,音符在手风琴风箱的一拉一合中,从我的指尖流淌出来,我的身体也随着打起了节奏。
音乐演奏完毕,我歪着头笑着看噶太,不知道噶太什么时候把烟头灭了,认真而安静地看着我,他的眼睛里有种我平时看不到深沉。他站起走到我面前,认真地看了我三秒钟,然后低下头,轻吻了一下我的额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