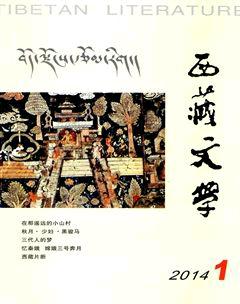秋月·少妇·黑骏马(短篇小说)
赵有年
一
群星拱簇着一弯残月缓缓探出了山头,山巅与星斗相连,惨淡的月光照映着茫茫的巴滩草原。
残月下,一顶黑帐篷里如隐如现地闪烁着一盏孤灯。
帐篷门前的那匹黑骏马蓄势待发,在焦急中等待着主人将要实行骑马扬鞭而去的使命。
刚嘎坐在帐篷门前,静默地张望着那轮冷冰冰的残月。朦胧的月色中,远山如黛,隐约可现,秋风扫地,黄草萧萧,显得一片凄凉。
他和心爱的姑娘只距一山之隔,由于两个部落之间的恩怨,阻断了他俩的浓浓情意,现在他们锦书难托,琴瑟之恨,寸心幽怨。
两地离愁,愁肠百转,那重压于心头的人间烦事,搅得他百思不得其解。
他喝了最后一碗奶茶,走出帐篷,骑上骏马扬长而去。
二
山那边,少妇琼吉刚打完酥油,盘腿坐在帐篷里的酥油灯下,开始挑灯绣起了刺绣。
她全神贯注地绣着一幅月夜鹊登枝头的刺绣,针在花布上飞快地穿梭着。
突然,一阵悠扬的笛声闯入她的耳际。她不禁打了个冷颤,一走神,绣花针狠狠地扎进了她纤细的指头上,一股鲜血顺着针眼流淌了出来。
她吮吸了一口鲜血,眼泪却从她那双楚楚动人的眼睛里滚落了下来。
于是,琼吉顿时失去了制作刺绣的兴致,收拾了针头线脑,就囫囵钻进了羊皮袄中。
寂静之夜,在寒夜中传来的阵阵笛声,仿佛是一把冰冷的匕首,在锥戳着她那颗伤痕累累的心。
她辗转反侧,夜不能寐,重压于心头的人间烦事,同样搅得她百思不得其解。
笛声的终端是使她那个爱恨交错人儿,可她觉得地远天阔,露冷风清,只好躺在黑暗中独自悲伤涕泣了。
三
黑骏马在黑夜里嘶鸣着,仿佛也是为主人那凄楚的笛声给弄得悲惨不已了。
黑骏马的嘶鸣声,止住了刚嘎的笛声。
此时,他已泣不成声了。
一阵低泣后,他喝了几口青稞酒,一股悲凉又一次漫上了他的心头。
唉!两地离愁,一尊芳酒,愁肠百转,泪洒西风。
每个深秋的夜晚,他从未间断过夜夜笛声传情的举动。
夜雾弥漫,山峦在茫茫大雾中消失;月色朦胧,草原被朦朦的月色吞没,那顶爱人安居的帐篷,更是云遮雾障,无迹可寻了。
此刻,他才收起骨笛,骑上黑骏马,随着黑骏马的一身凄凉的嘶鸣,返回到自己那顶孤零零的帐篷,孤枕而眠了。
四
不知过了多久,帐篷的天窗外射进了几缕月光,失眠的琼吉抬眼往天窗外望去时发现:在空中飘荡的断云中缠带着一轮残月,忽隐忽现地在断云层中慢慢西行。一种久谙离别之苦悠然袭击了少妇琼吉的心里。痛苦又一次锥痛了少妇琼吉忧伤的心。
百无聊赖中,那美丽的童年时光又闯入了她的记忆。
幼年中的琼吉是在无边的寂寥中度过的。
还好,离她家帐篷不远处坐落着德格大叔家的帐篷,德格大叔多少是个安慰。
角巴每天来找她玩。可两人也没有什么好玩的玩具,无非抓羊羔玩,追牛犊玩,再就缠着爷爷玩羊骨。
山那边倒有几家牧户,可自从她记事起爷爷就对她和角巴说,山那边居住的是贡布部落的后裔,是我们落加部落的世仇。她也从小就发现两个部落为草原闹矛盾,今年杀了那个部落的几个壮丁,明年又杀了这个部落的几个汉子。闹得鸡犬不宁,生死不可往来。山两边牧民之间的恩恩怨怨,闹得两方的人都提防着对方,彼此不敢接近。
有一天,琼吉和角巴又跑到离自家帐篷不远的山丘上,趴在草地上玩羊骨。
他俩各拿出数目相同的羊骨,争做头家的事而闹得不可开交时,突然传来一阵马的嘶鸣声。当他俩停止争执,循声望去时,发现山梁上出现了一个骑马的少年。少年用一种渴求的目光望着这对尽兴玩耍的小伙伴。
那马是一匹黑骏马。
其马毛色乌黑,如同披着一身黑色的锦缎;走起路来昂首扬蹄,平稳优雅;神色性情暴烈,桀骜不驯。
琼吉和角巴被那匹漂亮的黑骏马给吸引住了。他俩都带着羡慕的眼光端详那匹黑骏马以及骑在黑骏马上,穿着一身讲究的藏服,戴着红色狐皮毛的少年而望而却步时,德格大叔来到他俩的身旁,说:阿米嘎吱(宝贝),不要轻易相信山那边的人,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不要被假象所迷糊,他们可是一群卑鄙无耻的小人,毫无人道的恶魔,你们要提防着他们一点儿呀。
那少年也见到了德格大叔,惊慌而逃,从那座山丘上消失了。
从此,一种结交的欲望占居了琼吉和角巴幼小的心灵。
某天,趁大人不注意,他俩也骑着他俩的马(一匹青马,一匹绛红马。)趁机溜出牧场,向更远的草场奔驰而去,去寻找更多的朋友。也是去消遣,打发寂静的草原带给他们的寂寞。
爬上山头,他俩第一次见到了山脚下,广袤无垠的草场里,忽隐忽现,海市蜃楼一样隐没在碧绿的草丛中,升起袅袅炊烟的黑帐篷。
汪……汪……汪……
他俩骑马站在山头上,俯瞰着山脚下的牧场好长一阵后,不知是哪家的牧羊犬发现了他俩而狂吠了起来。
牧羊犬的吠声,引出了帐篷里的牧民,站在帐篷前仰望山顶,不久,几个黑影匆匆向山丘移动而来。
“琼吉,撤!”
角巴一提醒,琼吉就调转了马头,紧跟着角巴疾驶而去。
没走多远,后面几匹骑手紧随而来,仿佛是激流而至的洪流。
“抓住他俩,交给社长处置。”
“站住!两个穷小子。”
“穷小子,看你俩往哪里跑!”
几匹坐骑越追越近。
“琼吉,加速,跟上我。”
角巴催促琼吉走快点儿,可后面的尾随者近在咫尺。
“哈哈,抓住她,抓住那个女的,那个男的就自然会来救这姑娘的,我们就不费吹灰之力能抓到他。”
一个稍微大一点儿男孩高喊到。
“我抓住她了,我抓住她了!啊……”
就在有个毛头小子从他的坐骑跃上琼吉马背上的关头,响起了一声清脆的抛儿声,那个毛头小子从半空坠落在草滩上,传来狼嚎鬼叫般的哭喊声。
同时,一匹黑煤球一样的骏马横空而出,追上琼吉的马,一把把她抱到了他马背上。
“角巴,救我!”琼吉惊吓得大声向角巴呼救道。
“琼吉,我来了。”角巴刚调转马头,准备向众人疾驶而去。
“快走,不要吃了眼前亏。”那黑骏马的主人又拨转了角巴的纯青马,向草原深处疾驶而去。
“刚嘎,你这个叛徒,有种你永远别回贡布部落!”
黑骏马的主人,不理那些人,驾驭着黑骏马向草原深处疾驶而去。
后面,紧跟着载人的一匹纯青马和一匹不载人的绛红马。
从此,她又多了一个异性朋友。
她们骑着马玩山游水,度过了无数个春夏和秋冬。
她多么留恋那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啊
五
月光惨淡地照耀着荒芜的巴滩草原。
夜异常的宁静,除了一两声野狼的惨叫声,整个草原沉浸在无边的寂寥中。
弯月下的黑帐篷像一叶孤舟,在凄厉的秋风中飘摇着。
从黑帐篷的天窗里洒下一层淡淡的月光,照射在灶台上,“塔夸”中微弱的火苗在努力地舔着锅底,将息就息的样子。
土炕上的德格老两口还没有睡着,显然也听到了凄楚的牧笛声和黑骏马凄厉的嘶鸣声。
老俩口在被牛粪火烘烤炙热的土炕上辗转反侧了好长一阵后,德格大叔再也耐不住性子了。
“这个犊崽子,也忒有耐性了。都五年了,他一直这样折磨我们,也太欺负人了吧?”德格大叔极不耐烦地说。
“唉,我还挺喜欢他的执着!按理说,他算是个有良心的汉子,如果我是儿媳妇(琼吉),也愿意等待这样的男人。”嘉毛吉大婶叹息了一声后说。
“闭嘴!蠢货!你老糊涂了吧!他可是我们仇敌部落的后生呀?有仇不报非君子,我还没来及给我的儿子报仇呢,你已经打算把儿媳妇嫁给他的情敌,亏你说得出口!”嘉毛吉大婶的话彻底惹怒了德格大叔。
“冤冤相报何时了,何况你我都成一把老骨头了,就算有了报仇的机会,你还能端的起猎枪吗?女人如花,过了一季就少一季,我替琼吉难过呀!多么漂亮的姑娘啊!她的青春就这样荒废了。可怜啊,可怜!”嘉毛吉替琼吉惋惜道。
“世上男人千千万,她嫁谁不行非得等他。她如果嫁给刚嘎就等于背叛我们的儿子(角巴)。”德格气愤难平地说。
“如果没有那次纠纷,琼吉不一定嫁给角巴。再说,引起那次纠纷的不是刚嘎,恶霸贡布的儿子才是搅起那场纠纷的屎棍子,我想我们冤枉刚嘎了,我们不应该把屎盆子扣在刚嘎的头上啊!”嘉毛吉大婶有些焦躁了起来。
“你,魔鬼缠身了呀?今天怎么一反常态地向自己恨之入骨的仇家辩护起来了呢?”德格大叔猛然有些不了解自己的老伴了起来。
“恨归恨,可人活着不能黑白颠倒啊!佛说,心中装满着自己的看法与想法的人,永远听不见别人的心声。你这个顽固的家伙!”嘉毛吉大婶愤慨地说。
“你可不要犯糊涂了啊,是贡布部落的人杀死了我们的孩子和琼吉的父母的啊!这口气我咽不下去!再说,琼吉也不见得放下包袱去嫁给那个杀死自己父母仇人后裔刚嘎的。”德格大叔分辨道。
“唉,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唵嘛呢叭咪吽,愿佛指明我们一条明确的人生路途,不要我们这些可怜的人活在痛苦中吧!唵嘛呢叭咪吽……”嘉毛吉大婶默默祈祷起来。
帐篷外面,秋风开始肆虐了起来。
残月冷冷地凝望着苍茫的巴滩草原。
六
淡月笼沙,秋水低吟,面对着沉浸在凄寒中的巴滩草原的冷落,凄凉悲苦之情在刚嘎的心中油然而生。
酿成他和琼吉悲惨命运的那段往事又一次闯进了他的心间,痛苦再次吞噬刚嘎刚被酒精麻木过的心。
他不想闪躲,也无法闪躲往事袭来折磨他的灵魂,就让无缘的痛苦徜徉在他心间,任它啃噬、折磨和抽打他的灵魂。
那也是一个凄凉的秋季,经过了一个夏季漫长的相思苦的情侣见面后,尽诉衷肠,忘记了草场上的羊群。结果,琼吉的羊群翻过了自家草场的领域,闯进了贡布部落的草场。当他俩发现时已经酿成了无可挽回的后果,以恶霸贡布的儿子吉琼为首的贡布部落的人马奔上山头,欲把琼吉的羊群强行赶走。
这时,在牧场里干活的琼吉的阿爸阿妈等人(落加部落的后裔)发现后,也骑马赶来阻止,于是两个部落的后裔们再次发生冲突,在激烈的搏斗中琼吉的父母等躺倒在血泊中。瞬时,琼吉失去了双亲,变成了孤儿。他和琼吉的爱情之花瞬间被那场突如其来的秋霜给摧毁了。
琼吉失去双亲,德格夫妇收留了琼吉,琼吉经过一段时间的痛苦折磨后,悻然嫁给从小爱慕她的角巴。
从此,琼吉心里装着对贡布部落的仇恨,与角巴过着不淡不浓的夫妻生活。
不知过了多久,某天,角巴出去寻找走失的牛群时,遇上了恶霸贡布的儿子吉琼为首的贡布部落后裔的人,被他们活活打死后,绑在马背上驮回了家。
悲痛再一次侵蚀了落加部落,也笼罩在了琼吉的心灵,刚嘎再一次成了替罪羊,她们把杀害角巴的罪名怪在了刚嘎的头上,同时,他和琼吉之间再次加深了仇恨的沟壑。
月缺月圆,酷暑穿梭了好几个轮回,有些事情被岁月的轮盘磨灭了,唯独仇恨和相思交织在他和琼吉的心间无法抹去。
七
夜里不知什么时候下了一场薄雪,少妇琼吉起床时,巴滩草原已经是银装素裹了。
她顾不了寒雪带来的刺骨之冷,洗漱好后,携带着挤奶桶凝然走进牛群中,温顺地蹲在母牛胯下挤起了牛奶。
随着她纤细双手优美的节奏,洁白的奶汁就从母牛体内喷涌而出,哗哗哗地流进奶桶里。
微风带着馥郁的奶香吹来,把整个草原的早晨都深深地熏醉了。
这时,她听到了骏马的嘶鸣声,她从母牛胯下站起了,往草原深处看去时,发现一匹疾驶而行的黑骏马,她出神地凝望着黑骏马和骑在马背上的青年。
黑骏马像一块煤炭,在皑皑白雪上渐行渐远。
白雪中,少妇琼吉分外妖娆。
站在皑皑白雪中,少妇琼吉依然春情荡漾,蜂腰婀娜,袍红簇翠……
八
残月在晨曦中失去了光泽,像一弯羊脂玉佩,冷冷地挂在西山顶上,就要隐没的样子。
一片孤云在万里苍穹飘荡,没有一定的方向,没有相随的伴侣,渺不知南北地在巴滩草原的上空游荡着……
德格大叔在帐篷前做早祷时,琼吉已经打好了酥油茶,静候两位老人用餐。
“琼吉,昨晚又没有睡好觉吧?”
德格大叔未进帐之前,嘉毛吉大婶就把自己的想法说给琼吉听了。
“阿妈,你怎么这么说话呢?”琼吉有些不安地说。
“昨晚,那笛声弄得使我心肠憔悴啊!”嘉毛吉看了一眼琼吉,说,“都是女人,我也是从你的年纪里走过来的,这女人就像原野上的花,有季节的,过了那个季节她就会凋零的。我明白你的心思,放下包袱吧?人总不能活在仇恨中,或许,我们真冤枉刚嘎了。再说,恶汉吉琼也被公安审判了,也替亡者报仇了。活在仇恨中是痛苦的啊!明天又到你阿爸阿妈的祭日了,我们都到寺院给他们祭拜,从此,我们都放下包袱,你也该有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阿妈,我的心早已死了,我们就这样过下去吧?”
嘉毛吉的话,再一次勾起了琼吉内心的苦楚,她眼泪婆娑地看着嘉毛吉说。
“这不是你心里的话,你已经够苦的了,不要有太多的顾虑了。佛说,不宽恕众生,不原谅众生,是苦了你自己。”嘉毛吉耐心地劝解琼吉。
“阿妈,您不要逼我了,难道我哪里做得不对吗?他是杀死我父母和丈夫的凶手,你让我去嫁给他吗?”琼吉哭泣道。
“琼吉,我不反对你嫁人,可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嫁给刚嘎,你为了自己的幸福,不会不顾你阿爸阿妈的仇恨吧?”
这时,德格大叔进了帐篷,唱反调道。
“琼吉,不要听他的。或许我们对刚嘎的成见太深了,明天我陪你们一起去寺院亲自听听曲加活佛的话,他是整个事件的知情者,对这件事他最有发言权。琼吉,不要太执着了,今日的执著,会造成明日的后悔啊。”嘉毛吉大婶挖了一眼德格大叔后说。
琼吉再也听不下去了,她痛哭着跑到帐篷外面去了。
帐篷里传来嘉毛吉大婶和德格大叔的吵架声……
九
那层薄雪很脆弱,一碰触到阳光就融化了,潮气变成了缕缕雾气,巴滩草原被雾气给笼罩了,袅袅腾腾地升上了天空,聚集在半山腰里,仿佛给远山系了一条洁白的玉带。
残月在被雪花覆盖的山顶上徘徊了一阵后,隐没在大山背后了。
羊群在草原上悠闲地啃噬着秋草。
琼吉牵着马儿,跟在羊群后面放声歌唱,满腹的惆怅使她透不过气来,只能用歌声来排遣内心的痛苦了。
苍茫的原野,
凉意还未尽,
绿色又渐渐盛满了你的眼睛,
故乡的温馨还是这样的浓,
勤劳的人啊,
你又要远行。
萧瑟的秋意淡淡的月光,
依然不见你回到故乡,
点点的星光为谁闪烁,
马背上的人啊,
你可否思念故乡。
借酒消愁愁更愁,用刀断水水更流。
她生活在千年不变的巴滩草原上,触景生情,历历往事不断涌进她稚嫩的心际。
她放了那匹骏马,平展展地躺在苍茫的秋草中,任无情的愁绪来撞击她的心田……
记得那也是个深秋的夜晚。
刚从夏季草场迁移到秋季草场后,琼吉、角巴和刚嘎他们久别重逢,难免有些忘形,就疯狂地嬉戏了起来。
夜深人静,刚嘎和角巴离去后,她阿妈就把她叫到外面谈心时,告诉了她一个使她意想不到的事情。
一轮弯月挂在天幕上,像佳人一抹淡淡的眉痕,天上新月穿越,月下秋草摇曳,把斑驳的光影轻轻地洒在草丛之间,那清新、柔和的光像秋水在流动,仿佛要冲破笼罩大地的暮霭。
在草滩上,琼吉躺在阿妈的怀里,望着那轮弯月在出神。阿妈爱抚着琼吉那头秀美的长发说:“傻丫头,这么大个姑娘家了,还没有一个整形,你已经有麻烦了!”
“莫名其妙,我有什么麻烦呀?莫非你嫌弃我了?”琼吉望着弯月没心没肺地说。
“唉,刚嘎和角巴都爱上你了。”阿妈忧心忡忡地说。
“当然,他俩都是和我一起长大的哥儿们啊,他们不爱我爱谁呀?”琼吉依然望着弯月回答。
“傻丫头,本来呀藤绕树,凤求凰是件好事,可是两个男子同时爱上一个女子,就会给那个女子带来痛苦的。”
“你说什么呢?我们是哥们儿,他俩是我的哥哥和弟弟,说什么爱呀恨的,兄妹之间能产生男女之情吗?”琼吉听出阿妈的意思,腾地翻起身辩论道。
“说你傻吧,你还不信,你这么认为,可他俩不这么认为呀。阿妈是过来人,我看出了他俩看你的目光中带着的那股火。我怕这火会烧着你。”阿妈耐心地劝解道。
“不可以,我只做他俩的姐姐或妹妹,我不允许他俩心存恶意。”琼吉强词夺理道。
“但愿事情按你的想象发展,怕就怕事与愿违,在你身上发生什么祸端。唵嘛呢叭咪吽,愿佛保佑我女儿一生辛福。”阿妈担忧地祈祷道。
“阿妈,您放心吧,我一定会幸福的。”琼吉信心十足地说。
“好,阿妈我相信你。”
于是,她俩都不说话了。阿妈轻吟着一首古老的歌谣,抚弄着琼吉秀美的头发。琼吉凝望着那轮秋月,内心交织着回忆与希望,时而明快,时而暗淡,沉郁顿挫,低回掩抑,耐人寻味。
后来,事情果然向阿妈所说的那样发展了。
刚嘎和角巴明争暗斗,轮番向琼吉献起了殷切。于是,琼吉就说出了她只愿做他俩的姐姐或妹妹,不做情人或妻子的决定。
可没过多久,她自己却陷进了恋爱的泥沼里不能自拔了,她深深地爱上了刚嘎。为了不伤害到角巴,她把爱情深藏在内心深处,可爱情却像海的波涛,层层叠叠,翻卷着浪花,在她的胸腔里翻滚。
直到来年夏季的赛马会上,琼吉发现刚嘎试图追求别的女子时,她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翻滚的波浪,向刚嘎倾诉衷肠。刚嘎当然求之不得,于是就向琼吉求爱,俩人迅速陷进了爱情的温柔乡,恩恩爱爱,卿卿我我了起来。
角巴当然免不了心生凄楚,可他不嫉妒刚嘎,在舔舐伤口的同时,他也默默祈祷刚嘎和琼吉恩爱美满,厮守终生。当角巴打算知难而退的时候,事情却发生了转变,两个部落后裔之间的恩恩怨怨升华,发生了一场惨案。惨案中琼吉失去了双亲,刚嘎和她反目成仇,那段令人羡慕的爱情像一块陨石,从他俩的青春中陨落了。
无耐之际,琼吉做了角巴的妻子。可好景不长,角巴也丧命与贡布部落的人手中。
从此,琼吉的心里对刚嘎爱恨交织了起来。
可每年深秋残月中传来的阵阵笛声,暗暗揭起琼吉对刚嘎的思念。琼吉对刚嘎和角巴思念的诚意,化作帐中一夜的幽梦,无奈醒后仍是水隔绝,天遮断,不见其形影。
十
远山连绵起伏,横亘千里。
起初,淡淡的薄云漂浮在层峦叠嶂的山峰之间。不一会儿云随风飘,迅速向巴滩草原深处蔓延。顿时,巴滩草原的上空云雾密布,一场猛烈的暴雨笼罩在了巴滩草原的上空。
沉浸在痛苦回忆中的琼吉还全然不知这风卷云滚的一幕,依然躺在草甸上,处在半醒半梦中,回忆着那场血淋淋的残酷往事。
另一场危机也悄然向她逼近。
一群四处觅食的草原狼,也从山岭上下来,悄然向琼吉的羊群挺近。
咔嚓嚓……
一声炸雷把处在深度痛苦中的琼吉给惊醒了,她一骨碌丛草地上翻起来,揉着睡意惺忪的眼睛向远处望去时,远山一带的秋雨呈青色向草原深处袭来。
那雨势很猛烈,几只悠然在天空盘旋的雄鹰来不及躲避而被击落,把牧草覆盖的原野一瞬间打得烟尘滚滚,她的羊群被暴雨的长鞭抽打着惊慌失措中四处躲避。情急之中琼吉到处追寻自己的羊群。
这混乱的巨变给狼群带来了可乘之机,都倒背着耳朵,冒着一缕缕雨幕,向琼吉的羊群出击。
雨幕中,那些机警的生灵像一枚枚离弦的箭,向一只只绵羊直飞而去。
少妇琼吉在不可收拾的潮水中被携裹,她大喊大叫,却毫无声响,她的喊声被炸雷和雨声给淹没了。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她看到了一幕动人的场景。
在一匹背上骑着牧人的黑骏马的带领下,一群不肯安分的生灵从无数谷口、山坡涌出来山洪奔泻似地在巴滩草原上汇聚后,嘶鸣着、喧叫着、纷乱着向狼群奔赴而去。它们追赶着、撕咬着、踩踏着狼群,狼群躲闪着、吆喝着、翻滚着四处逃窜。
几分钟后,马群消失,暴雨停歇,草原一下子静了下来。
处在错愕中的琼吉醒悟后,四处寻找惊慌失措中跑散的羊群,等把所有的绵羊都找到后,才想起了刚才骑马相救的黑骏马和牧人。
她四下里寻找马群和骑马驰骋的牧人时,发现那人骑着那匹黑骏马,牵着琼吉的绛红马,从遥远的谷口奔袭出来,匆匆向她驰骋而来。
走近后,琼吉才发现,那牧人不是别人,而是使她爱恨交错的刚嘎。
“怎么是你呀?为什么来关我的死活?你不是盼我们死绝而后快的吗?别拿这种伎俩来挣得我对你的宽恕!”琼吉不但不感激他,反而指责起他来。
“唉……”刚嘎不说什么,只是深深地叹息了一声后,坐在一块干燥的石头上,猛吸起纸烟来。
“你叹息什么呀?难不成我们冤枉你了不行?雪鸡洁白尾巴黑,老熊乌黑胸口白。我们冤枉你了,总会有澄清的一天,你能澄清自己的罪行吗?”琼吉咄咄逼人地质问道。
“河谷平原的长短,不走三步不明;大河流水的深浅,不到河中不知。你没有澄清黑白的诚心,怎么能解开谜团呢?”眼泪不听使唤地从他的眼睛中簌簌滚落下来,“这些年两边的人都对立我,我成了难鸣的孤雁,还背着杀死情夫的罪名,你知道我有多痛苦吗?”
“我亲眼看见你拖着角巴的尸体回来的呀?就是你怀恨在心杀死了角巴,你是凶手。凶手!”琼吉歇斯底里地怒吼道。
刚嘎不说话,只是静静地抽着烟。
在那两个旧日里恩爱有加的男女互相指责不休的时候,那两匹获得自由的骏马相互追逐着驰骋嬉戏了一阵后,这时已在近处缓缓停住,站在灿烂的夕阳中,低垂着脖颈,一副歉疚地想说“对不起”的神态,相互抚慰着。
过来一阵后,刚嘎打算要离开了。他打了个响亮的口哨后,黑骏马咴咴地嘶鸣着向主人跑来。
刚嘎翻身骑上马背,欲要挥鞭策马扬长而去。
“假如你想澄清黑白,请找曲加活佛吧,他会给你准确的答案。我一直在等待你做我的新娘,直到海枯石烂。再见!”
雄浑的马蹄声在大地上奏出嘚嘚的鼓声,渐行渐远了。
琼吉望着刚嘎渐行渐远的背影,失声痛哭了起来……
十一
枕簟生凉,帐内乍冷,秋的凉意已渐渐袭来。
凄清之夜,刚嘎满怀愁绪依然无法入睡,要忘却前愁,却无以为计,萦怀缭绕,纠缠缱绻。于是,他骑马来到附近的山梁上,对着少妇琼吉家的帐篷深情地吹奏起了笛子。
雨散云收,天空洁净如洗。一弯残月照在巴滩草原上,月冷星稀,微寒侵衣。
阵阵催人断肠的笛声,使得他追忆起往昔旖旎缱绻的一段柔情。
他和琼吉感情笃深时,刚嘎骑马带琼吉来到圣湖边上玩耍,一番柔情过后,刚嘎坐在草坪上吹奏起一曲《牧民新歌》的笛曲。琼吉即兴起舞,只见她长袖飘飘,翩翩起舞。那婀娜的舞姿、含情的笑靥、婉转的歌喉,都给迷恋中的刚嘎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而在这霜落之秋,刚嘎与恋人分手,自有一份难遣的情怀,尤其在这凄凉的秋夜,追怀往昔的恋情,更加重刚嘎今夜情思凄苦的惆怅……
十二
琼迈寺依山傍水而建。风景秀丽、奇峰重叠的环境中,山前山后林木茂盛,苍翠秀丽。
德格大叔骑着马,赶着牛车载着少妇琼吉和嘉毛吉大婶向琼迈寺缓缓驶来。
山谷中潺潺小溪,百鸟争鸣,与寺院学僧的朗朗诵经声浑为一体。
琼吉突然听到一阵马的嘶鸣声,抬头仰望时,发现那匹黑骏马从山梁上疾驶而去。
到了寺院门口,德格大叔把骏马和牦牛拴在寺院门口的拴马桩上,带上从镇上买来的哈达、酥油和供品,领着嘉毛吉和琼吉进了寺院。
院落宁静,殿前石头铺着庭院,石缝中生着淡淡的青草,好似空城。
进了寺院的大门,德格大叔径直走到煨桑台前,把炒面、柏香枝叶、茶叶等煨桑物品投进了桑池中,等煨桑物变成一股浓烟之后,他就边抛洒神马,边诵读着真言,围着煨桑台转了起来。
之后,德格大叔和嘉毛吉大婶口中喃喃诵读六字真言,迈着蹒跚的脚步,围着大殿或玛尼石堆一圈又一圈地转着。拨弄的那一排排的转经筒一个劲儿地转动。
转完大殿和经堂,德格大叔就带着嘉毛吉大婶和琼吉就来到曲加活佛的寮房门口,跪在寮房门的羊皮毡铺上,一个接一个地磕起了等身长头。
小沙弥推门进来说:“活佛,巴滩草原的德格大叔在门口等候,您看怎么办?”
“唵嘛呢叭咪吽,化解那份恩怨的时机终于来到了,你去把他们请进来吧。”曲嘉活佛思考了一下后说,停止了诵经声并收拾起经书。
小沙尼出去不久,德格大叔他们就推门进来了。
见到曲嘉活佛,他们立刻摘下头上的帽子和头巾,身子向前一扑,跪在曲嘉活佛面前,叩起了头。
“唉,这不是德格大叔吗?你们终于来找我了,我已经等你们五年了。”曲嘉活佛上前扶起他,关切地说。
“活佛,莫非你已经知道我们的来意了。”德格大叔疑惑地问。
“嗯。佛不渡无缘的人,看来我们还是有缘分的啊!”曲加活佛慈爱地说。
“活佛,这件事同样折磨了我们五年啊!”德格大叔眼泪婆娑地说。
“原谅别人,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以便回旋。也难为你了,这事你并不知情,再加上你们的心被仇恨占据,很难看清事情的真相。佛说,正人行邪法,邪法亦正,邪人行正法,正法亦邪,一切唯心造。”曲加活佛向他们解惑道。
“活佛,请把真想告诉我们吧?”德格大叔哀求道。
“你们确实冤枉刚嘎了。你们也听说了吉琼坐牢的事吧?吉琼确实为你们家儿子事坐的牢,可原告不是你们,而是被你们恨之入骨的刚嘎。”活佛缓缓道来,“对于角巴的死,刚嘎内心的痛苦不减你们啊,他一直视角巴为自己的亲兄弟,出事那天刚嘎在事发现场发现角巴的尸体,把他拖回去的。可当初你们因部落之间的恩怨仇视刚嘎,他又害怕你们伤害到他,就把马牵到你们家帐篷附近放马进你们家牧场的。唉,私情乃是为一切苦海的根源。可话又说回来,谁能闯出情网呢?所以,你们不必和因果争吵,因果从来就不会误人。你们也不必和命运争吵,命运它是最公平的审判官。”
“怎么会这样呢?”嘉毛吉大婶失声痛哭道。
“回去吧,真相就是这样的。放下包袱吧!当你用烦恼心来面对事物时,你会觉得一切都是业障,世界也会变得丑陋可恨。”
说完话,曲加活佛就到经堂里诵经去了。
德格大叔他们再三叩拜之后,也离开了寺院。
十三
时当深秋,阴云连绵,昏暝的薄暮笼罩着巴滩草原。
少妇琼吉从寺院里出来后,思绪更加纷乱,她支走德格大叔夫妇后,独自一人来到森林边一块宁静的地方放声大哭了起来。
当她发泄了一阵芜杂的愁绪后,收起激动的情绪时,眼前又展现了荒芜的深秋景象。她伫立在茫茫的大草原上,承受着无边的冷清,忽然长空雁叫,举目远望,唯见暮云合璧,不见雁鸿只影。无边的孤独又向她内心卷来。
不知什么时候了,一阵阵野狼凄惨的嚎叫声隐约从遥远的荒山中传来。
于是,琼吉一刻也不能耽搁,疾步向家赶去。
当她走到凄迷的芦苇荡附近时,突然传来一阵马的嘶鸣声,随后,刚嘎骑着黑骏马出现在了她的眼前。
“刚嘎……”
当刚嘎从马背上翻下身,缓缓向她走来时,琼吉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疾步上前扑进了刚嘎早已张开的怀抱里。泪水打湿了恋人的脸颊。
俩人以干柴烈火之势紧抱着对方的躯体,狂吻着、翻滚着进了浓密的芦苇荡中。
芦花花白,茫茫一片,在秋风中摇晃飘荡……
责任编辑:邵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