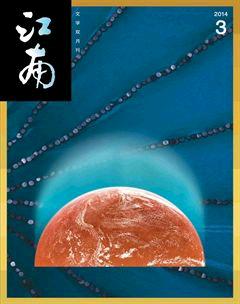刀臀
路内
每当我想到自己的十七岁,除了大飞、花裤子、飞机头这几个亲密混蛋之外,除了那些姑娘之外,还有一个人总是会被记起,那就是刀把五。我之所以记得他,并不是因为和他有感情,也不是因为他欠了我的钱,而是他傻。这辈子我遇到的傻矬够多了,他们全部加起来,晒一晒榨成汁,其浓度还是比不上刀把五。
他一直以为自己的绰号是“刀疤五”,出去泡女孩,他会叮嘱我们一定要喊他的绰号。因为这个傻瓜的学名非常土,土得我都不想说,一说出来就会让女孩们笑翻。他喜欢这个绰号,但他并不知道,“刀把五”是个围棋术语,它代表着一种死棋,会被对手点死的那种。
最初只有一条刀疤,在他手背上,他喜欢这条刀疤就像可可喜欢她的珊瑚手串。他对我们吹嘘说,这条刀疤是他初中二年级时,在一起斗殴中留下的纪念品,对手是一个成年的老流氓,他虽然没有打赢,但也把老流氓的鼻子打破了。他还说,老流氓拿出了一把匕首,企图割开他的颈部大动脉,他用手挡了一下,如果不是这一下他就会死掉,动脉里的血一直喷到屋顶上去。
每当他讲起这一刀的时候,我们都很害怕。我们怕挨刀子,虽然我们是技校生,每天在外面惹是生非像十三太保横练一样刀枪不入,但这只是一种猜测,一种恶意的幻觉。我们也是凡人,练好腹肌是为了对付女孩,而不是刀子。
而我们的刀把五,他不太一样,他真的不怕。他说自己是个嗜血的男人,喜欢身上有疤。有一次他和大飞在教室里吵了起来,他一拳打碎了窗玻璃,大飞早就跳到窗台上去了,像壁虎那样打算往天花板上爬。刀把五说:“大飞,我要杀了你!”举着受伤的右拳,那上面全是他自己的血,他舔了一口。大飞彻底认输,大喊:“把这个疯子拉走拉走!”
第一个学期体育课,跑八百米,刀把五跑了全班倒数第一。我们班四十个男生,连最孱弱的昊逼和小癞都赢了他。幸亏没有女生,否则他会输得更难看。后来我们知道刀把五是个平脚底,而且他腿短,这让我们笑了很久。嗜血的男人,是他妈残疾。尽管他举着那只有疤的手,在高年级女生那儿晃悠,表示他也是个可以依赖的男人,但是他腿短,腿短腿短腿短。谁会喜欢一个腿短的杀人狂呢?
我们最钟爱的学姐可可,她属于另一个小集团,她不太和我们玩。这完全可以理解,她进化工技校,首先被高年级的男生玩一轮,然后这帮人毕业了,她被本年级的男生玩一轮,本来没我们这一届什么事,但是上帝作证,我们这届没一个女生,四十个男人啊,他妈的每到下课时,女厕所冷冷清清的,男厕所里挤满了人。这正常吗?我们泡可可简直天经地义,不然我们去泡女老师好了。
轮到我们手里,可可已经被玩过三轮了。大飞十分看不上可可,说她是破鞋。为了这句话,刀把五又要和他拼命。我也觉得这么说可可不太好,在我看来她是个骄傲中带有温柔的调皮小姐姐,破鞋这种称谓太过时了,况且大飞并没有泡上她呢。
她那串珊瑚手串是红色的,在她的手腕上,冷不丁看上去像血痕,以为她割脉了。她并不经常戴,只有在心情很好的日子里,它才会出现一下。如果是夏天,她穿着短袖连衣裙,它会显得非常醒目,让女人发狂。如果不是夏天,她穿着长袖的衣服,它会若隐若现,让男人发痴。有一次我们在一起玩,我想摸一下手串,她竟然急了,要抽我。这时刀把五跳了过来,揪住我脖子警告道:“记住,永远不要染指可可的手串。”
我去他妈的,他竟然用了“染指”这个词。
可可说:“刀把五,过来,我给你摸一下。”
大飞阴阳怪气地说:“摸哪儿呀?”
于是刀把五又冲过去和大飞打了起来。我不得不说,虽然刀把五是个满嘴脏话、四肢发达的混蛋,但他对可可是真心的,奉为女神一样。后来大飞说,他妈的,什么女神,最多是个手淫女神吧?这话要是让刀把五知道了,大飞真的会死掉。
我一直记得轻工职校和我们班之间发生的那场斗殴,就是因为我们在街上看到两个该校的学生调戏可可。为了拯救她,为了让她知道自己已经轮到我们手里,我们全都扑了上去,企图打扁那两个倒霉蛋。但是我们还没来得及动手,刀把五已经抡起砖头,把其中一个打得满脸开花,并且让另一个跪在可可面前,用欧洲绅士的方式道歉。可可吓疯了,说这要闯大祸。第二天一百多个人冲进我们学校,见一个打一个,凡是不走运的都被揍了。
刀把五也被揍了,他满脸是伤,挨了一个处分。然后他放出话来,要找两百个人去踏平轻工职校。那个时候,可可已经不打算和他有任何瓜葛了。
“他到底是什么人?神经病吗?”可可问。
“他就是这样的,内分泌失常,控制不住自己。”飞机头说,“他以为自己是个英雄。”
“他会给我惹大麻烦的。”可可嚷道,“他说为了我他连大出血死掉都不怕!”
飞机头从来不信这种话,飞机头说:“嘁,我只见过大出血死掉的女人。”
可可走了。我们都不以为然,觉得刀把五坏了事,反而是大飞说:“刀把五固然是个傻叉,但他毕竟为了可可挨了一顿打,如果没有我们救可可,她在街上就被人摸了胸,现在反过来说刀把五是神经病。我觉得这个女人才是个神经病。我对她失望极了。”
后来刀把五也没找到两百个人,他狂暴起来一个能顶两百个,他为什么不独自冲到轻工职校,单挑所有人,然后大出血死掉?这样可可就会永远记得他。这样他就活在可可心里,永远十七岁,或者变成她珊瑚手串上的一粒珠子,永远血红色。
在狂暴或倒霉的日子里也会有风平浪静的时刻,有那么几个月,周围既没有暴徒也没有女孩,我们就只能打打麻将,聊以度日。打麻将的时候我们会谈起闹闹啊、冰冰啊、闷闷啊,这些女孩,但我们不谈可可,免得刀把五发狂。
打麻将我们通常都在大飞家里,后来有一天,刀把五邀请我们去他家。其实他不太会玩麻将,他连电子游戏都搞不来,任何玩的东西他都不太擅长,除了玩命。为了照顾他的自尊心,我们还是去了。
在他家里,我们遇到了他的爸爸,一位钳工,胳膊爆粗,长了个菜刀头。我们私下里就喊他菜刀头。菜刀头很热情,不但招呼我们开桌玩麻将,还给我们一人一根红塔山。他也不会打麻将,在一边看着,感受到自己的儿子很有号召力,他也很得意。后来发现我们是真的来钱的,他生气了,很严肃地告诉我们:“青少年不能赌博!”
“青少年不能干的事情多啦,也不能抽烟啊。”我说。
菜刀头说:“抽烟嘛,你们迟早都得学会的。但赌博是不允许的,就算你们结了婚,你们的女人也不会同意的。”
我们就说:“叔叔,行了,我们不来钱了,随便玩玩。”
菜刀头说:“你们要学好。”
我们说:“是的是的叔叔。”
刀把五出去买啤酒,我们就一边打麻将,一边和菜刀头谈论着青少年道德品质的问题。我也搞不清菜刀头的观点,一会儿他怂恿我们抽烟,一会儿他说打架是流氓行为,一会儿他又说如果刀把五在外面为非作歹,他就打死这个独养儿子。我们越听越不明白,后来我们都认为,刀把五的神经质是从菜刀头那儿遗传的。
我们说起了刀把五手上的刀疤,一方面是夸奖他勇猛不怕死,另一方面也提醒一下菜刀头,他儿子并不是什么善类。谁知道菜刀头大笑起来。
“那一刀是我砍的!”
“什么?”我们一起大喊起来。
菜刀头说:“他念初中的时候,有一天旷课,我抡起菜刀砍在他手上。就这样喽。”
飞机头摇头说:“我从来没听说过老爸用菜刀砍儿子的。”
菜刀头说:“那次我气坏了。中学生是不可以旷课的,对吗?他念小学的时候成绩很好,我本来以为他能考大学的。可是他旷课,只考上了化工技校,以后他也会是个钳工。”
大飞说:“你现在还提小学时候的事情干吗呢?我小学时候还是班干部呢。我们所有的人,将来都会是钳工。”
这时刀把五回来了,他抱着一箱啤酒,听见了菜刀头的埋怨。他放下啤酒走过来,隔着麻将桌瞪着菜刀头。菜刀头浑然不觉。我说:“原来你手上一刀是你爸砍的,你骗我们不要紧,怎么能骗可可呢?可可是你最欣赏的女人啊。”这时大飞站了起来,很识趣地退到一边。我一看刀把五的脸色,也赶紧往后面退。刀把五已经扑向菜刀头,隔着麻将桌,骂了两百多声操你妈。菜刀头大怒,抡起凳子照着刀把五脑袋上乱打。麻将像焰火一样四处溅开,我们一会儿劝刀把五,一会儿劝菜刀头,后来他们一直打到了阳台上。很显然,刀把五长大了,他完全可以对付菜刀头。我们退到后面看热闹,直到刀把五真的把菜刀头揍趴下,飞机头才说:“我从来没见过儿子敢这么打爸爸的。”
糗事传千里,而且是一日之间。每个人都知道,刀把五的刀疤,是他爸爸砍的。可可坐在儿童乐园的木马上,吃着冰淇淋,笑得前仰后合。可可说:“你们这个年纪的小男孩哪,最爱吹牛皮。”
刀把五背着书包来上学,看到无数异样的、嘲笑的目光,他什么都没说。这次他不打算和任何人打架,也找不到人可打。他抚摸着手背上的刀疤,坐在窗口喃喃地说:“我会让你们知道厉害的。”
于是可可继续笑,笑得从木马上掉了下来。
两个月后,有四个女流氓来到化工技校门口,她们也吃着冰淇淋,她们中间有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好看的难看的。好死不死,可可戴着她的珊瑚手串,背着书包上学,在离学校五十米的一条窄巷里遇到了四个女流氓。那些人揪住她,问:“你就是可可?”
可可说:“我不是。”
那四个女流氓说:“放屁,你都戴着红珊瑚手串了,你还不是可可?”她们一人给了可可一个耳光,然后从她手腕上撸下了手串,扬长而去。
我们看到可可的时候她已经哭得快要断气,她像个念幼儿园的小女孩,蹲在地上发抖,说起话来两只手连同肩膀一起疯狂甩动。
“她们抢走了我的手串!”
飞机头说:“她们就是冲着你的手串来的。”
可可说:“我认识其中一个人,她就是纺织职校的司马玲!”
一听司马玲我们全都噤声了。这是一九九一年最让人胆寒的名字,她的爸爸被判了死刑,她的哥哥是劳改释放分子,她身后的男人有一个加强连,全是流氓,战斗力超过了海豹特种部队。她带两个女生冲进化工技校就足以踏平我们所有人,因为我们学校最狠的那个大哥,是司马玲的忠实拥护者。我们从地上扶起可可,安慰了很久,她总算不哭了,但她提出了很过分的要求。
“你们帮我去把手串抢回来。”
我们面面相觑。大飞头说:“如果在其他女人那儿,我能给你抢回来。如果是司马玲……”
飞机头说:“我不敢。”
我说:“我也不敢。”
花裤子说:“报警吧。”
可可说:“你们这群怂逼。如果刀把五在就好了。”
刀把五不在。那阵子菜刀头在工厂里出了点事故,行车上有一个吊件飞下来,砸中了他,把个菜刀头砸成了锅铲头,他颅内积水,快要死了。刀把五天天在医院照顾他呢。
一九九一年那会儿,我们有一个奇怪的规矩,无论发生什么事件,只要不是强奸杀人烧房子,就不能随便报警。因为报警就意味着你退出了江湖,以后你最好参加高考,去做一个文静的大学生。更何况,哪个派出所会为了一串珊瑚手串而出警呢?除非所长是你爸爸。我们围着可可,商量了很久,最后她没了耐心,把我们一个一个痛骂过来,说要找她的同班男生去解决问题。我们表示同意,那些男人比我们大一岁,他们的战斗力会稍强些,但他们敢不敢去扒司马玲的皮,我们也觉得不那么乐观。
为了这串手串,我和飞机头去了一趟旅游品市场,那儿有大量的珊瑚工艺品。我们看到了大量的白珊瑚,有的做成假山,有的做成笔架,但我们没有找到红珊瑚,也没有发现手串。店主说,这种东西还蛮少见的,可能是港台过来的货色,就算有,你们也买不起。我想想也对,要是满大街都能买到,司马玲这种大佬又何必来抢可可呢?
我和飞机头郁郁寡欢地往回走。我觉得我们真的很爱可可,虽然没法为她抢回手串,但愿意出钱给她买一条,也算尽心了。我们顺路去了纺织职校,在那儿看到了司马玲,她独自坐在操场的司令台边,风吹着她的长发,她显得沉静而又优雅,完全不像是个女煞星。那串红珊瑚手串,那么醒目地,挂在她手腕上,非常耀眼。我们要是冲过去给她一砖头,就能抢回手串,赢得可可的芳心,但不能这么干。司马玲也很美丽,她像可可一样美,我们不能打一个美丽的女孩。
刀把五出现了,他手臂上戴着黑纱。菜刀头死了。
“节哀。”我们说。
刀把五说:“以后没人管我了。”然后他就知道了可可的事情,他说:“这事儿先放一放。”
我们表示理解,说:“是的,你别管了。你爸刚死。”
我看不出刀把五有什么哀痛的,他像往常一样上学下学,阴着脸,摆出很酷的样子供人观赏。花裤子说,刀把五的沉默说明他还是很哀痛的。但大飞说,刀把五从那次打麻将以后就一直沉默。
可可来找刀把五,当着他的面把我们几个都损了一遍:大飞是怂包,飞机头是怂包,花裤子是怂包,路小路是怂包。说得我们无地自容。刀把五笑了笑,笑得很残酷,说:“我知道了。”然后他就走了。
可可说:“刀把五也是怂包。”
红珊瑚手串事件并没有结束。可可快要过生日了,她筹备已久的生日派对,届时她要穿上最漂亮的衣服,配她的手串。可可找了她班上一个蛮威风的男生,绰号叫老虎,是她的追求者,单枪匹马跑到纺织职校去交涉。老虎说,可可愿意用一百块钱买回手串,另外再送给司马玲一串珍珠项链。司马玲给了老虎一脚,又拍拍他年纪轻轻就胡子拉碴的脸蛋,说:“明天陪我去看电影吧。”就这样,连他妈的老虎都被司马玲抢走了。
过了一个星期,可可那个惨淡的生日派对在一家小舞厅里搞起来了,很多人都没来。舞厅破旧不堪,球形激光灯已经不转了,卡拉OK里都是些过时的老歌。可可要求我们每个人带三瓶啤酒,她以为我们班会去上最起码二十个人,可是只有我和飞机头到场。我们喝着自己买的啤酒,看着可可逐渐发绿的脸,这时,刀把五来了。
他从裤兜里掏出了红珊瑚手串,对可可说:“我帮你抢回来了。”
他是这么干的:下午溜进了纺织职校,认准了司马玲,然后缩在角落里等着她落单。黄昏时她果然落单了,像我们上次所见那样,独自来到操场上吹风。这时刀把五走了过去,吹风的司马玲很美丽,但他一点没有怜香惜玉,一把叉住她的脖子,从她手腕上撸下了红珊瑚手串。司马玲挣扎了一下,刀把五揪住她的头发,把她放倒在地,然后撒腿狂奔,越过围墙,连自行车都没敢回去拿,一直跑到了舞厅。
我们看着手串,等着可可伸手去拿,给予刀把五最大的奖励,也许会吻他一下。可是可可比我们想象得更聪明,她说:“完了,你死定了。”这时从舞厅的前门后门各涌进来七八个男人,他们揪住了刀把五,暴打一顿之后把他按在桌子上,他直接趴在了可可的生日蛋糕上。其中一个男人拔出一把弹簧刀,像切蛋糕那样插进了刀把五的左臀。
那天我只记得刀把五的惨叫,以及可可的尖叫。等到这些面容模糊的男人消失之后,刀把五还趴在蛋糕上,可可的叫声还没有停下来:“刀把五,你把我的生日派对搞砸了!”
红珊瑚手串后来消失了,既没有归可可,也没有归司马玲,它在混战中不知去向。也许是被某个混蛋顺走了,而它确实也不再重要。
那时我们谈论过各种刀法。我知道有人被一刀捅穿肚子之类的故事,那太凶残,更多的时候,故事是温情而令人发笑的,比如某个倒霉蛋在打架的时候被人捅了屁股。你知道,那些擅长使刀的人,他们并不会愿意为了哪个无名小卒就把自己搞成杀人犯,他们只捅屁股就够了,有时捅屁股也会闹出人命,比如不小心挑穿了股动脉——这没办法,毕竟是流氓,不是外科医生。
刀把五没死,他屁股上插着刀子一直送到了第二人民医院。医生问怎么回事,我们说他不小心坐到了刀子上。医生说,呸,我不知道这是被人捅的吗?手术以后,刀把五坚持让医生把弹簧刀还给他,自此,弹簧刀就一直在他书包里了。
化工技校89级维修班最耀眼的明星、煞星、丧门星就此诞生,他就是刀把五,他身上拥有实打实的两条刀疤,都很吓人。他爸爸砍的那条在手上,另一条则因在隐秘的位置,不太好拿出来示人。在特定的时刻,比如我们谈到可可,他仍然会露出一种奇怪的神色,仿佛骄傲,仿佛忧伤,然后举起他的手,注视着自己的刀疤。大飞会一再提醒:拜托,属于的可可那条疤在你屁股上。
有一天,老虎也过来凑热闹。老虎打趣说:“刀把五,可可现在看见你怕死了。因为你太勇猛了,你居然敢打司马玲,你再这么搞下去,可可会遭殃的。”刀把五看着老虎说:“你说说,我们到底谁是怂包。”老虎很生气,说:“好吧,我怂包,我们都是怂包,只有你不是。这总可以了吧?但是你不要再去给可可惹麻烦了,红珊瑚手串已经没了,可可不想为了它被人砍一刀。”
甚至是司马玲,她都托人送来了两百块钱,算是汤药费。因为司马玲听说这是个不要命的货色,她也担心哪天落单了被他在屁股上捅一刀。她毕竟是个女人嘛。刀把五收下了钱,低声说:“我是不会用刀子去捅女人的。”
大飞说:“拉倒吧,抓她头发的就是你。你还以为自己是骑士了。司马玲比可可上路多了,而且更漂亮。”
刀把五说:“我只喜欢可可,是她让我去抢回手串的。”
大飞冷静地说:“她让你抢回手串,但并不想把火烧到自己身上。也许你应该在操场上就杀了司马玲,把手串交给可可,这样你去挨枪毙,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愿意吗?”
我们整天游荡,无所事事。我们围聚在少女可可身边的日子一去不返,她很快就去了糖精厂实习。后来我们认识了很多女孩,马路少女闹闹,纺织职校的闷闷,她们取代了那个冷酷心肠的可可。刀把五有时也会参与进来,但他不太受少女们的欢迎,以前他嚣张而热血,自从挨了那一刀之后,他变成沉默阴鸷,没人对他有好印象。有一天我们说到刀疤,闷闷说你们都是怂包,没人真的挨过刀子。大飞就把刀把五的故事说了一遍。闷闷说:“屁股上有刀疤还真他妈的挺难办的,以后只能威风给他老婆看了。”
这故事差不多就结束了,其实还没有。那年秋天,我们的可可在实习五个月之后回到了化工技校,她挺着一个微微隆起的肚子,怀孕了,而且不打算打胎的样子,于是她被开除了。她幸福地笑着,拿了开除通知书,从我们的眼前走过。我们喊她:“嗨,可可,孩子爸爸是谁?”她笑而不语,兀自前行。有一个化学老师指着可可骂:“贱货。”她也没有回头,就这么走了。我看到刀把五轻轻地叹了口气,啥都没说。第二天晚上化学老师在一条小巷里被个蒙面人捅了一刀,捅在屁股上,也没人知道是谁干的。
【责任编辑 高亚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