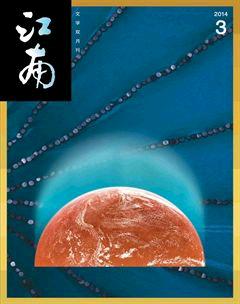小说二题
尤凤伟
桥
1954年我们这届学生进了北岘村完小。
人生由许许多多“阶段”构成,对于一个农村孩子,初小升高小应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头一回走出自己的出生地(村),来到一个新环境和一些完全陌生的人(新老师、新同学)中。原先逼仄的世界一下子在眼前展开。
我们村与北岘村相隔五里路,一早一晚跑两趟。必经的东河(汉河)石桥在1953年被大水冲垮,要在早年,按惯例村里的富户会集钱把桥修好,当富户在土改中被斗,分走了地、房和财物,自己也成了贫户,桥就修不起来了。村里人(包括我们学生)常年只能趟水过河。冬天河水冷得刺骨,夏天一发洪水就干脆过不了河,我们学生就上不了学。遇这种情况,家也住河这边的丁老师就带着其他村的完小学生到我们村,合起来一起上课。这就不会因发大水误了课程。
丁老师是我们五(3)班班主任,教语文课。三十多岁,高瘦个,白净脸。是乡下人又不像乡下人,听说在天津一所师范读过书,论学历是全完小最高的。开学第一课,丁老师走进教室先问句:同学们好。把大家问怔了,以前从没老师这样。见没人应,丁老师笑了一下,说老师问同学们好,同学们也要问老师好。不然不礼貌。大家笑了。丁老师说现在我们再来一遍。我们欢笑着高呼老师好——觉得很新鲜,很带劲。也许就是这蛮有意思的“前奏”拉近了我们与丁老师之间的距离,很快便亲近起来,在意识里不觉得他是老师,而是小叔、小舅什么的。丁老师教课很认真,也很和蔼,不像别的男老师那样动不动“熊”人,下了他的课,大家就把他围在讲台上,除了问功课,还问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城市的洋灰(水泥)路不渗水,下大雨是不是把房子都淹了?还有电灯那么亮不能把人的眼刺坏了?等等。丁老师就边笑边回答我们的怪问题。
很快我们又发现丁老师也有短处,就是胆子小,在路上碰见大牲口和狗便绕道走,有回教室飞进一只蝙蝠,吓得他赶紧用讲义挡着脸。这时班上一个叫常桂欣的男生从书包里掏出一个弹弓,一边往上装石子一边朗念判决词:狗日的,吓坏我们的老师,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正要发射,被丁老师喊住。当蝙蝠被哄赶飞走,丁老师才恢复常态,解嘲说蝙蝠是世界上最瘆人的物种。有同学问蛇呢?他说一样。问你打蛇吗?(在我们那儿有见蛇便一定打死的惯例)不打。为啥不打?丁老师说,蛇长得丑,吓人,可它也是一生灵呵。停停又说,人要善待所有的生灵呵。下了课,他说我教你们唱首歌吧,我们觉得很稀罕,想你也不是音乐老师还教什么歌呀。丁老师就一句一句地教。我们会了,他就从口袋掏出口琴,先吹个过门,等我们唱起来,他就一直伴奏下去,我们唱:
有一种爱像夏虫永长鸣
春蚕吐丝吐不尽
有一种声音催促我
要勇敢前行
圣灵在前引导我的心
……
和丁老师在一起我们很愉快。
转过年到了1955年,这一年整个春、夏没下过一场透雨,进秋却下个不停,像有人把天捅漏。汉河涨满了槽,哇哇响着奔向北海。水面上漂着从上面冲下来的树枝树根,也有一些淹死的猫狗。
我们在村头翘首以待,等候丁老师送教上门。可等了大半晌,也没见老师的身影。就想老师一定有事脱不开身。没了指望,我们就一齐奔向河坝,看大人“捡洋捞”从河水里打捞木头和死猪死狗,挺乐呵的。到了黑下,满村都飘着肉香味。
丁老师一直没来,我们很惦记,等雨停水退返校上课,也没见丁老师的面,换成一个姓赵的女老师给我们上语文课。同学们议论纷纷,不过很快便晓得丁老师被县公安抓走,犯了反动道会门的罪。至于是啥个道哪个门,又反动在哪里,就没有人能说清了。反正被政府捉拿问罪,就和反革命、特务是“一路货”了。
这一阵子抓人很多,“排”(枪毙)的也多。一件事如反复发生也就习以为常了,就像肉市杀猪杀羊那般。可这一回要倒霉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喜爱的丁老师,不知咋的,明明知道是阶级敌人,对他也恨不起来,反倒有些可怜他,盼望政府能从轻发落,最起码留下一条命。我们班有个叫丁素梅的女生,她爹在县检察院工作,虽说不是大官,也能知道些内部消息。我们就想让丁素梅回家打探。出面找丁素梅的是凤起,他与她同桌,又长得帅,丁素梅对他很有好感。他的话丁素梅会听。
果不其然,第二天丁素梅就带回了消息:丁老师因“在教”被抓,不仅“在教”还传教,用反动思
想毒化人民,危害革命事业。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
大家哑口无声,过会儿凤起说:当不得丁老师真犯法了呢,有一回,我到他办公室送作业,是晌午,桌上摆着饭。他闭着眼,两手合成块,嘴里不住念咕:我有罪,我有罪……
真的么?大伙惊讶问。
撒谎是王八。凤起伸手摆出王八形。
自己都承认了,那肯定是有罪了。丁素梅说。
会、会判死刑么?我们紧张万分地问。
这个……
你爹咋说?
他说,是剃头刀子擦腚——
险乎啦!可重抢先说出来。
我们更加慌张,你看我,我看你。
这时,上课钟敲响。
趁吃晌(午饭)的时候,俺们几个同学又凑在一起,也没心思啃干粮,一齐议论快丧命的丁老师,心里沉甸甸的。当然也有些责怪:你个丁老师,好好教书得了,干么要弄那些乌七八糟的事呢?这般政府能饶得过你吗?连老蒋都打倒了,你这样的小鱼小虾,还扛收拾?
又一齐叹气。
丁素梅,你还得打听打听,丁老师到底能不能判死罪?凤起再次给丁素梅下命令。
丁素梅面带难色,最后还是应承下来。
第二天俺们又聚在学校后面那片杨树林里,听丁素梅报告情况。
她说:俺爹问了,领导说丁槐仁(丁老师的名字)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我们“咝咝”地吐气,布告上对判死刑的人都这样写,就晓得丁老师是凶多吉少了。我想起树昌叔对我说的活人与死人永不会再见的话,心如刀割。树昌叔见不到了,很快丁老师也见不到了。对此,我们都很悲伤。可除了悲伤又能怎样呢?
别说我们孩子,连大人都无能为力呵!
现在,能、能救丁老师的,恐、恐怕只有老、老神仙了。家在北岘村的磕巴候廷选同学说。
神仙?神仙法力无边,可又到哪儿去找呢?叫许爱莲的女同学说。
迷信。迷信。丁素梅望着许爱莲说。
迷信。迷信。许爱莲响应。
不,不,俺不是说天、天上的神仙,是地、地上的神仙。候廷选解释。
连天上都没有神仙,地上还会有?胡说。可重说。
有,真有。候廷选打断说,等他磕磕巴巴说完,要说的意思才明了,就是老神仙在他二姑村,一百多岁了。他有法道,能让要死的人留命。
他有仙药?可重问。
我想起白素贞盗仙草救许仙的故事,也跟句:他有灵芝?
就算灵芝能救病人,可丁老师不是病人,而是……马上要被枪毙的……凤起难过地说。
候廷选说老神仙有法道,啥样的人都能救哩。还救过他姑父的爹,断了气,又救活了。
真的?可重问。是咋救的?凤起问。
候廷选说对这个他不清楚。反正捎信叫他赶过去出殡,后来又说不用了。
人没死成?
对。
你姑父的爹还活着?
活着,成天下地干活。
候廷选说得有鼻子有眼,大伙就将信将疑起来。经一番议论,决定让候廷选去他姑家一趟,把事情问清楚。要是真的,就请老神仙为丁老师施法。
反正我觉得这事有点玄。放学回家路上可重说出他的担心。
有句话叫死马当成活马医。凤起说。只要有希望,咱就不放弃。
问题是世上到底有没有神仙呢?这话我没有说出口,是问自己。
刚到家,见婆婆正在灶间做饭,婆婆把风箱拉得呱哒呱哒响,湿麦根也不肯着,直往外冒烟,呛得婆婆一把鼻涕一把泪。我不识时务,赶这节骨眼儿问她听没听说老神仙的事。她没好气地问句你是不是膘了,这么着三不着两?我就把同学要救丁老师的话说了,不料婆婆火气更大,把烧火棍往地上一扔,吼道:这年头连自家的命都难保,还敢管别人?!去!去!
黑下起来撒尿,听爷爷和婆婆在东屋嘀嘀咕咕,我听了听,这一听不要紧,吓得差点连屎都要拉出来,说我一个在青岛当掌柜的本家大爷(我叫他大大爷)被抓起来了,当不了会给枪毙。婆婆说凤池(大大爷的独儿)和他妈命苦呵,以后的日子咋过呀!
这一晚我再没睡着,从大大爷联想到在烟台开文具店的爹,不晓得会不会像大大爷那样“犯事”。他刚出外是在东北伐木头,有一年从黑河里往下放排,被抓了丁,后来逃出来了,不晓得这码事能不能算有罪?要有,俺们一家也就完了。
好不容易挨到天亮,我对哥哥说了黑下的事,哥也害怕,拉我去找婆婆,婆婆在院子里喂猪,哥劈头问:俺大大爷给抓反革命了?婆婆翻翻眼没吱声,哥又问:俺爹会不会有事?婆婆把瓢“砰”地丢在猪食缸里,嚷:政府的事俺一个老婆子咋知道?我和你俩讲——风庄风响,不是成天吵吵着到烟台念书,往后吃香的喝辣的吗?去吧去吧,关你大大爷的地场等着你俩往里进呐。别看婆婆不识字,嘴头子厉害,村里人都说我妈是叫她气死的。哥也不好惹,顶她:不用你管,我就是要到烟台念书。我跟句:我也要去烟台念书。
村里没有秘密,大大爷在青岛被抓的事很快传开,让人惊慌不已,在人们眼里大大爷是村里“出外”人中最风光的,是尤姓人的骄傲。大大爷学问高,会写会画交际广,与康有为称兄道弟,大大爷还乐于助人,借钱借到他跟前,没二话,给。村里要有想“出外”的年轻人,他们的爹妈会说句到青岛去找凤池(大大爷的独子,我的叔伯大哥)他爹吧。“移民”就成。人到了,大大爷先帮忙着“落脚”,再帮着找事做。
不知怎的,想到大大爷犯了事,他的模样在眼前陡地清晰起来:陇长脸,八字胡,五冬六夏光头,灰长衫套马褂,见人笑眯眯。对于我,有件事终生难忘。那天妈吩咐说:风响,你大大爷回来了,你大大妈在家包饺子,说给咱一碗,你去端回来吧。我就去了。进门见炕桌上摆着刚从锅里捞出的饺子,冒腾腾热气,我忍不住咽了下口水。大大爷笑笑,夹起一个饺子送我嘴里,问句风响,想不想天天吃饺子呵?都知道那句“好受不如倒着,好吃不如饺子”的话,还听说皇帝天天都吃饺子,我赶紧吞下嘴里的饺子,说想呵。大大爷说那就好好念书,出外,飞黄腾达。我连着“嗯”了几声。大大爷指着一碗饺子,说快端回去吧,别凉了。肯定是刚吃下肚的饺子勾起了馋虫,等大大妈关了大门,我立刻把碗放在台阶上,吃起来。记不得吃了几个,反正端回去妈看看皱起了眉头,说句给了一顿才给半碗,嘎古(小气)。我不敢吱声,又吃起妈分给的那一份。我敢说那是一辈子吃的最好吃的饺子,余味难忘。可等我懂事,——甚至直到现在,我都对自己的可耻行为自责,难过极了,也后悔极了。觉得对不起死去的妈,也对不住大大爷和大大妈。因我的馋,让他们背了“嘎古”的黑锅。
凤池哥急火火赶去青岛探监,临走时爷爷让他路过烟台时给我爹带信,说自己病了,要他赶快回来。我在心里嘀咕:好好的,咋就有病了呢?不过,能把爹“诓”回来也不孬,爹炒的醋溜白菜肉丝好吃。还能带回些糕点糖块,当然最主要的是问问他能不能摊上事。
学校放“秋假”了,让学生帮家里秋收。我、可重、凤起几个,不时凑在一起,议论大大爷的事,还有丁老师,心事很重。最担心的还是那个老问题:大大爷和丁老师能不能被枪毙。可重嘟囔句:不晓磕巴能不能从老神仙嘴里问出“仙方”。凤起不停摇头说:这是迷信,不能指望。可重说你不信我信。凤起说你想想,丁老师在教,成天拜神,要真有神这茬口神能不管他么?我俩瞪瞪眼,无法反驳他。多少年后我才晓得,这一充满思辨的质疑困惑了满世界的人:老天,你在哪儿看着我们这些凡人?
秋天的毒日头将每个返校学生的脸涂黑,连白皮肤的丁素梅也黑了许多。黑里透红。我们没有约定,第四节课下课钟一响,便一齐提着干粮袋来到杨树林,又不约而同将目光投向候廷选那张磕磕巴巴的嘴。事实上好消息已经闪烁在他的眼睛里。他说放假期间他在姑姑村见到了老神仙,央求再三(还下了跪),老神仙终是大发慈悲道出救人之方,其实很简单:用泥(或者木头)塑(雕)出一个人形,在后背刻上姓名及生辰八字,然后把这“人”下葬。人只能死一回(古时皇上杀人,若一刀砍不死便留命),这是天道,天道不可违。
我们听得目瞪口呆,似乎听到人渴了就喝水。是啊,这么简单的道理,怎么只有老神仙才悟得出来?不知别人,那一刻我确实是这么想的。后来我又想,许多事不能简单说是迷信,迷信常常建立在“想望”的基础上。我们想望造出个替身,替丁老师死。
于是我们就开始做下葬“丁老师”的准备。谁干这个谁干那个。这些看似“儿戏”的事体道出来许多人会不信。其实我们自己心里又何尝不嘀咕,可只要有一丝希望,也要做。
这天放学回家,见婆婆又从柜子往外拿孝衣,我心里咯噔一声,想又要给谁出殡呢?不久知道,是凤池哥从青岛回来了,他没探成监,晚了一步,头天他爹和一伙人犯在六号炮台被执行了死刑,没家人收尸的,由政府一并处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凤池哥只带了他爹的几件衣物回来,还有一些书籍字画。没尸骨,只能把盛了大大爷的衣裳棺材下葬。多少年后我才晓得这种墓叫衣冠冢。
因大大爷死得不光彩,出殡不敢有一点声张,只几个没出五服的晚辈出殡送葬。“入殓”时凤池哥掉着泪说:俺爹和康大爷交情深,算是文友,就让他把康大爷的字带走吧。就把一卷宣纸放进棺材里。后来我知道的是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迁坟,打开棺材见衣裳已经烂了,字还完好。这时凤池哥已经知道康有为的字不一般,能卖钱,就带回家。1960年闹饥荒,村里不断饿死人(包括我婆婆),凤池哥就把康大人的字拿到烟台卖了,换回一些粮食,一家人这才没饿死。说起来是康有为救了他一家人的命。
已记不准是大大爷下葬的第几天,第三天?还是第四天?我们为救下丁老师加紧准备,心里忐忑不安,怕这事被别人知道,更怕老神仙的法道不灵,老神仙也有话在先,说能不能救下,得看这个人的命大不大。我们很骇怕。
后面发生的事就不仅让我们害怕,而是惊恐,绝望。当我们准备完好——塑好丁老师的“金身”,镌了字,在杨树林里挖了“墓坑”,正要下葬,这时传来噩耗:县里已将丁老师这拨人犯执行了死刑,“排”了。刑场在八里外的上庄——汉河入海口的沙滩(现在也不明白那时“排人”为啥要选在沙滩上)。没听到枪声,可能当天是逆风,也可能因路远。
我们悲伤极了,眼泪夺眶而出,心里充满了悔恨:没能赶在公审会前(主要是打听丁老师的生辰八字费了不少周折)把事做完,没能救下丁老师。我们对不住他,还有他的老婆孩子。丁老师死了,他们将孤苦伶仃,无依无靠。想到这一层我们备感凄惶。
可让谁也想不到的是,事情突然有了改变,不,是奇迹,这奇迹之乖戾不啻于死人在“入殓”那一刻从棺材里坐起,让人惊且喜。第二天,丁素梅悄悄告诉大家:丁老师没死。还活着。
咋,没判死?!大家异口同声。
判了。
那……
丁素梅告诉大家,丁老师越狱潜逃了,就在临“排”的头一晚。
我们大瞪着眼,咬紧着牙关,尔后轻轻松开,吁出一口气。泪又涌出眼眶。丁素梅那伙女同学轻轻啜泣。什么叫喜极而泣,这就是。
死犯逃跑事件如雷炸响,很快传开,说法五花八门,当然最权威的还是从“内部”走出来的消息:由于监狱人满为患,一部分犯人关押在民房里,丁槐仁和一个曾在国民党游击队当过司务长的人,关在一间小厢房里,厢房有个被封死的后窗,窗外是野地。据说首先是“司务长”发现这一秘密,撺弄丁槐仁一块越狱。夜深人静时他俩扒开了窗洞,丁槐仁逃了,司务长因太胖钻不出,没一点咒念,只能留下来等着领刑。事情就是这样,正如那司务长临刑前吐出的一句话:各人有各人的命。
丁老师命大,死里逃生。真是死里逃生!
如同所有的事情都会成为历史,丁槐仁案件渐渐被淡忘。当然,除了县公安,丁犯槐仁让他们集体蒙羞,成为一块难以抹去的心病。
若干年后,我把家安在青岛,不,是命运将我带到青岛。后来又一直在这里生活。这中间,我拜谒过康有为墓,发现这里离“排”大大爷的六号码头并不远,便勾起一串串往事,不胜唏嘘。有一天接到村书记可重的电话。可重是我童年的好友,异姓弟兄,每逢过年都会在电话里拜个年,叙谈几句,今番不年不节打来电话,我意识到有些不凡。果然一开口就挟雷裹闪:对你讲,丁老师回来了。
丁老师?哪个丁老师?我一时没反过味儿。
丁槐仁老师呵。
我对上了号,一干往事倏地从遥远处向眼前奔来。如鬼影幢幢。
三十年啦,我像在自语。
可不是。
丁老师从哪回来的?我问。
国外,美国。现在的身份是华侨,富商。咳,今非昔比呵。
当然今非昔比,我感叹,不由想起那个救人却不能救己的司务长和那句几近真理的“各人有各人的命”的话。
当年,丁老师是怎么逃出去的?我问,这是我最想知道的。可重说:开始在内地流浪,东藏西躲,后来偷渡到香港,又从香港到了美国。对了,几个同学想去看看丁老师,你,能不能赶回来?
很遗憾,因杂事缠身,我没能回去看望丁老师。
又过了几天,在县水利局干事的凤起打来电话,说他们已见到了丁老师,又说丁老师很忙,县领导成天围着他谈招商投资。
他投么?我问。
投,不过他说要先做两件事。
哪两件事?
一是为当年的司务长狱友修一座墓,再是在汉河上修一座桥。
我轻轻呵了声,为谢救命大恩修墓完全在情理之中,而修桥……凤起在电话那边像清楚我的疑惑,说:丁老师说,当年秋天的一个雨夜县公安到村里抓他,本来逃出来了,可正逢汉河发大水,河上没桥,他不会游泳,生生被公安堵在了堤坝上……
为这个?我不胜诧异。
凤起又说:可重对你讲没讲,他对丁老师讲了当年我们求老神仙救他的事。
丁、丁老师,他怎么说呢?我急急问。
他什么也没说,哭了。有句话叫什么来着,对了:老泪纵横。
放下电话,我的泪也默默流下。耳畔萦绕起合着丁老师口琴伴奏的那首歌:
有一种爱像夏虫永长鸣
……
对,是1951年,那年我刚入学。在本村初级小学念书。津津有味地朗读第一课:羊,大羊大,小羊小,大羊小羊山上跑,跑上跑下吃青草。
对,是六一儿童节,这一天,我们新生入队,还有县里在大苇子河滩开公审大会“排人”(枪毙)。两桩事凑在一起,所以印象深刻。难忘。
早晨起了床,见爷爷在院子里打纸钱,心想是哪家死了人要出殡么?我开门要走,被爷爷喊住,说别走,一会儿把香和纸给你三爷爷送去。我说三爷爷不是死了吗?爷爷说不死还送这个干什么。先送去,过会儿我也过去,一块给三爷爷出殡。我说不去,今天学校有事。婆婆问今天不是礼拜天吗?有啥事?我说入队,曲老师上午去北岘村完小领红领巾,回来就发,还照相。曲老师说谁都不能请假。
你敢!爷爷把手朝我一扬。
平日我还是很听爷爷婆婆的。妈死了,爹“出外”(外出打工),爷爷婆婆照顾我们兄弟姊妹。有句话叫吃人家的饭嘴软,遇事不大敢“翻腾”(忤逆),何况爷爷脾气大。可今天不成,说啥也不成。还有比入队更重要的事么?当然没有。
跑出家门,才晓得错了,错在没把事分开档,应先把香、纸送给已成死人的三爷爷,然后开溜,上学校,不出殡无碍。出殡的人多,穿一样的白孝服,认不清谁是谁,能打马虎眼。
走在街上抬眼向村东方向望望,那里没一点动静,日头还没从东河上升起来,雾气也没从堤坝上的柳树梢消散,出来得太早了。回家?不行,那是自投罗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溜达了一会儿,肚子就咕噜咕噜叫起来,这才想到没吃早饭。稍一思忖,就抬腿朝村西头我的伙伴可重家走去。
可重一家人正在吃饭。煮地瓜,苞米面饼子,糊涂粥(高粱面粥),还有咸萝卜干。论吃饭,家家户户都差不多。而可重家让我上眼的是摆在炕中央的那张雕花红木饭桌,亮得刺眼,可重说这是土改时分给他家的。除了这张饭桌还有一只樟木箱子和一具犁。我挺眼馋,家里被划中农成分,啥也没分到。
我说可重快吃,一块去学校。别晚了。
下面就按我的预料发展了:可重他妈问我,风响(我的小名)这么早出来,吃饭了吗?我说不饿。他妈说这阵不饿,过会儿就饿了,在这儿吃吧。不等我回声,可重从柳条盘里拿起一块饼子就往我手里塞,说吃。我觉得人家这样,再不吃就是不识敬了,就大口大口吃起来。同样是饼子,我觉得可重妈焐的比我婆婆焐的好吃多了。何况还有这么讲究的饭桌。
吃得肚子舒舒服服,没别的可说该上学校了。出门,日头已升到柳树梢上面,雾也散了。打眼能望出好远。而可重看的是近处,是一座有“红杏出墙”的院子。可重指指问句想吃?我问人家能给?可重做了个鬼脸就上前去敲门,吆:凤超上学了。没人应声,他再吆一遍,里面传来凤超他妈的声音:走啦走啦,去学校领红巾去了。
哼,还红巾呢!计谋没能得逞,只能以嘲笑来解气。
再往前走,碰见从胡同出来的可举和凤起。在俺们村,可字辈的是毕姓,凤字辈的是尤姓,论辈分可字辈和凤字辈同辈,称兄道弟。上学后就跟着老师直呼其名了。可气的只我例外,一齐叫我的外号:地龙(蚯蚓),叫地龙是因为我小时吃土的缘故(多少年后晓得是身体里缺锌)。
凤起问我:地龙你知道三大爷是咋死的吗?我说病死的呗。他说不是的。我问那是咋死的?这时可举接过话头,说是吊死的。我根本不信,瞪他一眼说:胡说八道。凤起说可举说得对,三爷爷是吊死的。我害怕起来,两个人的话由不得不信,可嘴里还是不肯认,嘟囔说不能不能,好好地咋要上吊呢,不可能。可举有些生气说爱信不信。凤起说吊死好几天了,没声张,很多人都不知道呢。一直拖到今天才出殡。我问为啥拖到今天才出殡?凤起吃惊问这你也不知道?三爷爷他儿,也就是凤坡他爹,今天就会死,等死了一块出殡。我握紧拳头,直想朝凤起那张永远洗不净的脏脸打过去,他好像也意识到危险来临,赶紧撤后一步说骗你是小狗,开始我也不信,好好一个人咋能说准了死期,可这事还真是这么回事。我反驳说树昌叔在县里当干部,好好的……可重打断说啥个好好的,好好的能被抓起来,判死刑?今天在大苇子河滩开会排人(枪毙),里面就有凤坡他爹……
凤起说:三爷爷就是为这事才上吊的……
他们再说什么我就听不见了,耳朵嗡嗡地响,像丢了魂似的跟在他们身后往学校走。
县里要开公审大会,在大苇子河滩排人,排的里面有凤坡他爹,因事关我的本家叔,尽管心里害怕还是竖起耳朵来听,事情的来龙去脉就一点一点地聚拢起来:开会排人的事本来是严格保密的,可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而凤坡家的一个亲戚就是在县公安工作的,这亲戚就悄悄地把消息传给凤坡家,凤坡的爷爷(也就是我三爷爷)经受不住这个打击,半夜在牲口栏里上了吊。就这样。想到三爷爷那副驴脾气(他外号就叫三驴),我相信这是真的。至于三爷爷死了不发丧,家里要等他儿——我树昌叔死了一块埋,大伙,也包括我,就不怎么相信了,觉得凤坡家不该把两桩惨事合成块,这不是惨上加惨么?然而事实胜于雄辩,这事实就是凤坡他叔已经带人在尤家茔地并排挖了两个墓坑。
俺爹也被叫去挖坑了。一个外号“大头娃娃”的男生说。
真的?
撒谎是小狗。
大伙瞪眼你看我,我看你,由不得不信了。
这时,从大苇子村方向传来嘀嘀嗒嗒的军号声。号声就是命令,神情惊慌的同学们一齐奔出校门,来到与学校毗邻的河坝上,往河上游望去。这河俺们一直叫东河,多少年后才知道官名叫汉河。一条不起眼的河却有个雄伟名字,真不可思议。汉河发源于昆嵛山,流经沿途的村庄后流进北海(渤海)。大苇子村在俺们村的上面,有三四里路远,河在那里拐了一个弯,就拐出一大片河滩来,由于被河坝上浓密的柳树遮掩,俺们看不到今天被当成排人刑场的河滩。可晓得河滩上肯定扎了台子,台下肯定有密密麻麻的人群,当然还会有跪在那里的反革命和用枪指着他们的民兵。可我们一概看不见。凭想象。
听说年后县里已“排”了好几回人,在别处,大苇子河滩是头一遭。这在当地算是新鲜事。爱看热闹的人就从下游各村涌上河坝,沿平坦的坝顶向大苇子河滩奔过去,浩浩荡荡。
同学中也有人跃跃欲试,特别是三、四年级的男生,但遭到大部分人的反对,理由是说不定曲老师早早就从北岘村回来,要见人跑掉会发火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一向严厉的曲老师不会容许他的学生不守纪律。于是就没人敢于擅自行动,甚不情愿地留在坝上,眼巴巴望着柳树行后面的大苇子河滩。似乎能听到大会会场的嘈杂声,当然还有那吹起来就不停歇的军号。
为什么“排”人之前要大吹军号呢?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仍然不解其中原委。然而却形成一种条件反射,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只要听到嘀嘀嗒嗒的号声,我就会想到行刑“排”人,眼前出现将白亮沙滩隐藏起来的柳树行。
我们在等待,等待一桩人人惧怕的事情,尽管对这事情的意义并不明确,甚至也晓得其观赏性也仅限于最终从柳树后面传来的一排枪声,这枪声也许并不比过年的鞭炮来得更清脆响亮,可仍然让人充满期待。恐惧也是人与生俱来之所需?
漫无边际的等待会让人困顿,感到无聊,不耐烦,便就地做起了游戏,女生从兜里拿出毽子来踢,还有的在地上划了线“跳房子”。男生的玩法更是五花八门,却也是老掉牙的“庄户耍”。如弹蛋(玻璃球),打“家棍”(木头)。其中一项颇新鲜的是“打老蒋”:用五块石头摆成一个军事阵列,中间一块大些的代表反革命头子蒋介石,他的前面和后面是前锋与后卫,左面右面是左军与右军。玩法是大家依次向阵列投掷石块。争先恐后将前锋后卫与左军右军打倒,而没能建功的那一个人就成了此役抓获的老蒋。对老蒋的惩罚是游街示众。前锋背着,左、右军扯着两耳,后卫在后面抡拳击背。这游戏的结局常常是“老蒋”忍受不住揪打而哭泣,告饶。这也是游戏本应取得的效果。
这是男孩子们最喜欢玩的游戏,我也是。可没等轮上我,我就听见有人喊我的小名:风响——风响——我先一愣,转身望望,是婆婆那半截树桩样的身影立在村头。
我慢慢吞吞地挨过去,气呼呼地吆:干吗喊俺小名?婆婆不理会我的抗议,说时辰到了,快回去给你三爷爷出殡。我说急啥,俺树昌叔还没“排”呢。再说还要等着曲老师回来发红领巾呢。婆婆不由分说地抓住我的手,往村里拉,边拉边说:你三爷爷是你爹的亲叔,你这当孙子的不去出殡人家会笑话的。我想想也是,这是不能破的规矩。我妈死时,不单是凤坡,他爹——也就是我树昌叔也专程从县城赶回来,带回“童男童女”和“大白马”。可今天,树昌叔就要……
我不再与婆婆争竞,规规矩矩地回了家,婆婆从柜子里拿出一件孝服,这是妈死时做的,后来过年过节上坟也穿。农村孩子差不多是穿白衣长大的。婆婆边帮我穿边说:你爷爷已经过去了,你快去,别耽误起灵。
尽管心里还是惦记着“入队”大事,可还是听从婆婆,以当尤家子孙为重。凤坡家在后街,从一条胡同穿过去就是。刚出胡同口,便听见哭声,呜呜咽咽,再往前去,就看见凤坡家门口站着几个持枪民兵,个个绷着脸,像大敌当前。我都不认识,知道是外村来的。我多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心里不由得怦怦地跳。害怕是害怕,还记着自己来的“任务”,硬着头皮往凤坡家大门走。就被民兵用枪指住。我赶紧分辩,说自己来是给三爷爷出殡的。一个长红鼻子头的民兵仔细看看我,说晚了。我吃了一惊。问句:人抬走了?红鼻子头民兵收回枪,说抬走了一个,另一个……他住口了,可我晓得他咽回的话是什么。就是……我也不敢再想下去,抬腿往前跑去,刚跑几步又停住脚,回头问句:家里还有人吗?红鼻头民兵说有个老太婆,我知道老太婆就是我三婆婆,我还知道,凤坡也跟着出殡队伍到茔地去了,在那里等他爹的尸体从河滩运过去,和他爷爷一起下葬。
回到家,我把孝服脱下来,丢给婆婆,婆婆生气地说:这孩子,叫你去给三爷爷出殡咋又跑回来了?我闷闷地说,晚了。婆婆皱起眉头问晚了?我说嗯。婆婆又问去茔地了?我又嗯了一声。婆婆想想说:你赶快去茔地,三爷爷和树昌叔都是你长辈,得去磕头。我说我不去,害怕。婆婆看看我说,没事,死鬼不吓唬自己的亲人。我一下子想哭,咽声说:可树昌叔还没死哩。婆婆半天不吱声,阴着脸,后叹了口气,说不去就算了,在院子给你三爷爷和树昌叔磕个头吧。又说把孝服再穿上。
磕头的时候我终于没忍住,哭了起来,起身后我看见婆婆用衣角拭眼泪。
我出门往学校赶去,觉得曲老师应该能从北岘村回来了,虽然耽误了出殡,但入队仪式还能赶上。走到尤家祠堂前的老柏树下,陡然听到上面的老鸦(乌鸦)“哇哇”叫了两声,我吓了一跳,站下,陡地想起我妈出殡那天也有老鸦在树上叫,那一刻我在树底下吃生花生,头一天下大雨,水把还长在地里的地瓜花生冲出来,村里人都去捡。凤池大哥从地里回来,顺手把一墩带蔓的花生撂给了我。我馋得要命,不管不顾地在柏树底下大吃大嚼。对了,也就这时候我看见凤坡他爹我树昌叔从村外走来(后来晓得是回来给妈出殡),他在我身前停下来,不住打量,问句:你是锡诚家的风响吗?我哎了一声,还继续嚼花生。他又问:你今年几岁了?我把花生咽下去,说六岁。他叹了口气,又摇了摇头,说真是个孩子呀,不懂事,妈要出殡了还在这儿吃花生。说完又叹了口气,问:知道人死是咋回事么?我没应声,呆呆地看着他。他说我告诉你吧,人死了就再也见不着了。我懵懵懂懂问句:再也见不着了?他一边点头一边擦脸上的泪。我吓坏了,也许就在那一刻我明白了人生死的真谛:就是活人再也见不着死人,死人也见不着活人。这时树昌叔抬头看看天上的日头,说你妈就要入殓了,快回去看最后一眼吧。我撒腿飞奔,一头撞进院子,这时棺材盖已经盖上了,木匠正要钉钉子,我的哥哥、妹妹围着棺材哭,爷爷看见我,想发火又止住,对木匠挥挥手说等等,让风响看他妈一眼。木匠就放下锤子,将棺材盖错出一道缝,我跷着脚,从这道缝里我看见妈像睡觉一样平躺在里面。我大哭起来,随后被爷爷拉开。妈一辈子没留下一张照片,我头脑里的全部印象就是她躺在棺材里面的样子。
而让我见妈最后一眼的树昌叔,此时此刻正在大苇子河滩等死。想到这我眼里又流出了泪,止不住。
学校里空空荡荡,人还在堤坝上。我只得再返回去,这时男生都不见了踪影,一个女生说都去菜园偷黄瓜了。果不其然,不一会儿,男生风风火火地奔回来了,手里擎着翠绿的黄瓜大啃大嚼。可重看见我说你不渴吗?来,给你一根。说着把一根黄瓜塞在我手里。正这时,只听有人高喊红领巾——红领巾——顺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我们看见河对岸有一个身影,不住挥动手里的红领巾。呵,是曲老师,曲老师回来了。
走呵,去迎曲老师呵!可重高呼一声,真是一呼百应,同学们迈步冲下河堤,正要趟水过河,被一拉溜站在河滩上的民兵拦住(在这之前俺们竟没有注意到)吆:站住!谁都不能乱动!大伙就止住步,又一步一步退回河坝上。都明白曲老师也是被民兵拦在对岸,不得回村。他挥动红领巾只是向同学们报信他回来了,而且领回了大家盼望已久的红领巾。
有人气愤地嚷:层层把守,干么这么戒备森严呢?
有人说是怕劫法场吧。
老蒋被赶到台湾了,谁还能劫法场?
老蒋跑了,还有特务反革命哩,今天要“排”的这些人就是。
特务长个啥样呢?
谁知道,反正和平常人不一样。
咋不一样,凤坡他爹就没啥两样的。
他爹不是特务,是反革命。
特务和反革命是一路货。
一路货咋叫两个名?
黄狗黑狗都是狗。
谁的话都不能让人信服,就不再争竞了。大伙又为公审会拖的时间太久愤愤不平。
顶多半个钟点,枪就会响。说话的是可重。
你凭啥知道?丁启原不服。
就知道。可重说。
你敢打赌?丁启原问。
敢。咋不敢?怕你?可重不后退。
那打啥赌?
啥都行。
听说丁启原和可重要打赌,现场的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一齐怂恿他俩把赌打成。箭上了弦,不得不发。
一盒洋火。丁启原提议。
多了。十根。可重修正。从一盒改到十根,是因为他家穷。
打一回赌,赢输才十根,没劲,没出息,不干。就一盒,爱赌不赌。丁启原不肯让步。
行,一盒就一盒。可重不想让人笑话,咬咬牙,应了。
达成一致。又有了新问题。没有钟表,无法计时。
可重问丁启原:你爷爷不是有块怀表么?你回去要出来用用。
甭想。甭想。丁启原把头摇得像货郎鼓。
偷出来。毕可重支招。
那他能砸断俺的腿。丁启原一脸惊悚。
事情给绊在这里。
丁启原转向身旁的可重,说你隔家近,回去把你妈的座钟搬来用用。
可重刚要反驳,却一下子打个怔,所有的人也怔住了,这是因为吹了半头晌的军号陡然停了,这变化有些让人猝不及防。
几乎在号声停下来的同时,从柳树行背后的河滩那边传来了一串清脆的枪声。
啊!啊!啊!孩子们一齐惊叫起来。个个吓得脸色煞白。
啊,树昌叔!我在心里呼了一声。
这时军号又吹响了。
刑场那边大乱。嘈杂声压过了号声。那是围观的人发出来的。
果然,这边民兵也从河里撤岗了。我们看到曲老师挥舞着红领巾趟水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