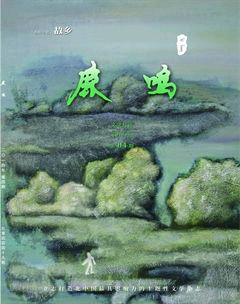忽略的隐喻
洪忠佩
相框里的相片我是第一次看到,黑白的,褪色得有些发黄,带有那种远去的色调,一张没有笑意的脸,端正、暗淡、陌生。相片究竟拍于什么年月,我无从知晓。而相片里的人是谁?相片又是什么时候挂起来的?老家(婺源人口语习惯,欢喜把故乡称作老家)也没有人跟我提起过。相框里的相片与奶奶的相片并排挂在老屋的墙壁上,我猜想相片里的人应该是我没有见过面的爷爷了。他的血脉遗传给了我父亲,父亲的血脉遗传给了我,他却没有给我机会叫他一声爷爷。记得父亲去世时,我儿子才学会走路。儿子比我幸运,他至少见过爷爷,也叫过爷爷。对于爷爷这样的称谓,我的记忆始终是缺失的。在技术层面上,相片可以翻拍放大,然而,我奶奶与父亲都先后走了,能够与相片中的爷爷产生记忆重合的叔也卧病在床了。
叔的少年、青年,乃至老年都是跟着他相依为命的母亲(也就是我奶奶)生活的,他父亲(也就是我爷爷)走的时候,他还是个“小把戏”(小孩)。奶奶一身之下有三个儿子,一个是我父亲,一个便是我叔,还有一个是二叔。不过,二叔从小就送给了村里人。当年,爷爷英年早逝,奶奶连自己的小儿子都无力抚养,那样的家庭困境真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叔长大后,由于家庭苦寒,老婆都娶不起,一直打着光棍。十多年前,奶奶走了,叔的天就塌了。勤劳省俭的叔,开始变得懒散、抑郁、偏执、沉溺、邋遢,并在孤独中苍老。人老的特征是不爱说话,容易发呆,懒得动,而这些都在叔身上得到了印证。我怕叔在老家一个人生活没人照顾,就动员他去敬老院。我说叔,你是五保老人,一个人在家待着也不是个事,散养还不如集中供养。没想到,我为此还挨了他一顿臭骂,好像送他去敬老院是对他的一种侮辱。叔最后放下脸说,去敬老院,要你们这些侄子干什么?叔应了村里一句俗话,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一年四季,叔情愿在村里闲逛,也不去管田地抛荒,他陷入了一种困顿与孤苦之中,以至挨边七十了,还是一个人孤零零地生活在空荡荡的老屋里。老家二叔和邻居的电话,成了叔身体疾病的信息源。他身体出现状况了,二叔和邻居的电话是我获取信息的唯一渠道。每每看到手机上显示二叔和邻居的电话号码,我知道叔又病了。从蛰居的县城到乡下老家,我只有来回跑。能够为叔做的就是送去就诊,把他的身体交给医生。冷一餐,热一餐,饿一餐,饱一餐,成了叔一个人无序的生活常态。他一日三餐图省事,经常把村里小吃摊上卖剩的油条菜包包销了,兜里没钱,就赊着。有的时候,摊主问他结账,他嘿嘿笑一笑,像似自嘲,话都不回一句甩手就走了。摊主知道,我们侄子辈的几个一年回老家都会帮叔付钱,也就由着他照赊不误。叔的不管不顾,换来的却是肠胃功能紊乱、退化。往往,叔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依然有一餐没一餐的,冷热不分,甚至馊了也照吃不误。叔这是和自己,或是和侄子过不去吗?肯定不会。那他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依然我行我素呢?有的时候,别说村里人,连我和家里人都想不通……
即便在秋天的昼上,老屋房间里的昏暗足可以隐藏甚至碾碎一切。从我走进房间的那一刻起,昏暗立即把我淹没了,我的眼睛进入一片盲区。昏暗的房间里,弥漫着一种泔水与屎尿混合的怪味。连接叫了几声叔,叔都没有应我,只能听到他微弱的呻吟。我摸索着找到电灯拉线开关,扯了几下,毫无反应。这是我从小跟着奶奶生活过的房间,奶奶也是在这个房间里病逝的,房间里的每一处我都烂熟于心。然而,我却不得不从房间的昏暗中退了出来,到邻居家去借手电筒。借着电筒的光亮,我才看清躺在床上的叔已经瘦得皮包骨了,他裸露着身子,头发篷乱,胡子拉碴,堆在身边的被褥和衣服上都沾着屎斑。而地上的痰盂里呢,装满了呕吐物,床头的木桌上,盘碟里剩着几个菜包,还有一碗没有动筷的面条。我真弄不懂叔了,房间里的电灯是切了电源的,窗户也被木板铁钉钉死了。但有一点很明显,叔已经卧病在床多日,而且大小便失禁了。我叫着叔,叔还是没有应,但眼角上有了泪痕。面对叔这样的状况,我去找村里诊所的医生,村里的医生听后就婉拒了。我再去找乡医院的医生,乡医院的医生不以为然地说,你不看见门诊都看不过来,还有时间出诊?无奈之下,我找来同村的二叔,把叔背去了乡医院。医生说,像这样的病人大小便都失禁了,乡医院没有能力接受,要住院得院长同意。我解释说,病人没有什么恶症,他只是肠胃上的毛病,年纪大了,卧床久了,功能紊乱,虚脱而已。我是他大侄子,病人万一有什么事,也不会怪你们。医生说,现在的病人家属都不是省油的灯,这样的事见多了,万一有个事就是医患纠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经过软磨硬泡,院长才勉强同意接手。吊针输液,医生找不到病根、病源,只有打葡萄糖的点滴。换衣、擦身、洗脸、剪指甲、喂水喂食、接大小便,说实话,所有这些,奶奶与父亲当年生病的时候,我都没有能够做到如此具体,而面对苍老孤苦的叔,我做了。人呀,只有经历过生死离别的人,才会懂得“子欲孝而亲不待”的感受。
乡医院的住院部是一排平房,有二十个床位的样子,却只住着叔一个病人。住院部病房与门诊部打吊瓶的输液厅有着鲜明的对比:一边冷冷清清,一边挤挤挨挨。点滴一瓶瓶地打,叔的身体还是没有半点好转的迹象。二叔一天急匆匆走,急匆匆来,讲话的机会都少。在病房的走廊上,二叔一身汗滋滋的,脸颊与肩膀上都是水泥灰,他歉疚地说,大概有一个多礼拜了吧,街上看不到他人,就知道他病倒了。自己家里的屋去年受台风“海葵”的影响,墙都裂了,没办法,今年只好勒紧裤带,正在忙着拆倒重建,想照顾他也照顾不过来,一天只有抽空送点豆浆面条什么的去给他。几天不吃不喝,身体好的人都扛不住,何况他还病成这样。我也纠结了几天,实在没办法了才给你打电话。我对二叔说,老人抵抗力差,拖不得,早看医生早好。叔如果是绝症,他熬不到现在,以前不是打打针吃吃药就好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我的话是在安慰二叔,我自己心里也没底,毕竟,叔是七十岁的老人。与医生碰面,医生就接二连三地催促转院,说得我心里开始发毛。是我的侥幸、盲目,还有一厢情愿吗?我能眼睁睁地看着叔等死吗?第三天的晚上,我终于坐不住了,给远在广州打工的弟弟打了电话,说了叔的病情。弟弟二话没说,连夜往家赶。次日下午,就把叔送进了县人民医院。抽血、化验、检查,结果让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叔除了肠胃和肾上的毛病,医院给出的主要病因是“重度营养不良”,并没有患什么绝症。在老屋房间里,在乡医院,叔对生命的态度是自暴自弃的,有放弃治疗的意思,而在县人民医院,除了情绪低落时,我感到他求生的欲望明显。住院时,叔有不良反应,双脚肿得厉害,容易出血,脚指脚背都结着血痂,让一家人担心了好几天。他倒好,干脆“跌倒赖着睡”,连病床都懒得下。同病房的病友佝着背叹着气对叔说,你呀,有这样的侄子是你的福气,你看看我,都是女儿来照顾,儿子连影子都见不着。endprint
每年的深秋,都是县里筹办乡村文化节的日子,也是我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叔在医院住院,我只好宿舍、医院、单位轮着转。让我和家人感到欣慰的是,经过十二天的治疗,一个半月的休养,卧床不起的叔,又回到了能够上街闲逛的叔。问题是,如果叔跟我生活,住房是个大难题;如果送叔回乡下老屋,等于又让他重蹈覆辙,弄不好过不了几天又要上医院。我试着与叔沟通交流,想让他去镇上的敬老院生活。毕竟,在敬老院有人照应和管理。我对叔说,镇上敬老院我去看了,环境不错,临河,两排楼房,有个院子,还有菜园。里面四乡八村的老人有二十多个,村里“大头炳”、“细女犟”在那里都生活好几年了,你去了也多个老年伴。起先,我怎么说叔总是不吭声,甚至翻着白眼。然后,垂下眼睛,陷入了沉默。嗯,哦,每次与叔交谈,他的回答像挤牙膏似的,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挤,而且重复。有的时候,我和叔说着说着,他就有了鼾声。叔在村里老屋生活惯了,他在县城宿舍进房间不换鞋,上卫生间不冲水,弄得一家人都头痛。我跟叔说了,他嗯一声答应得很好,过后又忘记了。一天晚上,我陪叔去健康路街口理发,他说今天在街上碰到村里谁谁谁了,他们也老了哩。我故意气气叔,说那天背你去乡医院,村里卖猪肉的瘪三跟着要账呢,你欠了他多少猪肉钱?叔嘀咕了一句,他具体说了什么,我都没听清楚。回家的路上,我见叔有谈话的兴趣,又提到了去敬老院事,没想到他爽快地答应了。
乡下的老屋,是乾隆年间建的,屋的堂名叫“忆善堂”,不仅有前堂、中堂、后堂,窗棂房梁上有雕饰(“渔樵耕读”、“瓜瓞绵绵”等),清一色的石板地,还有三个露天的天井,阔大、空灵。一个在唐代建村,以洪姓氏族聚居的村庄,在整个村子里像我家这样的老屋也屈指可数了。我没有机会看见家谱(在人性泯灭的年月,家里的线装书连同家谱都付之一炬),无处知道祖上有怎样的发家史,能够在村里建起这样的大屋。祖上的家境应该很好吧,可后来怎么滑入了如此窘境呢?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和母亲从老家迁往县城跟父亲生活后,两位弟弟还跟着奶奶和叔在老屋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来,父亲患病又回了老家。记得父亲嘱咐我送他回村庄时说,叶落归根,在外转了大半辈子,也该回老家去了。当着父亲的面,我眼睛泛红,差点眼泪就滴落了下来。奶奶与父亲先后去世,两位弟弟上完初中也就陆续南下打工了,村里的老屋只剩下叔和堂叔一家居住。叔的年纪虽然只比堂叔大十几岁,但性格却孤僻得很,他和堂叔一家,甚至二叔都断了来往。有时,见着面还像冤家似的。叔在县城住院休养的一天早上,堂叔和村里的一位亲戚到了我家里,绕来绕去说了一大通,才把话题扯到了村里的老屋上,说什么县里文物部门普查登记了一次又一次,也没见个动静;说什么老屋年久失修,漏的地方漏,朽的地方朽,而且白蚁蛀得厉害,若没人住,是个大问题,照这样下去,终有一天要倒塌;说什么你母亲有一块菜园地前几年就配给外姓人做了屋,今后老屋与其好了外人,还不如好了自己人。说来说去,他们的话外之音是想出点钱买下老屋。面对两位长辈,我说了句实话:祖居屋我肯定不会卖,也没有权利卖,何况我两位叔叔和我母亲还健在呢。再说,有栋老屋在,心里对老家还有个念想,不然,真的回老家就是清明扫墓一件事了。两位长辈磨了许久,看到没有商量的余地,悻悻地走了。
叔去镇上的敬老院生活了,老家也没人给我打电话了。大年二十四的前几天,我邀了几位书法家朋友去老家帮村里乡亲写对联,除了上了年纪的老面孔,年轻的我基本都不认识,尤其是有的年轻人出去打了几年工,讲话口音都变了,有一个居然染上了水红色的头发,是那种爆炸式的。与我少年一起长大的“少年伴”,有两个在南方打工都落下了残疾,一个肺部出了毛病,一个脚上截了肢,而他们最小的小孩还“一把秧”(很小)。身体的残疾,给他俩的家庭带来了一团糟,一家一个,大的子女高中没毕业就踏上了打工的路途。二叔的儿子媳妇也在外地打工,他家的新房建好了,他要了两幅喜迁新居的对联。趁朋友挥毫泼墨,我抽空去了老屋。巷子里已经有了浓浓的年味,向阳处晒起了腊肉、香肠,还有咸鱼。而“小把戏”呢,开始玩起了噼噼啪啪的甩炮。老屋大门紧闭。叔去了镇上的敬老院,老屋彻底失去了烟火气息,屋里寂然无声,落寞、阴冷,弥漫着一股霉味。伫立老屋堂前,我不禁想起了奶奶领着我大年三十拜祖宗和一家人“吃隔岁”(吃年夜饭)的情景,仿佛那饭菜香还在,那爆米花和炒米片的香甜还在。唉,香椅桌和八仙桌依旧,却物是人非了。我想,如果有一天老屋坍塌了,老家就真的只剩下几堆坟冢了。
那一夜,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从清华走到唐下,转过岔口,我发现河床裸露,新房栉比,老家那丰腴的轮溪,以及古朴的村庄不见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