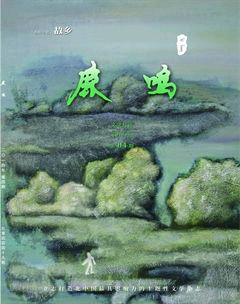故乡是什么
王存喜
1
故乡是什么?
我曾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
从我懂事的时候,就晓得了自己是收养的,亲生父母是谁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个谜。奶奶在世的时候,我曾经在某个黄昏噙着指头问过她,她听到四下瞧瞧,慌乱地堵住我的嘴说,不许胡说,不许胡说,谁跟你说这混账话来着。
我定定地瞧着她,弄不明白她为啥那么慌张。
奶奶瘦小枯干,裹着一双小脚,走路轻飘飘的。记忆中的她总是围着锅台转来转去。逢到养父发狂,我就盼着奶奶出现。奶奶很少让我们失望,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飘进我们的屋子,奋力把正在挨打的我或者是姐姐妹妹拉到她的屋子里。实在拉不开的时候,她会拼命扯住养父的胳膊喊,还不快跑,瓷在那里等他打死你!
我喜欢奶奶的屋子。她的炕上铺着整块的油布,颜色墨绿,四个角有连串带拐弯的黄色方格,那些方格恰好把油布中间的一只黑白相间的鹤圈在里头;我也喜欢奶奶墙围子上的那只威风凛凛的老虎,总想看个究竟,凑得近了、盯得紧了,那老虎反倒没有在地上看那么逼真了。
奶奶屋子里的窗户上只有几空狭窄的玻璃,其余的小格格都是用毛边纸糊的,冬日里慵懒的阳光顺着有玻璃的窗格射进来,我便能看见光线中的尘埃快速流动。这时的奶奶盘腿坐在炕上,目光沿着那些尘埃飘得很远。你若是问她什么,她仿佛没听到似的,问得紧了,或者扯她一下,她会“哦”的一声收回那悠远的过去。
她的过去被透进窗格的光柱切得支离破碎,听起来也如同一堆乱麻。日子一天天将那团乱麻梳理清晰了,我慢慢知晓奶奶曾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家里有四挂马车,爷爷家也是殷实人家,后来抽大烟破落了。奶奶讲过的故事很多,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年爷爷用箩头将养父从“口里”(山西)挑出来的那一段。那时的我总会用手抚着奶奶小巧的鞋,脸上现出几丝迷茫。我不大相信奶奶的话,总觉得她那双小脚不可能扯着两个幼小的孩子走完那么遥远的遥远。
我还好奇什么是大烟?抽烟怎么能把家抽穷,大爹、二爹、养父都抽烟,家怎么没有穷呢。
奶奶屋里有一个长长的红柜,里面有白面、白糖、红红绿绿的缎面、衣服什么的。那个柜子更像一个魔术盒,还能变出很多我想吃的东西来,几粒花生、一两块糖果。若是赶到八月十五以后,丝丝缕缕果味混合着月饼的清香便顺着柜子的缝隙溢出来。一般情况下,柜子永远是锁着的,一个大大的铜钥匙就在奶奶的口袋里。
她偶尔也有忘记锁的时候,我曾趁着她不在的时候和姐姐踩着凳子用力掀开柜盖,翻出一块带花牙的月饼。月饼已经风干,很硬。我们想吃又不敢吃,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姐姐说,我们舔舔吧。俩人你舔一下,我舔一下,舔了好久。末了,我实在忍不住了,轻轻用牙齿小心翼翼地在月饼的花牙上划了几道。姐姐慌了,一把夺过我手中的月饼砰地盖上了柜盖。
故乡是什么?
故乡就是月饼上浅浅的划痕。
2
那块月饼对我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终于在一个暖洋洋的冬日里我将它揣进了口袋,那一刻,惊喜、恐惧、罪恶、慌乱交织在一起,从奶奶屋子逃出来时,被门槛绊了一溜跟斗。顾不上拍打膝盖上的土,也顾不上手掌的疼痛,逃向南房。
南房的门是用铁线摽住的,但窗户早就烂了一个大洞,黑狗在不拴的时候,常常从那里进进出出。遇到院子里的哪扇门响,它就会将硕大的脑袋探出来看个究竟。我恐慌的情绪感染到了黑狗,但它的反应慢了些,我从窗台上踩着它背跌了下去。
南房的灰尘很多,我的摔落,狗的躲避碰掉了一个铁桶,发出了巨大声响。我潜在地上没敢动,过了好一会儿,才站起来顺着窗户的破洞鬼头鬼脑地向外偷窥了一会儿。
躺在干燥厚实的草袋子上,头枕着黑狗柔软的腹部,我一点一点享受着世间里最香甜的美味。吃到一半,我忽然舍不得起来,四下踅摸了一阵,踩着一个三条腿的板凳将余下的月饼放在了墙上一块凸起的砖上。随后又从窗户里跳了出去,出去不久又担心月饼会被黑狗吃掉,又火上房似的跳了进来。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等我进来后,月饼正好消失在黑狗的嘴里。
我恨透了黑狗,小声啜泣着对它连捶带打,还扳开它的嘴试图从里面找出我那半块月饼。黑狗也知道自己错了,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一声悠悠的叹息打断了我的狂躁,那是奶奶,我瞬间清醒过来,探头向外看时,奶奶蹒跚着向正房走去。
奶奶知晓我偷吃了月饼,我躲在南房里不敢出来。太阳沉到了西边,呼啸的风将夜忽地塞住了南房窗口的那个破洞,我眼巴巴地瞧着奶奶窗口暗黄的光,几次将腿迈到了窗台,又作罢。黑狗回来了,挟着一股冷风,我怕它再次走掉,死死搂住它的脖子,它仿佛懂得我的心思,卧在了草袋子上,我蜷在它怀抱里,在恐惧中睡去,再次醒来却是在奶奶的炕上。
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奶奶屋里那个长长的红柜会是她最终的归宿。那个令我好奇、神秘、渴望、万花筒一般的柜子最后装的是奶奶。
我也从来都没想过奶奶也会死。
当那个红色的长柜被漆了层黑亮亮的油漆后,看上去是那么陌生、诡秘、恐怖。柜子是敞开的,柜盖立在柜子旁边。柜子和柜盖下边的红砖地面上有着点点滴滴的黑点子,我大声哭喊着奶奶流血了,奶奶流血了。
大爹斥责我的养母,还不把孩子带回去!养母拽我的时候,我死命扒住柜子连踢带踹着:我不走、我不走,奶奶在流血。养父上来就是一大巴掌,我的头嗡的一声,但手还是没有松开柜子。没见过几次面的大姑一把搡开养父抱起我说,军军,你奶奶没白疼你,你是不是想看看你奶奶,来,好好看吧。说着话,她揭开了奶奶脸上的那张黄裱纸。
奶奶很安详,睡着了一般,我探着身子去摸她的手,但就是差一点没够着,用力一挣,却栽进了红柜。脸触到奶奶的脸,冰凉。养父抓着我的领子把我提了出来,我两腿乱蹬着喊,奶奶冷、奶奶冷。没人听我呼喊,我被养母抱出了外边,临出门,我看到五爹和二爹把柜盖盖了上去,大爹和另外几个大人用锤子将几枚长钉钉到了柜子的边缘。endprint
我不知道他们抬着奶奶要去哪里,好长时间里都担心奶奶怎么才能从那个被钉死的柜子里出来。
故乡是什么?
故乡就是奶奶那一声悠长的叹息。
3
我在该上学的时候没有上学,这倒不是因为穷得上不起,而是养父认为上学不仅没用,甚至还有害。不少亲戚在他不发病的时候劝说他让我上学,他常常会把他四弟抬出来,说他就是因为学的东西太多了才把命丢掉。
他说到我四爹的时候,那些亲戚总会有意无意地瞟上我一眼,然后叹息着离去。
院子里该上学的孩子都上学了,院子外的大人不让他们的孩子跟一个疯子家的孩子玩耍,我寂寥得不知道该干什么,便跟上堂哥他们去了不远处的学校。
我偶尔也会叼根辣麻麻盯着天上的云朵发呆。
我没见过四爹,但每天都往学校跑,因为能跟我玩在一起的孩子都在学校里。人家上课的时候,我就扒在窗户外边听;人家下课的后,我又跟着人家疯跑。偶尔,我也会盯着黑板上方那几幅大大的相片出一阵神。
堂哥很笨,他经常因为写作业被二娘敲打,有几次在我们家写作业,我见他咬着铅笔头对着几道数学题发呆。我急着要跟他玩,看了看他本子上的题,随口给他念出得数。他真就照着写了,还全对了。
慢慢的,他的作业成了我的作业。我喜欢本子,尤其喜欢新本子上的那股清香,能够在他的本子上胡写乱画仿佛是占了很大的便宜。二娘也因堂哥的作业欢喜了好一阵,她很愿意让堂哥去我们家写作业。我也曾担心堂哥在某一天会不让我在他的本子上乱写,可这事从未发生过。有那么几次,因为我玩疯了顾不上给他写,他还送给我四个烟盒叠的三角。
堂哥上二年级那年,我们院子里的大人们争吵过几次,好像是因为奶奶的屋子。没过几天,院子就搬来了一家,男人的脸上有一道疤痕,女人白白净净,家里有四个女孩,他们住进了奶奶的屋子。又过了几天,我居然在学校里碰到了那个女人。她是新来的老师,教的恰好是堂哥那个班级。有一天,我在外边听得正入迷,肩膀被人拍了一下。回头,却是那个女人。女人说:想听就进去听吧。
在教室里听了没多久,赶上了期中考试,女人给我发了卷子,还给了我铅笔和橡皮。我三下两下答完了卷子就走了。后来,女人三番五次地到我家,再后来,她还搬出了养父厂里的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我一直以为养父从没怕过别人,可他看到那个戴眼睛的男人后,畏畏缩缩地同意我上学了。同一年上学的还有我的姐姐。有趣的是,姐姐上一年级,我却直接进了堂哥的那个班级。
我上学没几天,堂哥便惹下了滔天大祸。他在跟同学闹着玩时把黑板擦甩在了黑板上方的一副相片上,相片上那人的嘴角有个痦子。黑板擦硬硬的角把相片上那人的眼睛戳了个洞,看上去有些滑稽,我当时觉得很好笑。接下来的事情就不好笑了,几个老师先后进来,后来是校长,堂哥反复被叫出去又回来,走马灯似的。
次日早上,我们家的大院里来了许多人,整个院子和屋子被翻了个底朝天,最后,二爹被带走了。养父那天也犯了病,躺在院子里口吐白沫。再次见到二爹是次日下午,他佝偻着身子悄悄掩进院子,当天夜里,二爹一家人就失踪了,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来我们家的人越发多了,养父养母姐姐还有我都被盘问过。他们问的很多是关于我四爹的事,汇聚了很多问与答,我隐隐知晓了四爹是内人党、反革命。冥冥中,我总觉得自己和这个十恶不赦畏罪自杀的四爹有着丝丝缕缕的关系,我怕,我当时非常害怕。终于有一天,养母被逼着说出了我的身世,我的亲生父亲正是四爹。
故乡是什么?
故乡是我那些战战兢兢的日子。
4
我见过两个从不会笑的男人,一个是养父,另一个就是脸上有疤痕的那个男人。男人不仅脸上有疤痕,还没有右臂,样子很像鲁迅。
奶奶虽然没了,但她那屋子仿佛被她的灵魂浸透了。很多时候,我都在那个屋子里。疤痕男人姓巴,是个初中老师,教语文。他的妻子是我的小学班主任,姓李。养母既懒又邋遢,我们家永远是处于一种乱哄哄脏兮兮的状态,李老师一家总是那么整洁干净。每次养父犯病,我都会躲在李老师的家里。这样的日子持续到我小学毕业。
仿佛是命中注定,我上中学的班主任居然是巴老师。那时的社会治安相当不好,我们头道巷就有一个帮派,是以七号院二林为首的斧头帮,另一个是以二道巷一号院南霸天为首的菜刀队。
二林倒是熟悉,小的时候常拖着两桶鼻涕跟在堂哥的屁股后,他们家很穷。听大人们讲,二林的爷爷曾经是梁上的土匪,解放后被正法。两个帮派经常火拼,但谁也吃不倒谁。我始终弄不清楚他们为什么打来打去的。姐姐已经辍学,常常跟二林他们几个斜楞着膀子叼着烟卷立在房山头晃荡。我不知道她靠什么养活自己,但很少回家。由于二林的缘故,养父对她也是忌惮三分。初中快毕业的那一年夏天,养父在二道巷口犯了病,不知怎么惹着南霸天,结果,他被南霸天一伙十几个后生追打到我们头道巷口。
二林这边只有姐姐和另外两个小混混,他二话没说,跑回自家院子里提了一把长长的杀猪刀冲出来。我没有亲眼见到当时的情景,但巷子里地上墙上到处飞溅的血迹,让我知道了战斗的惨烈。南霸天当场毙命,另外还有三个重伤。
姐姐被抓了进去,很快又被放了出来。
我家东边有一个大坑,那是枪毙人的地方,二林就是在那里被枪毙的。公审大会的那天,我也去了,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二林的腿在发抖。我没想到二林也有害怕的时候,姐姐也在那一天失去了踪迹。
瞧着二林倒地那一刻,忽然觉得死有时是那么简单容易,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思索着人为什么活着。我想不通养父为什么活着,养母怎么能够忍受着养父,姐姐活着又是为了什么。想的多了,想的久了,我觉得活着很没意思,有好几次,我都动了自杀的念头。高中快毕业的那一年,养父添了一个毛病,经常喝酒,喝醉了就耍酒疯,打养母。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是逃走,逃到梁上那个亭子里俯视着梁下苍苍茫茫的屋脊,想着生与死这个话题。endprint
一个闷热的夜里,我将将放下书本钻进硬撅撅的被窝,养父那沉重凌乱的脚步声传了来,我知道他又喝多了,忙把头埋进被窝,攥紧拳头,紧闭着眼睛,等待着风雨的过去。
一阵闷闷的打击声伴着养母压抑的呻吟响起,声音和往常不一样,我的心颤抖着,一只手死死攥着被的一角,恨不得有个缝隙能让自己钻进去。猛然,一个冰凉的身子挤进了我的被窝,我不该勃起的地方勃起了。被子豁然被揭开,我下意识地捂住下体,养父的一声嚎叫让我脑袋一片空白。
故乡是什么?
故乡是我青春曾经的勃起。
5
故乡的生活是从倒尿盆、上厕所开始。一道巷子只有一个旱厕,一道巷子里住的人却很多很多。夏日的清晨里,男人们叼着烟,女人们提着尿盆陆续从一扇扇门中出来聚集在厕所的周边。赶上有内急的,往往会喊:“里边的,快点!”厕所里的人也许会说:“急,急你不早点出来。”
上完厕所的人们也不闲着,他们会顺手从自家的煤堆上撮一簸箕煤回去。厕所边上的人聚散的空当,某家或某几家屋顶的烟筒便有了烟,先是稠稠的,很呛,那是在引火。很快,烟便淡了。高低不一的烟筒将北梁人一夜的晦气喷吐出来后,新的一天便在火炉里欢快跳动的火苗中开始了。
我从那个家里逃出后,就在梁上那个高高的亭子里瞧着下边黑黢黢的一片坐了一宿。养父的嚎叫声不时在耳边响起,我用手掐自己的腿,头碰亭子上的柱子。想到天亮以后,我那见不得人的丑事会随着厕所的臭气蔓延到整个巷子里,我再次动了念头,想找根绳子把自己悬挂在这个亭子上。
什么都没发生,太阳照样从东边升起来了。
我茫然地下了亭子,被挟裹在滚滚的人流中又走进了学校的大门。整个上午,老师讲了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到了中午,同学们都散尽后,我依旧对着空落的桌椅发呆。
晚课结束后,我饿得头晕眼花,最大的愿望是等同学们都走后,去捡纸篓里那几块半截的饼子。我的同桌是巴巧珍,她是巴老师的三女儿,见我磨磨蹭蹭的样子,她犹疑地瞥了我一眼。
饥饿将侵蚀我心灵的羞愧挤到了一边,我不停地想着去哪里寻找吃的东西。校园的灯光都熄灭后,我悄悄潜回了教室,从纸篓里,同学的书桌里寻找能吃的一切东西。
夜里,我在教室里几个凳子拼就的床上想起了卖火柴的小女孩。第三日下午,我在菜市场捡吃的东西时隐约看到了李老师。晚上,我潜回教室不久,忽然听到了一阵脚步声。我屏住呼吸躲到墙边。门口传出了开门的声音,我慌忙逃向窗口,准备跳出去。临跳那一刻,门开了,巴老师那张永远不笑的面孔出现在门口。
他只说了一句:孩子,别逃了,跟我走吧。
我的鼻子发酸,眼泪哗地淌下来,蹲在窗台上呜呜地哭起来。从小到大,我很少哭,即便是养父怎么粗暴地毒打,自打奶奶去世后,我就没有哭的权利了。
巴老师走过来轻轻抚着我头说:想哭就尽情地哭吧,哭出来会舒服些。我提心吊胆地在巴老师家住了二十多天,生怕他们一家知晓那个闷热的夜晚。高考结束,我在填报志愿的时候,选了一个不用交学费的军事院校,以我高考的成绩,我完全可以选一个更好的学校。
故乡是什么?
故乡是巴老师那句话,孩子,别逃了。
离开故乡北梁已经二十多年了,我从没惦记着回去看看。有两次出差曾经路过那里,列车停靠那一刻,我的心无由来地忽悠了一下,转瞬即逝。那一刻,心如同一个被摁在水底的开口瓶子,片刻便被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溢满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