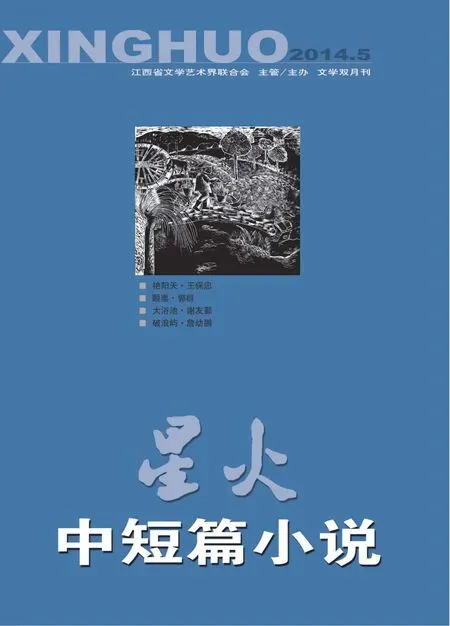小说是一棵树(创作谈)
□王保忠
在《艳阳天》里,我讲述了艳阳、艳天兄弟以及他们的老父亲的故事,兄弟俩的名字组合起来构成的题目给人一种温暖透明的感觉,而小说所呈现的现实却恰恰与此相反,是一种黑色的让人压抑的氛围。或者说,故事黑色的氛围与题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整个故事就在这样的氛围里进行。甚至也可以说,这是一个书写黑暗的故事。
黑色的矿难,给一个普通农家带来的疼痛,悲伤,让人无法乐观起来。
我记起了那年秋天给大哥办丧事,刮了一夜的风。风将枯黄的树叶从地面扬到窑头上,又从窑头上狠狠地甩落下来。还有那两只遗在压水井前的锈迹斑斑的水桶,让风推着从院子的西面滚到东墙根下,又从东墙根推到西墙根下,有时两只桶就碰到了一起,发出很响的撞击声。吊在院当中的那个二百瓦的大灯泡,也在风中晃来晃去的,人走到下面,会扯出一道长长的影子。但我没感到一点惧怕,心里有的只是悲伤。半夜里,我还爬起来走到院当中,将那两只被风推来推去的空桶放进了柴房,又将摆在供桌上快熄了的蜡烛续了一支。
写这个小说时我常记起这个情景。
我让艳天讲这个黑色的故事,讲一场突如其来的矿难和无法逃避的金钱给人的伤害。特别是金钱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破坏,摧残,乃至践踏。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说,小说家有三种基本的可能性:他讲一个故事;他描写一个故事;他沉思一个故事。无疑,昆德拉是把沉思一个故事作为小说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
我不知自己在这篇小说里做到了“沉思”吗?
但有一种感觉是,我害怕把一个故事讲完,害怕讲完后的那种空虚。这使我觉得,很可能我更在意讲故事的过程,沉醉于其中的情节和细节,然而看到艳天重新走向那种黑色的结局时,我又有一种无力的颓败感,我害怕他陷入我不愿看到的那个黑窟窿。但这都是无奈的事,小说里的人物一旦在故事里活起来,其命运的走向就不是小说家能左右的了。
于是我明白小说是一棵树,也是有生命的,叶片是茂密的细节,枝杆是故事和情节,而它的生命却是蓬蓬勃勃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