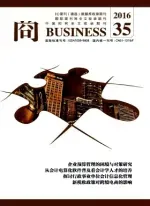浅析《法学总论》与《唐律疏议》的差异
陆涵缘
查士丁尼之前,由于历代皇帝的政策经常变动,执法人员常常感到无法适从。为了巩固君主专制和帝国的统治秩序从而实现其“一个国家、一部法典和一个教会”的宏伟计划,东罗马帝国拜占廷皇帝查士丁尼于在位期间编写了《法学总论》。该书又名《法学阶梯》,取自罗马帝国鼎盛时期大法学家盖尤的同名著作,并以早期罗马诸多法学大家的著作为蓝本编写而成。
当东罗马帝国征服欧洲之时,中华法系中的中国处于该法系的鼎盛时期——唐朝。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法学总论》,笔者认为可以将其同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唐律疏议》进行比较分析。
唐朝的法律处于与道德和合的完善阶段,其标志是礼法结合。唐前期是法律的礼教化,后期是礼教的普通化,“一准乎礼”也成为了《唐律疏议》制定的立足点。开篇《名例》“序”中就提出以“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为指导思想。在具体内容上,婚姻与家庭方面的规定对该特点的体现尤为显著,如《户婚》篇通过礼教确认了家长对家庭财产的支配。
不同于唐律,羅马日耳曼法系下的《法学总论》选择将法律与宗教结合。基督教将衡平的理念引入法定权利和义务中,使严苛的法律得以缓和,这一特点在继承中最为显著。
与唐朝法律相比,《法学总论》除了上述核心差异外,还有以下不同:
(1)该书结构严谨,反映了民法的本质要求,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灵活性,“它的稳定性表现在它的四大类核心结构体系上”;而《唐律疏议》中的民事法律关系内容则主要集中于《名例》、《婚户》等篇,在体系结构上遵循先总则后分则,先实体后程序,反映出法典与社会同构的立法原理。
(2)两者的法律渊源也不尽相同。对于东罗马帝国而言,其法律或是成文的,或是不成文的,“成文法包括法律、平民决议、元老院决议、皇帝的法令、长官的告示和法学家的解答”。而《唐律疏议》则不同,其法源更为多样化,律、令、格、式属于第一层次的法源,而敕令、习俗等则属于第二层次的法源。
(3)形式上,《法学总论》中存在着大量的强行性规范,如在《物的分类》篇中规定“一切河川港口是公有的,因此大家都有权在河川港口捕鱼”。无疑,其规定只是单纯地否定或强行要求某一行为,很少阐述若违反该法律应负的法律责任。而《唐律疏议》则不同,它在相应规则后都附有不同程度的处罚性规则,如“诸占固山野陂湖之利者,杖六十”。这使得法律责任更为具体明确。此外,《唐律疏议》的另一特殊性在于其在法律规定后都夹杂了相应的“疏”,即对法律条文的解释。而《法学总论》对于相应条文的解释更倾向于举例说明,如《遗赠》中记载“例如遗嘱人说‘我以在我家出生的奴隶斯提赫作为遗赠,虽然奴隶并非在他家出生而是买来的,只要能够确认其人,其遗赠是有效的”。
(4)笔者认为两书的内容差异主要体现在物法、人法和涉外法律三大块上。
《法学总论》的后三卷中对物法进行了详细阐述,它将物权分为了所有权、地役权、用益权、使用权等,并对每一项物权进行了以篇为框架的阐述,例如《地役权》篇4条,《用益权》篇4条等。此外,罗马法的债制度也是一个较为复杂、细致、完备的系统,其广度涵盖了从契约、侵权、不法行为直至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等广泛领域。而《唐律疏议》仅在《杂律》等篇中记载了对物的规定,且缺乏“所有权”这一重要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财产观使得人们更多地关注财产的使用而非财产的所有。当时物法的规定以适用为连接点,呈现出以使用为导向的价值取向。在债的制度上,唐律则体现出朴素、简洁、实用的特点,其广度仅涉及契约、侵损等领域。
就人法而言,笔者认为以下几点较为鲜明。
第一,《法学总论》规定“一切人不是自由人就是奴隶”,即罗马法中将人分为自由人与奴隶两种。而唐律中则更侧重于对等级的划分,皇帝、贵族、官僚属于特殊的民事主体,而平民被分为良贱二等。无疑,唐朝的划分更为具体、开放,但仍同罗马法一样存在着鲜明的地位差异性。这种对人的不同划分深受社会性质的影响。唐朝属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因此对人以阶级划分;罗马帝国处于奴隶社会时期,因此将人分为奴隶与自由人。
第二,罗马法不断对家长权进行限缩,至查士丁尼帝时期,家长权已缩小在极狭小的范围内,成为有节制的矫正权和约束权,同今日在限度方面无大的区别。需要提及的是家长权是对男性以及直系女性的专属权利,“你女儿所生的子女,不在你的权利之下,而在他们自己父亲的权力下”。相比《法学总论》,中国的家长权在《唐律疏议》占据绝对支配地位,诸如“诸居父母丧,生子及兄弟别籍异财者,徒一年”。
在涉外方面的法律规定上两书也存在着巨大不同。《唐律疏议》有关涉外方面的规定,真正体现了它那个时代罕见的开放性和先进性。它赋予不同民族、种族和国家的人的权利,达到了古代世界最大限度的平等。在私法领域,唐律允许外邦人士在唐娶妻生子、自由经商并保护他们的财产;公法领域,允许外邦人参加科举。相比而言,罗马法在这方面的法律规定逊色不少。《法学总论》中“市民法与万民法有别,任何受治于法律和习惯的民族都部分适用自己特有的法律,部分适用全人类共同的法律”。
这些差异是由不同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简单商品经济所形成的简单财产关系致使物权、债权法律极其不发达。此外,传统中国重义轻利、官方视民事为“细故”的法律意识,主观上也削弱了对物权、债权的关注。与之不同的是,罗马帝国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相当发达,因此对物与债的规定更为具体。(作者单位:宁波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法学总论》,
[2]张中秋:透视唐代经济民事法律,《法学》,2002年01期
[3]罗冠男:基督教会与教会法对罗马法的影响,《中国西部科技》,2006年24期
[4]王志华:罗马法与唐律——“民法”与“王法”的对立,第四届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国际研讨会,2009年10月
[5]江兆涛:中国古代法与罗马法中家长权之比较研究,《法制与社会》,2008年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