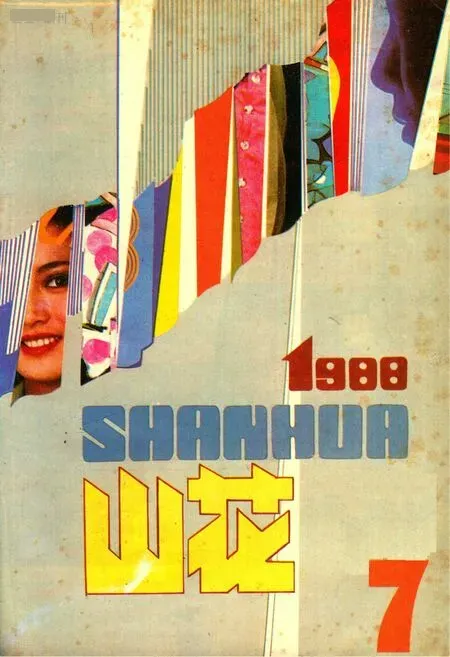没有方向的河流
我站在村外河水的浅处,一直往东南方向行走。日光高远,层层叠叠地拍打下来,水面漾着整片白晃晃的光芒,让我睁不开眼睛。我想那一定是我的童年,我的童年里小伙伴们像木偶戏里的木偶,他们和我处在同一条河,像一起上演一场默片。童年无比寂寞,我们在寂寞中逆流而上,两条瘦腿插在浅浅的河水里,一路挖蟹洞里的螃蟹。最后我们从丹桂房沿着河水一直走到了大悟村,那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水的声音低回,鸟阵铺天盖地地从我们头顶飞过,蹿进绿油油的树林。
在我童年的眼里,大悟村是一个桃花源。我久久地站在浅水里,望着不远处岸上新鲜的大悟村发呆。我认为大悟村成群的房子和树木背后,深藏着一个个谜团。
我随时都能记起我出生在一座叫“枫江”的桥上,那座水泥桥是诸暨通往绍兴的必经的公路。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初八,冬天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我年轻的父亲拉着板车出现在枫江桥上。板车上铺着温软的稻草,稻草上躺着我年轻的母亲,她的肚皮高高隆起。他们是去医院生孩子的。那时候已经黄昏,鸟群开始回巢,一个孩子没来得及赶到医院,就在桥上出生了。这个孩子就是我。
所有的一切,都是在一个大雪封山的日子里,父亲不急不缓地告诉我的。他捧着一只搪瓷茶缸烤火,屋后院里的竹子被积雪压折,发出啪啪的响声。我坐在炉火的边上,想象我出生的年岁,我突然想到,来到人间的那一刻我能听到桥下隐隐的水声吗?
我现在仍然对大悟村心存美好的向往和深深的恐惧,有时候我觉得那个村庄简直不是人间。偶尔,会从村庄的深处骑行出一个穿深蓝色直筒裤的女子,二十四寸的脚踏车,长发披肩,是一九八三年左右的美丽。这样的美丽干净、清爽,散发出肥皂的气息。而我是懵懂、混乱、脏、和自卑的少年。我更喜欢我出生时的那座枫江桥,仿佛在桥上我便能窥见自己的灵魂。我也喜欢在桥上听水声,不时有车子从我身边一闪而过,呼啦一声,像转瞬即逝的妖怪。
我想,我整个的童年时光,其实全被河水打湿。湿得像一望无际的岁月。
我想有时候我是在选择虚度光阴的。
我用我整个的少年上山,像一个去“假壁铜锣”山顶请香的道士。有很多时候,我会长久地守着一汪清澈得让人无地自容的山泉。那山泉来自于山顶的某一个地方,显然我是找不到它的源头的,我对源头也不是十分感兴趣。我只知道它来了,十分安静地俯卧在我的面前。所以我会蹲下身来,掬起一捧水喝。那汪山泉周边,全是潮湿的枯叶和败草,显出阴冷的气味。我把这从上游落下来的山泉,叫成一条山上的河。
我的少年有一个理想是当武侠电影中的侠客,我觉得我要买来一匹马,然后带着一把宝剑行走江湖,路见不平的时候拔刀相助。当然,我也会选择一个酒肆歇息打尖,并且叫一壶黄酒和一斤牛肉。我还有一个理想是当一个游方的道士,穿着带八卦图案的道袍,肩插一把桃木剑。自从看了《西游记》以后,我对伏妖降魔这件事充满了无限的向往。我就在侠客与道士这两种矛盾的职业中徘徊着,一直到有一天离开小镇枫桥。
我觉得我就是那汪隐秘的山泉,我都没有搞清楚那些败叶的脉络,我只知道它们阴暗与潮湿。我走到太阳底下的时候,我的少年变得阳光起来。我的眼睛长得比较细,我眯上眼睛的时候,差不多就是闭着眼睛。在我闭着的眼睛里,晃荡起来的镜头是狭窄细小的山泉从天而降。
少年辰光,一直有一条河水在我的梦境里游动,像招摇的水草,像村庄上空的炊烟。
1989年春天我和80位枫桥新兵出现在轮船上。那轮船就行驶在长江,它从上海十六铺码头出发,目的地是江苏南通。江风阵阵,我假装玉树临风地站在甲板上,突然觉得长江不过是一条宽阔的河流。
我们来到了南通一个叫环本的地方。这个地方是江苏省第二十一劳改农场,我们在这儿执行看守犯人的任务。那是我最美好的三年光阴,草绿色的军衣下包裹着混沌,粗糙,力量,甚至弥散着汗味的青春。我们有时候选择喝酒,有时候选择在操场上的单双杠边上谈论家乡的姑娘,或者是环本镇上一个卖包子的小嫂子。
环本这个地方的四周,是大片的麦田和油菜。如果你在春天潜行,你一定会被整片的庄稼吞没。1989春至1991冬,我一直乐此不疲地做着这件事,我真希望长久地行进在充满植物气息的庄稼地里。那摇晃的麦穗或者油菜花,有时候会让我激动得想哭。我想我会不会这样一直都走不到头,走到了荒无人烟的地方,那儿野麦生长,或者有一头河水边的小鹿……我认为我必须弄清楚,你也一样,你也得弄清楚。哭是一件美好的事,哭不是流泪,流泪没有高潮。
环本农场的更远处,就是黄海的滩涂,滩涂上爬行着一种奇怪而丑陋的独脚蟹。三年的光阴,让我对环本了如指掌。我十分热爱那儿纵横的沟渠,认为那是一种平原上的河流。这样的沟渠中盛产小龙虾,红或黑的笨重的壳,长得一点也不秀气,仿佛是镇上的憨大。我们常把它红烧了,放姜和葱,少许酱油,用它来下酒吃。我们用它下酒的时候,谈论的仍然是家乡的姑娘。
我相信世上所有的路其实是相连的,如同世上所有的河流,会有同一个隐秘的源头。离开南通的时候,我坐上了汽车。我记得那是冬天的一个夜晚,天还没亮,我看到了营房胖墩墩的,像黑色而且发福的妖怪。新兵们敲脸盆欢送我们,他们因此而欣喜,从此他们不用再受老兵的压迫。和当年入伍时的来路一模一样,下车后我们登船,在长江某条船的甲板上,我觉得这条宽阔而绵长的河面上,阳光正在翻晒着我那三年被完全虚度了的光阴。
我出现在丹桂房村外的土埂上。如果我说的一切是一部电影,那么镜头是这样的。一个叫海飞的退伍军人,穿着旧军装走在田野,他给你看到的只是背影。他的背影越过了阡陌,进入村庄,然后出现在一幢老式的民居前。他举手敲了敲门,门打开了,一个老男人的脸呈现在我们面前。
他是我的父亲。
2005年初夏,我开始在杭州段的运河边上行走。每天晚上我都要在石板铺成的小道上走一个小时。我走进那些若隐若现的灯光里,我穿得有些不伦不类,绿色旧军裤,白的广告T恤,运动鞋。我知道汗水把我的衣裤打湿。我喜欢那条河,是因为运河的水面上,总是有运货的船只经过。那些船上晾着衣物,可以看到有人在灯光下的小房间里看电视,一条狗沿着船舷走来走去,装着视察的样子望着运河两岸。我一直都在猜想着船上的生活,这些船有些来自于绍兴,有些来自于诸暨,或者别的什么地方。他们有好多是抵达盐城的,我从未到过盐城,只知道有一个战友生活在盐城。战友之间,有一条运河紧密相连着,但是战友本身却不联络。一晃就是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在想,人生又有几个二十年,是可以用来挥霍的?
现在我选择在杭州城西居住,每晚走在余杭塘河的边上。我知道我的身体已经开始发福,有好多年轻的女孩叫我海叔甚至海爷。既然作为长辈,我得有所修养,并且要有一定的温文尔雅。但是当我走在余杭塘河边上时,我的脚步风快,甩手甩脚横冲直撞,走路的姿势一定是不雅的。我仿佛是在追着一条河流西去,难道我想和河流赛跑?
我不知道运河的方向是哪儿,我想既然是京杭大运河,那一定是会通往北京的。我感兴趣的是运货船上的人生,我奇怪地想,怎么会有一种人,是可以生活在水上的。
光是“苏州河”三个温文尔雅的字,足以令我想入非非。我对她的痴迷,来自于一部同名电影,以及各种传奇。所以她屡屡进入我的小说中,无论是《向延安》《麻雀》还是《捕风者》,苏州河都是一个使用频繁的地标。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方向,后来百度以后我终于明白,苏州河流向是从太湖瓜泾口,一直注入黄浦江。
1937年苏州河畔的炮火明亮,淞沪会战如火如荼。国军谢晋元团长率一支孤军驻守四行仓库,那时候日军攻势凌厉,上海童子军战地服务团的十四岁女团员杨慧敏冒着横飞的子弹游过苏州河,给那支浴血中的孤军送去了青天白日旗。旗帜飘扬,苏州河与战事有关,与一个少女的人生有关。她的人生方向从此改变,此后她去了重庆,又去了台湾。她像一条苏州河的支流,流向自己约定俗成的方向。
我想象地球上的水们,大多是没有方向的,就像地震后海面会出现一座小岛,就像河流的方向会发生变化,就像我们的人生,分分秒秒都会有各种突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和蚂蚁没有什么两样,轻飘飘的一阵随随便便的风就能把你吹走。我们的人生像是没有安装刹车片的河流一样,翻滚着向前,带走泥砂,淹没一棵树,一片庄稼。
有时候我喜欢的一种状态是,河水淹没了好多树。这些树从腰部开始露出水面,仿佛是长在水上似的。这样的场景容易让人觉得,河水以下其实藏着许多的秘密。
我喜欢的另一种状态是坦露的河床。我觉得那样的河床几乎是个老年人,他丑陋而本真地在天空下晒着太阳。他是有资格丑陋的,那是另一种美。
我给小说中出现的一匹马取名大河,它最后死了,它是躺在江南祠堂的地上合眼的,像一个人的死亡,像一条河的干涸或者消失。我真喜欢它的名字,它叫大河。
我认为既然说到河,我们是必须要说说溥仪的。很多年前的一场电影,叫做《末代皇帝》,苍凉得让人胃酸。我记住了电影中的道具蛐蛐,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一定也会和我一样对蛐蛐念念不忘。那是一只神来的昆虫,一只妖怪形的生物,是我喜欢的太过艺术的蛐蛐。我还记住的,就是一个人的名字,他叫溥仪。
其实在很早以前,应该是在一九八六年以前,我躺在上海杨浦区龙江路75弄12号一间小房子的大钢管床上,翻动一本叫做《我的前半生》的厚书。那是我外婆的家中,外婆像苏联老太,肥胖敦实,头发花白。住在这样的屋子里,我感到幸福,我就像出国到了苏联一样。而溥仪莫大的幸福,不是登基,而是被从战俘改造的劳改农场里释放。他变得如此的谨小慎微,所有的棱角都被国家机器的轻微举动磨平。
如果他是一条河,他一定也不知道,他会流向何方。皇帝和战俘是他的双重身份,很难搞得清楚,他快乐的时光是在他人生的哪一刻?我喜欢他的那种脸型,那种脸型接近民间,不像皇帝,那么的凡俗,但又仿佛隐隐的有些皇家之气。我在一部黑白的纪录片里,看到他被战俘营释放时的欣喜,也看到他在狱中的谦卑。所以只要你是一个凡人,一定会被各种打压摧毁。摧不毁的是孙悟空,但孙悟空谁也没见过,也根本没有真正来到人民中间。
这让我想到了另外的一些人事。小凤仙的后半生如此的颠沛,读到她在东北度晚年时的悲凉晚景,不禁让人悲从中来。大流氓黄金荣殷勤地在上海扫大街,这个不可一世的魔王,在暮年时分把扫帚玩得风生水起,最后死得十分民间和苍凉。他死在他发迹的上海。另一位大享杜月笙死在了香港,可以想象他逃离上海前的那种悲苦心境。八千湘女上天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轰轰烈烈敲锣打鼓以后,是漫长的平静和压抑,甚至苦难。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命运这条河游向河方,哪一个点才是转弯处;哪一个点是高坡的跌落,状如瀑布;哪一个点,又是一片荒凉。这芸芸又芸芸的众生里,那个丹桂房村庄最著名的懒汉海飞,后来拉煤摆摊,或者在诸暨县城的街头悠闲地晃荡,多么像一粒忙碌的灰尘。
我们都是被命运这条河裹挟着前行的人。我们来不及去改变命运,就发现自己在虚度光阴以后,在三杯黄酒一轮好月以及清唱一曲以后,垂垂老矣,老得须眉皆白,老得苍凉似海。
很多年后我选择码字谋生。女儿渐渐长大后,我的书房被她无需理由地占据,像一个理直气壮的霸王。渺小的我只好搬到了露台改装的另一间书房。那是一间玻璃房,三面通透安装着明净的玻璃,白天拉着厚重的窗帘,夜晚则完全打开。所以我能看到更多的夜色,以及远远近近的灯光。夜深人静,夜色像一只黑色的大鸟,在我的四周蛰伏着。如果有雨来临,雨点就敲打在玻璃房的屋顶,声音急促得像鼓点。那时候我被这样的雨声笼罩,密集而响亮,我喜欢这样的响亮。这大概是另一种嘈杂的安静。我把笔直落下的雨水想象这是一条来自天上的河,无比忧伤地流向了人间。
我愿意被这样的雨阵和雨声笼罩,以及包围。窗明几净,一株普通的龙舌兰笨拙而鲜活地生长在地板上,夜色清凉像是薄荷糖的滋味。我在这间简陋如我的人生的书房里,生产剧情,编织恩怨,并且为之矫揉造作地歌哭。我想,作家的人生不尽相同,张爱玲为了寻找战乱中的胡兰成,从上海跑到了诸暨,而胡兰成在那个叫斯宅的小地方,已经搭识了已故同学之妻。这样的故事比较寻常,几千年一直发生着,不寻常的是那时候是战乱。我喜欢战乱时期的黄昏,比如远处有隐隐的炮声传来,近处的野花在微微地颤动,乌鸦在一棵乌桕树上鸣叫。甚至有硝烟因为被风吹送,而向这边飘来,硝烟中混和着的是火药和硫磺的气息。张爱玲注定是一条悲伤的河,一直到客死异乡,河床干枯。如此说来,那么古龙是不是狂放的河?海明威是不是野性的河?杜拉斯是不是爱情和糖果之河?川端康成是不是清奇之河?
不管是哪一条河,今夜都密集地汇集在我的面前。此刻是凌晨二点十九分,杭州的金汇大厦十七层1705房间,我在码字,以及思念那些先行的作家,像思念一些远去的亲人,像想象一条条纵横交错的白晃晃的河流。多么荒凉。
写作是一个奇怪的行当。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在做了如此多的粗俗工作以后,选择这一行当。我插秧割稻,下河捕鱼,十四岁那年我开始去河里捞沙,那是需要把整个人泡在水里的工作,这让我后来感觉到关节不是那么健康。我当兵,拉煤,当保安,摆小摊,办厂报,做水电安装工人……我尽可能把我的许多行当想象成充满温情的工作,比如想象一下,其实这些工作也充满着相对的艺术。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还是身不由己地与文字息息相关,又爱恨交加。如果我是一条河,我该是一条什么样的河。
除了写作以外,我必须要说说我的父亲。父亲十分荒凉,这条已经进入暮年的河流,他的流向一成不变。不见涨潮,也不见干涸。我又突然想见,在我女儿的眼里,作为父亲的我该是一条哪般形象的河流。或者,她根本不会把我想象成河流,她会想象我是小溪,小沟,甚至自来水龙头下挂着的一滴欲滴未滴的水。
我为什么要说说父亲,是因为我觉得父亲大概就是我距离最近的源头。年轻的时候,他是丹桂房村第五生产队英俊的植保员。后来他赶猪去镇上叫卖,他也贩卖红枣,农忙的时候跌跌撞撞地在农田里插秧割稻。他过着中国普通农民在过的日子,我想他可能也对我是充满好奇的,他一直搞不懂我的职业,后来慢慢懂得他的儿子是会写东西的。但是,他仍然搞不明白的是,写字怎么也能够养家糊口?
现在父亲这条无力的河流,生活在上海闵行区我妹妹的家里。他学会了带孩子,并且在小区的空角落里种植青菜、萝卜和玉米。他在老年之际突然有了一个上海户口,但是他一生都不会被人认为是上海人。我去上海看他,好多时候,他坐在沙发上捧着茶缸一言不发。那幅镜头很像是一张静止的照片,光线把父亲斜斜地切开。父亲一动不动,我却感到了蚂蚁啮咬般的疼痛。
我想,多年以后我就是他的翻版,翻版得残酷无情,翻版得让人骨头疼痛。
春天就要来临的时候,我特别渴望迅速拥有一支桑树皮搓成的鞭子。我赶着水牛走向明晃晃的水田,或者赶着一头母猪去镇上找约克公猪配种。这是一种没有天理的生意,母猪最大的悲哀是倒贴着钱去赔公猪睡觉。我还渴望有一把竹筒做的水壶,可以让我在路上解渴;一辆板车,可以拉满我一车的梦想。我真想在庄稼地里躺下来啊,地面微凉而柔软,植物在我眼前摇晃,把太阳摇得七零八落。风一阵一阵吹来,世界多么宁静。
那就躺下来吧。躺在潮湿的地面上,我整个的生命随即与大地之气相连。地气透过背部向内传达着阵阵阴冷的潮气。我合上眼睛,就像回到了蛮荒的远古。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年代,人们腰间围着树叶,手中持着长矛,奔鹿,野狼,蛇,狐狸,以及地上次地呼啸盛开的野蘑菇,让这个世界彩色而美好。
我躺在野地上,我就是一条没有方向的河流。或许有一天我会成为河床,但我至少也以河的形式存在过。此刻,请允许我欢叫一声,并开始想念小说中那匹叫大河的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