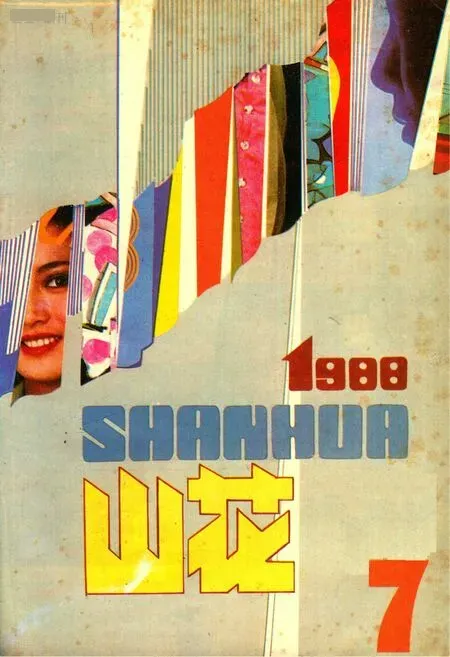离别的一种
魏荣钊
大雨滂沱,睡不着觉,总觉得有什么事会发生。
老公侧身呼呼声很响,雷打不醒。我知道他已精疲力竭。由于孩子原因,老公馋了很久,想动而一直没能动我,难耐有点冒火。晓得他再也忍不住了,下午我把三岁儿子送到了父母家,决定满足他一回。外面的雨声一阵强过一阵,事毕,老公滚下身来睡得酣畅淋漓。按说,雨夜是最能让人安静,最能让人睡好觉的,可不知怎么,我心里总是慌慌的,无法入睡。
快凌晨一点了,突然,放在床头柜边的手机铃声骤响,把呼呼大睡的老公惊了一下。我探身拿起手机,摁下接听键,母亲在电话那头,急促而又悲伤地说,贝贝,快过来,你爸爸走了……我一下子懵了,下午送孩子到父母家时,父亲好端端的,虽然他患有哮喘病,但精神尚好,才几个小时过去,怎么可能?我不敢相信,可我还是哭了。我的哭声惊醒了老公,他跃起身说,你怎么啦,三更半夜的搞哪样?我哭着说,快起来,我爸爸走了。老公愣了一下,滚下床说,怎么会?又没生病,好好的怎么说走就走了,不会是脑溢血吧!
我和老公急急走出门,整座城市几乎被雨和雨声淹没。街道上看不见人,也没有出租车来往。我们站在小区门口焦急地等。一会,一辆出租车冒雨开到小区大门,小区的邻居刚下车,我急忙拉着老公钻进车里。司机说,雨太大,不跑了。我急了,说,求你送我们一趟,我爸爸死了!司机再没吭声,一踩油门顶着哗哗的大雨把我们送到了父母居住的林城老教师楼门口。
雨一直没停,我和老公不顾大雨倾盆,下车向父母居住的楼奔去。门开着,母亲抱着我三岁的儿子坐在门口,急得不行,一见我们就哭着说,贝贝,怎么办啊,怎么办啊……我顾不得母亲哭诉,直奔父亲常住的房间,却不见父亲。我转身出来,又跑到母亲常住的房间,还是没有看到父亲。母亲见我到处找父亲,半天才说出话来:你爸爸走了。我问,走哪里了?母亲说,他出去了。我说这么大的雨,他去哪里……?
我这才明白,父亲没有死,而是出了门。可这么大的雨,他去哪里呢?
母亲说,她大约是十二点钟的时候,醒来见屋外的灯光亮着,以为是父亲上厕所忘了关灯,就大声喊叫父亲,可不见父亲应声。母亲就起来关客厅的灯,顺便走进父亲的房间,然而房间的灯关着,走进了才发现父亲并不在。母亲急了就到处找,厕所里、厨房里找了个遍,又下楼找,还是不见父亲,急得不行,才给我打的电话。
父亲到底去了哪里?这么大的雨。
父亲今年刚满七十一,虽说身子骨还算硬朗,但他不善交际,所以朋友不多,说得来的人就更少。他是林城三中退休老师,当年书虽说教得不错,相当受学生欢迎,也给学校争得了不少荣誉,但他性情孤僻,和学校老师几乎没有深交。如今,父亲退休已整整十年,平时很少串门,兴致来了顶多到林城清明河岸走走,或去一趟姑姑家。他没有什么爱好,唯一爱好就是看书看电视,偶尔走到对面和开烟酒铺子的王老头下下象棋。年轻时的父亲常写些随笔散文之类的文章投寄刊物,但发的不多,因为他的文字风格偏于悲观、晦暗,很难被编辑采用。退休后,几乎不写了,除非有人约他写。我苦思冥想,这么大的雨,父亲能去哪里?他年轻时都从不在外过夜,除非出远门,如今这么大年纪了,在这么大的雨夜离家出走,况且身上穿的是单薄的睡衣睡裤,没带一分钱,难道去开宾馆不成?太奇怪,太不可思议了。头都想大了,我们都没想出父亲到底去了哪里以及离家出走的理由。
我拿起手机拨打父亲的号码,却处于关机状态。母亲说,你爸爸的手机在我这里,他没带走,关机放在床上的。
我又拿着手机拨通姑姑家电话。姑姑是父亲唯一的妹妹,也是他在林城的唯一亲人。如果说他要去别人家,最有可能是去姑姑家。
父亲从小在林城郊区长大。我长大后听他说,“大跃进”时期,他的父母,我的爷爷奶奶就死了。死因很简单,没有饭吃,加上生病没钱医治,爷爷奶奶前后一年就走了。爷爷奶奶去世时,父亲和姑姑都未成家。还好,那时父亲已高中毕业安排在郊区的一所学校教授语文。高中生教初中生在那个年代很普遍,对于好学上进的父亲来说,教初中语文对他而言,简直不费吹灰之力。他教的学生十分优秀,年年获得教育部门表彰。改革开放之后,父亲被林城市三中领导看中,调了进去。父亲为人为事细心认真,而且胆子小是大家公认的,他走路都生怕树叶子掉下来打着耳朵。父亲调到林城三中上高中语文课,高中生上高中生的课按说是不符合要求的,但父亲就有这本事,教的学生成绩一点不比其他老师的差。不过为了装点门面,后来父亲还是读了个函授大专。
父亲结婚晚,他先给姑姑在林城找了份工作,让姑姑进了酱菜厂当工人。姑姑结婚一年后,父亲认识了我母亲,又过了一年,父亲才和母亲走进婚姻的殿堂。姑姑对父亲很尊敬,经常给父亲送好吃的,父亲没得哮喘病之前,每年过年都要送他一瓶茅台酒。总之,姑姑对父亲要有多好就有多好,尤其是这几年,姑姑三天两头都会来看望父亲。
姑姑在电话里得知哥哥不见了,急得说不出话。尽管雨大夜深,姑姑带着表哥很快开车赶来了我们家。夜深人静,大雨滂沱,我,我母亲,还有赶来的姑姑和两个男人在几十平方米的屋里急得团团转。我们又开始在家里搜寻,希望能够发现父亲出走的蛛丝马迹。
几乎搜遍了所有房间,包括厨房和厕所,仍然什么都没捞着。正在我们商量着准备去清水河岸寻找父亲时,母亲在父亲房门背后发现了一张二指宽的小纸条,纸条上是用铅笔写的一行数字。母亲拿出来想了半天,突然想起了这是父亲工资卡上的密码。
母亲说,以前父亲用的是存折,前几年为了方便就让银行添了张银联卡,虽然简便了,但父亲害怕丢失,就把卡交给母亲保管,父亲用钱时才管母亲要卡。
对纸条上的数字,大家心照不宣,知道它意味着什么。但是大家都没说出来。我心想,就算纸条是父亲和我们永诀留下的遗物,那他为何要这样做?
我们就叫母亲好好想想这几天父亲有些什么反常?母亲着急得什么都想不起,她坐在凳子上一筹莫展。过了一会,母亲倏地想起了什么,她说,对了,晚上吃饭时,外面下着大雨,父亲犹犹豫豫地对她说,他腹部有个包,硬梆梆的,但不痛,只是摸着不舒服。母亲正想问他要不要紧,父亲却把话题岔开了。母亲心想,等明天再提醒父亲去医院看看。
表哥急切地问母亲,舅舅提了几次那个包?母亲说,就第一次听他说了一下。是啊,我结婚后虽然住在另一个小区,但至少一个星期要回家一趟,从来没听父亲说哪里不舒服。即使有个包又有什么?何况不能确认那个包就是天下没治的可怕东西。
这不可能证明是父亲出走的原因。这时,姑姑坐在一旁自言自语道:那他为什么要把纸条丢在门背后啊?
母亲说,也许是随手丢的呗。表哥说,可能是风吹到门背后的吧。我老公说,肯定有原因,他怎么不放在桌子上,用什么东西压住?
我暗忖,父亲如果是因此想这样离开我们,那纸条一定是他有意识丢在门背后的。这样,可以让他有更充足的时间走到他想要去的地方。
想归想,老实说也只是一种猜疑。谁知道父亲到底去了哪里?按正常思维,我们决定到清水河岸找父亲。尽管雨还下着,但我们还是打着雨伞出了门。我们让母亲和姑姑留在家里,一来因为她们年纪大了;二来万一父亲踅回来也不至于没人开门。
清水河虽然叫河,其实只比溪大一点,要是没有堤坝,人们可以在河里横冲直闯。清水河弯弯曲曲穿过林城,通过城区的长度大约三四公里,在这三、四公里的河床上有三道堤坝。林城是山城,东去的河床呈梯形下降,为了让清水河看上去像一条河,林城很多年前就筑起了这三道堤坝。有了堤坝,河水就涨得很高,最深的地方可能有六七米,因此常有人不幸死于河中。死法当然各不一样,有的是在河里游泳丢命;有的是不慎掉进河里淹死;还有的是一件事想不开自愿跳进去的。
我和老公、表哥打着雨伞照着电筒在清水河两岸寻找父亲,我们都希望父亲躲在岸边哪个涵洞下,或是迎着夜雨浪漫地行走在岸边的路道上,哪怕是和一个年轻女人。不管父亲因为什么理由躲在这里,或是因为什么隐衷在雨中行走,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找到父亲,见到他的人。不然,我们会很伤心,感到失败。我们的衣服早已淋湿,但我们还是坚持找遍了清水河两岸。我们尤其重视三道堤坝,我们都不吱声地在每道堤坝两面细心察看,反复照着电筒在堤坝上下扫射,但我们最终还是没有发现任何疑点。即使我们内心都不希望看到不愿看到的一幕发生。
我们在几公里的河段上寻找了三遍,直到天亮,才带着一身疲惫回到父母家中。母亲和姑姑也一夜未睡,她们坐在门口,眼睛红彤彤的,显然是哭过。她们巴巴地看着我们无功而返,极度悲伤在脸上流转。
已经是早上上班时间了。我们来到林城三中,没头没脑的在学校周围走着,引起了学校几个老师注意,问是做什么的?我们说,不做什么,想看看。结果被老师叫保安赶出学校,我们不愿说父亲以前是三中老师,也不愿告诉他们父亲出事了。我们离开学校,我提议去父亲在三中教书的同事家问问。父亲退休后和学校两个老同事偶有交往。我和老公好不容易找到父亲其中一个同事家,当我们谈到父亲昨晚不辞而别的情况时,这个和父亲差不多年龄的老人十分惊讶。他说,韩自立这个人挺好的啊,我们一起教书,他的性格都是不温不火的,怎么会这样呢!想了想,老人又自言自语说,不过,这个老韩啊,是有点不合群,虽然没见过他发过火,但也很少见他和几个人来往……老人还说,你们去老李家问问,他和李进尚老师的关系也还马虎,看看去他们家没有?
唉,怎么可能呢,深更半夜,那么大的雨,他跑人家家干嘛?不过是找找而已。我们没有去李老师家,而是给李老师打了电话。李老师说,老韩从来没来过我们家,我们家门朝东朝西他都不晓得,怎么可能来家里。
返回父母家时,对门烟酒铺子的王老头已经开门了。我站在门外问,王老伯,昨天我爸爸和你下过棋没有?王老头说,是中午杀了两盘,他输了,有点不高兴。怎么了?贝贝。我说,我爸爸昨晚走了。王老头惊讶地说,唵,昨天都好好的,怎么说走就走了,什么疾病啊?我说,王老伯,不是那意思,我爸爸是真的走了,离家出走了。这时,王老头更加惊讶,他说,昨晚下那么大的雨,一个老者会跑到哪里去啊!
我们离开王老伯门店时,王老伯在我们背后自言自语说,这个韩老者,做些事情怪怪的,硬是让人想不明白。
再也不知道去哪里找父亲了。表哥说,去报警吧。
我们来到辖区派出所,派出所民警给我们做了简单的笔录,然后叫我们回家,说他们马上派人巡查,一有消息马上通知我们。
回到家,母亲给我们每人煮了碗面,我只吃了半碗就吃不下。老公饿得不行,把我吃剩的半碗也吃进了肚里。吃完,我们又分头去清水河上找父亲,都暗自坚定父亲是跳河了,但又说不出合理的理由来,只是这么怀疑。我们分头在城区内的河段上继续寻找父亲。母亲和姑姑年纪大,就在离家最近的河段上找,我、老公、表哥就各自在上游和下游两岸寻。我们想,要是父亲真的跳了河,有可能被冲到河堤上,我们一致认为,三道河堤尤其要细心查看。
我们又找了父亲一个上午,然而还是什么蛛丝马迹都没发现。
都市报关系近的几个同事得知我家出事后,也跑来帮我们一起找父亲。可八九个人找了一下午,仍不见父亲踪影。晚上,我在都市报第二天的报纸三版配照片登了一则寻人启事。
我们坐在家里等消息,希望有父亲的喜讯传来,哪怕是一丝线索也好。可是,从白天到夜晚,整整二十四小时过去了,什么音信都没等到,包括派出所那边也没情况。
第三日,我们又继续在清水河上寻找父亲。母亲对我们说,人跳河死了,先是沉到水底,七天内尸体一定要浮现。我们就按照母亲的想法,白天夜晚轮流在三道堤坝上排班等父亲浮现,如果父亲真的是跳河自杀的话。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完全打破了禁忌,觉得父亲肯定是死了,至于是什么死法,我们比较统一的看法是,跳河自杀的可能性最大。因为我们家离清水河近,直径距离不到三百米。如果父亲真的是走了自杀之路,跳清水河是最方便的。可是,对父亲为什么要走这样的路,却没有一个人能讲出理由。
我常听母亲说,父亲和她结婚以来,关系一直不错,虽不敢说如胶似膝、心心相印,但在我的记忆里,却很少见他们吵架,打架在我记忆里一次都没发生过。父亲也不是那种沾花惹草的男人,年轻时都没听说他有过什么风流韵事的绯闻,老了就更不用说。父亲属于正统的人,那个年代的人都比较正统,很少见那代人做什么出格的事。父亲只有我一个独姑娘,我不敢说是父亲的掌上明珠,但父亲对我的爱那是没得说的。天下的父亲很少有不喜欢女儿的,更何况我和父亲能够交流。我和父亲从小就说得来,我大学读中文专业都是遵照父亲的意见,大学毕业后,父亲又建议我去报社当记者,他说,记者可以了解社会,知道很多事,别人不知道的记者可以知道,别人去不了的地方记者可以去,当记者可以丰富人生阅历,为老百姓做点事,几年后即使想改行,也来得及。
父亲是一个很开通的人,很少对人武断地强加自己意见。父亲之所以看得开,是因为他从小就饱尝父母早逝的辛酸苦辣。他曾经和我聊天时谈到,人生实际上都是空的,跟做梦没有区别。他觉得,现实中所经受的一切和做梦没什么两样。他还说他不相信生死轮回,也不相信来世,死了就是死了,老百姓说人死如泥就是那么回事。他还曾经开玩笑说,到他动不能动、吃不能吃的时候,就知趣地自觉接受阎王的邀请,到那个时候,他就提前回到老家乡村找棵树,把自己葬身树脚,图个干净利索。他认为,那样的归宿清静而最有诗意。那时,父亲是笑着和我说到这些的,我想父亲无非是在开玩笑,说说而已。但今天想来,父亲的离走确实与他过去的想法似乎不无关系。
可我想不通的是,即使要这样走得清静走得干净,为何就不留封遗书呢,哪怕几个字也好。这又成了我怀疑父亲的自杀动机。他要是早有准备,起码会给他心爱的女儿我留几句话吧。难道父亲出自他杀?这种可能性更小。谁杀他呢,一个老头儿,穿一身睡衣睡裤出门,身上分文不沾,杀他又有什么用?
所有的人脑壳都想痛了都没想出父亲出走的最佳答案。有人说,也许我们想一辈子也想不出真正原因,也许老人的出走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惊心动魄。
一个星期过去了,派出所没有任何消息,在报社登的寻人启事没有一个电话打来。我们一家人铁了心认定父亲已经死了,至于怎么死的,都基本认为是跳清水河了,至于为什么跳清水河,永远都是一个谜。
尽管父亲走得很绝情,但我们还是在家里给父亲设了小小灵堂,给他老人家上亮、供饭,给他守七七四十九天灵。
和我要好的朋友们都替我感到难过,他们展开超凡的想象,有的说,父亲可能是修道成仙上天了,试想,早不走晚不走,偏偏在那么大的雨夜走得无影无踪,不是升天还能上哪里?这只能是想象,人类现实生活是不可能发生的,除非是神的世界;有人假想的更离谱,认为父亲年轻时和一个姑娘有生死之约,生不能在一起,死在一起。这一夜正好是他们年轻时践约的日子,于是他们走得悄无声息。想象虽然悲情美丽,但非常荒唐,这种故事只可能出现在小说里,何况我们也没有听说有老太婆失踪。还有几个朋友,更是瞎乱想了一通,但都不着边际,根本不符合常情常理。
父亲走后的“二七”那天夜晚,我做了个梦,梦见父亲和我坐在林城清水河岸的一个小亭子里畅谈。父亲叫我不要多想,之所以没有跟我道别,是怕我伤心,人生自古伤离别,悄悄离开是大家都不用麻烦的事情,虽然对不起我,但也没什么值得伤感的。父亲告诉我,他半年前就得了绝症,他独自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已经晚期,没治了,最多半年时间。那个晚上,父亲说他突然感到疼痛难忍,觉得应该走了,再不走,就要麻烦我和妈妈了。他说,为了不让母亲知道,他忍着疼痛假装若无其事,等母亲熟睡后,趁雨下得哗哗响,就摸出了门。扶风山在林城的东北面,是一座小山,虽然被钢筋水泥围得水泄不通,但山坡上古木参天,清早和傍晚有很多老人都喜欢爬到上面静坐、聊天或锻炼。之前,他花了好几个夜晚在扶风山顶一棵盆粗的松树脚挖了一个洞,并在洞口安放了一块石板。他说,这棵松树和这个促狭的小山洞就是他最好的归宿。当他走出家门,雨突然小了,好像连老天爷都对他这种离走情有独钟。他摸索着走过马路,穿过一幢幢楼房,背后有一辆出租车驶过,一束灯光扫射过来,遮住了他的视线,幸好一转眼就消失了,他突然感到生命就和这束灯光一样,该消失的时候就应该毅然决然,不必留念和顾盼。他从小巷子里走过去,一眨眼就来到了扶风山脚下。这时,他突然有些兴奋,腿脚也有了力气,不一会就爬到了山顶,就像年轻时一样轻快。他在洞口坐下来,看着林城街道上夜灯闪烁,突然流下了眼泪。他突然觉得自己有点不近人情,觉得这样匆匆而别,有些对不起我这个女儿。可是,他说他必须这样离开,只有这样离开才是最舒服和美丽的。他坐在洞口望着山下的林城很久很久,终于有些累了,于是吃下带在身上的一把安眠药,义无反顾钻进了自己提前掘好的山洞,封上石板,然后很快就睡着了,睡得很香很安宁……
儿子突然几声哭闹,把我惊醒,醒来发现是一个梦,十分沮丧,我很想再睡过去,再梦见父亲,可是怎么也睡不着,于是就一直想着梦里的父亲和他说的话。
天亮后,我什么也没说,一个人悄悄爬上了扶风山。我挨着每棵树脚寻找夜里的“梦”境。我既害怕是事实,但又希望是事实。山上有很多老人,有的在打太极拳,有的在唱歌,有的在聊天,根本没有在意我的到来,只有一对三十岁左右的年轻男女对我的行为有些防备,我想也许是他们有些行为不轨吧,所以才对我的举动有所警觉。
我根本不顾他们的眼神,一边找寻一边想象着某棵树根下的奇迹,心神不宁,但还是查看了几十棵大大小小的松树根和别的树根。最终失望了,根本没发现一棵树根松土的迹象,更没发现有立起来的石板或细小的洞穴。
我有些累,在一棵松树下坐了好一会才走下扶风山。刚走到山脚的小巷,突然遇上迎面走来的母亲。我发现,母亲想躲开我,可是已来不及了。我问母亲去哪里?其实是明知故问,母亲无疑是要上扶风山。母亲没有回答我,反问我一大早上山做什么?我一急,竟然说看一棵树。话一出口,我自己失笑了。
一个多月过去了,还有人对我说,也许哪一天你爸爸突然就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