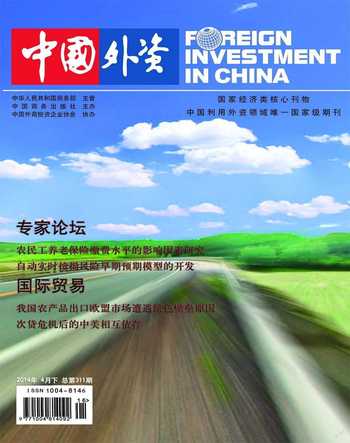中国撤回《CISG》第11条保留的探析
摘要:中国于2013年1月撤回了国际贸易合同必须以书面形式订立的保留。一方面,撤回保留适应了国际贸易趋势,促进了我国贸易的快速发展;但同时,撤回行为也给我国外贸企业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我国外贸主体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加以应对与适应:如建立境外信息情报管理组织、建设法律风险管理体系、注重电子订约的管理以及在实际业务中充分利用现有法律法规对法定书面形式欠缺的合同进行补救。
关键词:《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合同形式 保留
Abstract: China withdraws its “written form” declaration in January, 2013. On one hand, withdraw of the reservation fits the tendenc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hich woul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ommerce. On the other hand, it brings challenge to the Chinese foreign trade enterprise. The foreign trade players could cope with and adapt to this change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or example, establishing foreign information and intelligienc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establishing legal risk management system,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management of electronic contracting, and taking full use of current law to remedy the contracts which are not in the form of writing in practice.
Keywords: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the form of contract reservation
引言
2013年1月16日,中国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一份文件,撤回对《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合同形式必须以书面形式的保留 。公约为国际货物的买卖提供了一个平等的、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统一的框架。因此,《CISG》被视为国际贸易法中的核心条约。中国于1980年签署了该公约,并与1986年提交核准书时提出了对《CISG》第11条的保留,即合同形式保留,声明国际贸易合同必须以书面形式订立,以使《CISG》的规定与国内法的规定相一致。后来,因中国开始施行新的《合同法》,市场经济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对合同的书面形式保留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和价值,并造成法律适用混乱和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一、中国撤回保留的原因
“每一个要求采取特定形式的规则背后都存在一定的立法目的”。 基于我国1986年的经济运行体制和法律制度以及对外货物贸易的规模的国情而对《CISG》第11条作出保留,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时过境迁,随着我国贸易规模的扩大、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市场经济的逐渐成熟,对《CISG》11条的作出保留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撤回保留势在必行,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保留已失去原有的基础和意义
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随着新的合同法的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中華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这三项旧法同时废止。《合同法》第10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由此,书面形式不再是合同成立的必要条件。《CISG》第10条亦指明,根据本公约的目的,书面形式包括电传和电报。至此,中国《合同法》和《CISG》本身关于合同形式的规定基本吻合,即合同可以以书面以外的其他形式订立,对《CISG》第11条的保留也就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和意义,缔约时作出保留所依据的国内法基础也已经不复存在。
(二)保留导致了法律适用的不一致与不平等
首先,对《CISG》第11条的继续保留与国内法的规定不一致导致了适用法律的困惑。如前所述,保留旨在排除一缔约国承担的某项义务,而不是施加一项义务,所以我国对《CISG》第11条的保留排除了我国承认非书面形式合同有效成立的义务,但并不代表我国承担了不承认非书面形式合同无效的义务。因为《CISG》的适用并不具有强制性 ,在具体案例的适用中,如果当事人双方没有排除《CISG》的适用则适用《CISG》,按照保留条款,合同成立必须以书面形式,如果当事人双方排除《CISG》的适用,约定适用的法律,则适用约定的法律,如果当事人双方排除公约的适用,又没有约定适用的法律,则应按照法院地法或仲裁地法冲突规范中的系属指向的准据法适用法律,如果最终适用的是中国的《合同法》,那么合同可以以非书面形式成立。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尴尬的情形:适用《CISG》和适用《合同法》的不同,会导致国际货物贸易合同的成立与否不同。
国际条约是国际法的重要渊源,是各国际法主体之间以国际法为准则而为确立其相互权利和义务而缔结的书面协议,相对于通过国际习惯形成法律,国际条约是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 。国内法逐步与国际法接轨,是一种必然的趋势。然而,根据我国《合同法》、《民法通则》,以及《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在我国与《CISG》的缔约国当事人之间,合同必须以书面形式方为成立,而与非《CISG》的缔约国当事人之间,反而非书面形式亦可。这与公约缔结的目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促进贸易发展是截然相反的。以平等互利为基础的国际贸易发展是促进国家间友好关系的重要因素,对国际货物销售合同采取统一的规则并考虑不同的社会、经济、法律体系有利于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法律壁垒,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然而,国内法的规定与保留不一致,导致了对不同国家适用法律的不平等,这不仅有违签订条约的初衷,而且《CISG》缔约国基本上都是WTO成员国,因此这种法律适用的不平等也违背了最惠国待遇原则。
(三)保留不利于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
合同形式经历了“繁文缛节—充分开放—适度限制” 的历史发展,罗马法认为法律的拘束力源于形式化的行为 ,《CISG》第11条的规定反映了各国对合同形式的要求是“以不要式为主,要式为例外” 。我国《合同法》第10条的规定也反映了该趋势。《合同法》第37条的规定又进一步放宽了《合同法》第10条对书面形式的限制。我国制定新的《合同法》,就是为了顺应缔约形式自由的趋势,适应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促进贸易与经济的发展。
随着我国加入WTO,根据我国在加入时所作的承诺,我国《对外贸易法》第8条规定对外贸易经营权采取登记备案制,由此,每一个中国企业几乎都能从事进出口业务,对外贸易量必然迅速增长,严格的合同形式的限制将阻碍交易双方当事人自由缔约。
二、撤回保留的风险应对
保留或撤回《CISG》第11条都是基于对贸易自由和贸易安全的考虑。此次的撤回行为,表明中国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开始向更加注重效率转变,提倡交易的快速化和自由化。
但是,撤回保留为我国外贸企业带来了贸易环境恶化等风险,贸易交易安全性下降。撤回保留后,非书面形式合同将增多,可能出现更多的交易欺诈和违约行为,所以交易安全性下降,交易风险增大。中国贸易从业主体如何适应对《CISG》第11条保留的撤回后的国际贸易环境是关系其生存发展的问题。要想尽快适应和降低关于国际买卖合同形式上的贸易风险,这些对外贸易主体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措施:
(一)建立境外信息情报管理组织
中国撤回对CISG中第十一条的保留,中国外贸主体可以以任何合意形式与境外主体进行国际贸易。这样在进行合同合意过程中,当事人面临的影响订约的因素将会多样化、地域化和复杂化,每一次订约可能都要受到这个国家的商业习惯或惯例的挑战,都要受到该地区的人情风俗的影响和该地区的消费习惯的冲击。因此这些市场因素或者非市场因素的复杂性给我国当前外贸主体的订约风险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不过可以通过建立境外信息情报管理组织来解决这个问题。境外境外信息情报管理组织可以是多种符合国外法律的形式。可以是单个企业建立的境外企业代表处,也可以是中国外贸企业联合建立的信息情报管理中介,还可以是独立的信息情报管理中介。这些信息情报管理组织负责在自己的管辖区内搜集市场信息或者认为能够影响订约的非市场因素,进而进行分析评估,实现信息规范化管理,与中国外贸主体进行信息交流与共享。
(二)建设企业法律风险管理体系
对于企业来说,一方面,企业法律风险管理具有专业性。法律风险的认知是需要具有专业的能力;法律风险的防范同样需要具有专业的人才;法律风险的解决也需要专业的团队。而另一方面,法律风险又具有不可投保性。我国外贸企业长期在书面合同形式的庇护下发展,如今这种庇护不复存在,这让这些企业所处的贸易环境变得复杂和不稳定了,它们面临的风险也随之多样化和复杂化。所以建立完善企业法律风险管理体系对于外贸企业来说更加迫切。
建立企业法律风险的防范机制,通过企业内部法律风险防范机制、企业内部法律事务机构与外聘律师的联动机制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的企业内部法律风险防范交流平台增强风险控制的主动性、前瞻性、计划性和时效性,按照风险分析评估、风险控制管理、风险监控更新三个阶段,构建科学的动态闭环运行制度。
除此之外,企业内部的合同管理机制可以更加细化、灵活化。撤回保留也并不是鼓励当事人采取非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仍然可以采用书面形式缔结合同,企业可以在充分考量交易安全和交易效率的基础上,自主选择以何种形式订立合同。
(三)注重电子订约的管理
中国政府撤回了对CISG第11条的保留,中国外贸企业以后将会面临着各种非书面要式合同的冲击,特别是国际电子商务的冲击。中国政府方面也要把注意力转移到电子订约的规制问题上,尽快明确电子订约、电子认证、电子签名等法律适用问题,为我国外贸企业在电子商务贸易过程中提供订约指导和法律后盾。
当前国际贸易环境中,电子商务的发展越来越主流化,作为外贸主体的企业也必须适应和参与这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充分扩展现有的网上交易平台的功能,将电子订约、网上支付结算融入公司官方网站上。此外,电子订约中,企业要特别注意订约的规范性和电子数据信息的保留,根据现有的电子订约条约公约或国内法,审查其法律效力,清楚了解合同双方關于电子错误的法律规制和电子合同认证法律规制。
于此同时,电子订约过程中的风险分担的约定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项。电子订约中可能会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主要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原因),致使电子合同不能成立,而给订立电子合同的当事人带来的损失。 因此,当事人在电子订约过程中,应先行咨询了解这方面的公约、条约或者商业惯例,最好,能在订约过程中明确电子风险分担的规制。
三、结语
在中国入世十几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仍然没有得到一些西方国家的承认。《CISG》第96条授权本国法律规定销售合同必须以书面订立或书面证明的缔约国,可以对第11条提出保留,因此,继续对合同形式的保留,会给世人造成一种“中国的《合同法》仍然坚持以书面形式订立合同”的误解,而此次撤回保留,也是中国向世人证明自己市场经济、法制开放所作的努力。总的来说,撤回该保留是利大于弊,是我国适应时代、经济发展要求作出的正确选择,将促进国际货物贸易的发展和法律的进一步向前发展。如今,撤回保留的声明已经生效,展示了中国以更为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效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简介】卢雅澜,女,重庆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学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何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