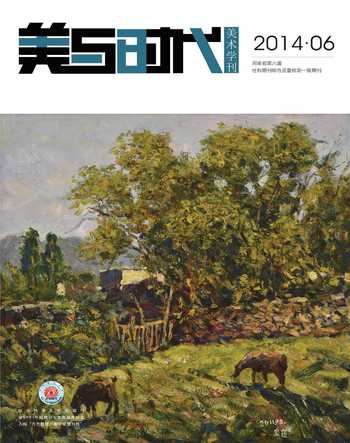美术史的伟大尝试——浅论艺术家传记

摘要:从瓦萨里(Giorgio Vasari, 1511-1574)于1550出版《名人传》(全名《意大利杰出的建筑师、画家和雕塑家传记》以来,艺术家传记成为一种重要的美术史载录方式。《名人传》正如冲决堤坝的第一股劲流,其后的两个世纪内,艺术家传记作为艺术理念的传播载体,真正汇聚成了裹挟史学众生相的洪流。在这从耳熟能详的文艺复兴至巴洛克时期,从温热湿润的意大利南部至欧陆板块北部的艺术运动中,涌现出了数量可观的艺术家传记名作,《贝尔尼尼传》正是这些艺术家传奇中摄人心魄的一部著作。
关键词:艺术家传记 美术史写作
古往今来,作传者如过江之鲫,而瓦萨里名誉加身,《名人传》功不可没。其原因正如瓦萨里被誉为西方美术史家第一人,《名人传》能跳脱出平庸之作的行列,是因为作者采用独特的传记写作手法论述了意大利三百年来的美术史历程。当然,《名人传》并非横空出世,我们应肯定在瓦萨里之前的诸多尝试,例如维拉尼(Filippo Vallani, 1325-1405)的《佛罗伦萨文化的起源》(Liber de origine civitatis Florentiae et eiusdem famosis civibus)以及《比利之书》(Libro di Antonio Billi)等等,在如此背景之下,瓦萨里选择传记的写作手法或许不那么令人费解。直到温克尔曼(Johan Joachin Winckelmann, 1717-1768)从德莱斯顿爬满灰尘的古代塑像之上领悟出“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两三百年来,瓦萨里的美术史写作手法影响了难以计数的艺术行家、作家,直到瓦萨里去世后一百多年还有诸如巴尔蒂努奇(Filippo Baldinucci, 1624-1697)的《贝尔尼尼传》(Vita del cavaliere Gio Lorenzo Bernino scultore,architetto,e pittore)以及贝洛里(Gian Pietro Bellori, 1613-1696)的《现代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传》(Vite de'Pittori, Scultori et Architetti Moderni)与之辉映,他们都想成为更好、更准确的“瓦萨里”。然而,诸多“瓦萨里第二”无法取代的是,《名人传》对于我们现在所称呼的建筑师、画家与雕塑家的扶正,在当时他们都是匠人,而瓦萨里以处理伟人的手法为其立传,称颂其品德,赞许其技艺,敢为天下之先,这一点在之中的《米开朗基罗传》(The Life of Michelangelo)展露无疑。
《名人传》正如冲决堤坝的第一股劲流,其后的两个世纪内,艺术家传记作为艺术理念的传播载体,真正汇聚成了裹挟史学众生相的洪流。在这从耳熟能详的文艺复兴至巴洛克时期,从温热湿润的意大利南部至欧陆板块北部的艺术运动中,涌现出了数量可观的艺术家传记名作,而上文所提及的《贝尔尼尼传》正是这些艺术家传奇中摄人心魄的一部著作。当试图比肩瓦萨里的17世纪大家贝洛里汲汲于古典艺术理论之时,同时代的巴尔蒂努奇开辟了另一条艺术家传记之路。贝洛里对古典艺术家的偏爱使其不再将目光投向同时代的巴洛克艺术家,《现代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传》在整体构架上基本沿用《名人传》,宣扬的是贝洛里奉为圭臬的古典艺术理想,诸如“designo”、“prudence”构成了捆绑于传记之中的美术史学理念。
若是读者手捧一本《贝尔尼尼传》,品咂其间,定会涌生出莫名的熟悉感。确实如此,观照近现代艺术家传记,例如我国林浩基所著、学苑出版社于2005年末出版的《齐白石传》,或是王家诚所著、百花文艺出版社于2008年刊印的《张大千传》;抑或是审视海外近现代艺术家传记,则会觉察出更为明晰的学术传承脉络,罗杰·弗莱(Roger Fry, 1866-1934)先后出版了《贝利尼》(Bellini)以及带有传记性质的《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Cézanne. A Study of His Development),后者犹如抛入干草堆中的烈火星,彻底引燃了后印象画派的狂飙突进。罗杰·弗莱能够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批评家之一,此代表作居功至伟。有趣的是,抛却其作家、评论家的身份不谈,罗杰·弗莱拥有着与前人巴尔蒂努奇同样的另一重身份,他们都是各自时代炙手可热的鉴藏大师,而这一身份标签反应在行文之中,则是他人无法复制的细腻、精准的风格论述。艺术家传记的传奇并未终结于此,而是不断证明在美术史学创作方式的选择上,其鲜活生命力依旧不可忽视,许多艺术家传记不再采用最为常见的传记书名,加入了时代盛行的文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研究与写作方式,其目的殊途同归,例如建立符号学帝国的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无论是大众文化的研究或是结构主义的建立与兴起,罗兰·巴特毫无疑问是学者讨论的中心话题,而其1975年所出版的《罗兰·巴特论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ditions du Seuil: Paris),是对其生平的自述、理论的概括、学术的总结,而这一传记中叙事的手法在《贝尔尼尼传》已然登场亮相,时间的推移使之更为完善、纯熟。
在艺术家传记发展史中,《贝尔尼尼传》是前中期艺术家传记的典范。顾名思义,这部传记著作的主人公就是17世纪叱咤风云的巴洛克艺坛领袖乔凡尼·洛伦佐·贝尔尼尼(Giovanni Lorenzo Bernini, 1598-1680),在这之前的艺术家传记多为群体性艺术家传记,1568年发行的《米开朗基罗传》是从瓦萨里《名人传》中剥离修订而面世的。诚如上文所言,《贝尔尼尼传》中许多美术史学创作方式在现当代艺术家传记写作文本中依旧为其执笔者所借鉴和采用。
对时间理解的差异使得每部艺术家传记都千姿百态,不少传记作者愿意遵循这一文学形式最为常见的时间处理方式,即将传记主角及其代表作品安放于一条脉络比较直观的时间轴上,这一写作惯例使得《名人传》及其早期艺术家传记作品大多采用从传记主角出生至死亡的叙事方式。而在《贝尔尼尼传》中,时间不再是一种说明性质的范畴[1],而是一个有条理的框架,读者将不再看到任何传统美术史中对于艺术家成长发展的叙述,时间作为一种服务于全书主旨的完整的系统或是讲究修辞的规则被现代当艺术家普遍接受。时间线缀链着的点或者面则是传记作者所遴选的素材,而大多数艺术家传记的素材选取基于两个方面,其一近于社会问题,为笼罩着神秘光环的艺术家本性,其二为众口称赞的精品佳作,这两点在近现代艺术家传记中俯拾皆是。面临同一个素材,拥有不同知识体系的作家会创作出风格迥异的文字。前文提及的巴尔蒂努奇以及罗杰·弗莱,他们丰富的鉴藏经历令他们在论述一件作品之时,能更少地运用主观臆造的词句而精确定位艺术作品本身的风格标签与艺术价值。在此之上,影响一部艺术家传记的最后要素则是串联上述所有元素的文本词句。早期艺术家传记对于修辞的讲究使得其行文带有时代的浓厚气息,例如《贝尔尼尼传》则是巴洛克时代艺术家传记语句风格的代表,叙事论述由长句堆砌而成,语势跌宕起伏,充满了内在的旋律感。[2]而在语言信息高度发达的当今,史学写作显然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如何紧随时代悸动的脉络,反应当今的语言特色无疑是每个艺术家传记作者不容忽视的难题。
菲奇诺(Marsilio Ficino)在给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之子的信中写道:“历史不可缺如,它使生命悦泽,且予其以道德意蕴。透过历史,逝者恒之,无者有之,旧者新之,少者壮之。若一位七旬老人,以其阅历而享智慧之誉,一个思接千载之人,该是多么睿哲!的确,一个胸怀历史春秋的人,真可谓历经千古了。”[3]我将文题定为“伟大的尝试”,并非妄图推卸行文的责任,而是此文也正是我的一次尝试,更为关注能否引发有价值的问题,而非对往昔历史做武断的判定。正如菲奇诺对于历史的精彩论述,纵然往昔成就斐然,我们仍需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就算是瓦萨里的《名人传》,在今人眼中,依然有透着陈腐气息的糟粕,在当时非常新鲜的艺术概念,诸如“disegno”、“grazia”等等,在今日看来,这些概念虽还有挖掘的价值,但若是将其略加粉饰便搬出挪用做评判艺术的标准,则会贻笑大方;抑或现当代艺术家传记也存在的弊病,地区狭隘性,就如当时德国作家,为丢勒的“落选”《名人传》打抱不平,这部分因为环境所限,部分是区域归属感作祟;而《名人传》中遭人苛责最严重的是瓦萨里那近似生物循环论的美术史阶段发展观念,瓦萨里在读者耳边不断叮咛着出生、成长、衰亡、再生的循环图式,我们应当肯定现当代史学创作者“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学术雄心,而更应警惕前人的桎梏。
正如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 1892-1968)所言,“几乎没有人能抵挡住这样的诱惑,即:要么对那些非平行现象的线索视而不见,要么叉开话题。但是如果我们弄不清平行现象是如何发生的,即便是货真价实的平行论也不能真正令我们感到高兴”[4],我不得不放弃一些尽善尽美的念头,从《名人传》到现当代艺术家传记写作,一定还存在着未知的联系,此文诚为抛砖引玉,向美术史的伟大尝试致敬!
注释:
[1]Baldinucci:The Life of Bernini, The Penn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6,p11.
[2]Baldinucci:The Life of Bernini, The Penn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6,p47.
[3]Marsilio Ficino致Giacomo Bracciolini的信(《马尔西利奥·菲奇诺全集》(Marsilii Ficini Operaomnio)莱顿,1676年,第Ⅰ卷,第658页)
[4]Erwin Panofsky:Gothic Architecture and Scholasticism, 1951, Foreword.
作者简介:
刘波涛,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