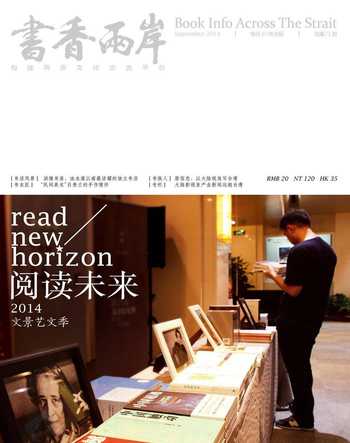即日出发,只映一场
陆彗风
建筑物都有生病死,唯独戏院会老。楼房屋宇经历过人来人往、人去楼空的阶段,要么化作瓦砾拔掉记忆,生还下来的雕栏玉砌重新粉刷投入循环,又见屹立如昔;戏院却采用了特殊的工程结构,其地基深植于梦和情感之中,其支柱投射在广告牌上、银幕里,有别于志在抵挡岁月的土木建设,偏偏是为着消磨时光而建的,朱颜伴随观众年龄变改。
《光影戏游》作者黄夏柏为这些难以见于史书的娱乐场所写下不少文字,除写作博客《戏院志》,还出版过《忆记戏院记忆》《澳门戏院志》等书,在城市的平面图上标注出一艘艘记忆方舟的人海航程。
《光影戏游》虽成书在后,实际上却是这些作品的“前传”,作者于序言中写道,近年因种种缘故无法远游,思绪却出发回溯九十年代初以还的多次海外之旅。因为当日尚未立意梳爬戏院故事,而且毕竟未尝长期于异国居住,浮萍过客无暇详细考察途上每淌甘泉绿水,本书没有谱成前述二书的系统化群像;然而戏迷念兹在兹,电影早就担当起背包客的伴游领队,以十多年间目的地殊异的多次旅程,剪接串连起来,还是织出了一张充满光影情怀的追忆之网,戏院则是这张网上的千千结。
千千结里起码有百百结坐落巴黎,乃作者每次欧游必经之地。浪漫花都戏院开遍,不缺阔派头的荡气大剧场,但回肠的还数巷弄里的小影院,小本经营,或放映别出心裁之作,或重温环球经典。大小林立、百味纷呈正是慕名而至的文青们最爱呼吸的艺术生态。
另一个美不胜收的地方要算旧金山。作者乘坐古雅电车,路经幢幢历史建筑,来到二十年代落成的卡斯特罗,欣赏到布满壁画雕饰的放映厅和开场前的管风琴表演,体会真正movie palace的华美气派。一如巴黎,旧金山亦是无数电影的取景地,除了金门桥和九曲花街这些范例桌面,还有拍摄《迷魂记》(Vertigo)的酒店,以及恶名昭著的监狱亚卡拉。于此加州之行,作者还在附近的奥克兰市,遇上民间发起筹款修葺老戏院的活动,深受感动,虽未如愿加入参与,亦一直于网上关注保育成果。
来到七年前的澳洲之旅,作者其时已开始博客写作,访寻戏院遂成指定动作,更几番冒着面斥之窘拍下照片纪录。阳光大陆上只逢夏夜才运作的户外戏院也许未够稀奇,作者还到过西岸珀斯的Piccadily,这家戏院不只布局古怪、观众席异常陡斜,居然还沿用人手拉动银幕两侧布帐!
什么嘛?都已是互联网时代了!没错,现在只消输入关键词,不难随时穿梭各大都会的放映厅,图文并茂全方位阅读每个座位每张银幕的历史,实时虚拟旅程媲美亲历其境,何用等自知身是客的作者花工夫翻着旧相簿忆述片言只字?这也许亦解释了作者现在致力于为自己城市的戏院作传,好教这些最地道的数据、最亲近的记忆得以在网上流传留存。
早说了这本书重点在“游”,但不是叫你按图索骥。比起惊鸿一瞥或水过鸭背之“到此一游”,与自助旅人较为有缘的明显还是那只神出鬼没的“错过鸟”,多数因为时间不对或不够,也试过念及人在异乡而放弃凌晨场次;有大意错达后门不得其门而入的时候,也有心情坏到过门不入的时候。不过只要你相信在柏林看温德斯、在台北看吴念真的风味确实无可取代,一切还是会值回票价,还未算上更难得的不期而遇和久别重逢。比如曾在华沙走进电影海报博物馆,却要到几年后游美国方后知后觉地发现波兰设计之精奇;比如在香港电影节透过苏古诺夫镜头重温第一次外游来过的圣彼得堡冬宫。说到生于长于澳门的作者,长大后终于在(真正的)葡京邂逅乐队Madredeus,买下唱片未及细听,反而经过巴黎时率先看到一行人亮相于《里斯本故事》,十年间于世界各地收集唱片,终能一睹现场演出的地点竟是回到蚝镜特区,此间缘法巧妙岂不正好配合一曲花渡的漂泊致远?
这些都是无法在网上搜寻下载,只能拔掉插头以肉身登入戏院才能撷取的私人连结。如果你以为来日方长机会还多,请记着外国的银幕并不特别四平八稳,市场压力之下,也会转型,会消失个性,或破败凋零;会拆卸,或面目全非而变成两个字母的名牌皮具店。
当然,出外旅游想尽量利用时间四处走也是人之常情,有多少人甘于一头雾水或是冒着不对胃的风险,安排宝贵假期中的个多两个小时自困于一个日常场所里?读到戏迷如作者独闯异邦戏院,言语不通似乎不能减去多少看戏的兴致,有时仿佛还彰显了一股目迷五色、光影流泻的纯粹感动。我不够资格自称戏迷,不过倒是有过唯一一次海外的戏院经验。在电影大国印度,但不是在“宝莱坞”之城孟买,却是恒河畔的瓦拉纳西,一位织品店的少东带着工匠、一位韩国人和我进戏院,英语流利的少东边看边给我们两个外国人解说,故事情节此际是记不起了,只知道爱写流水账的我当时居然将整出戏当作行程一般记在旅行日记里。如果旅行本身是为了逃离日常,那么在旅途中走入戏院,漆黑环境反而能盖过身处异地的陌生感、不安感,隔绝了街道上的喧闹和过多的新奇刺激。一份亲切的漆黑,安逸的漆黑,通过在非日常中经历日常,人摆脱内外的干扰,体悟到旅途上、体悟到戏剧里、体悟到生命中的一期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