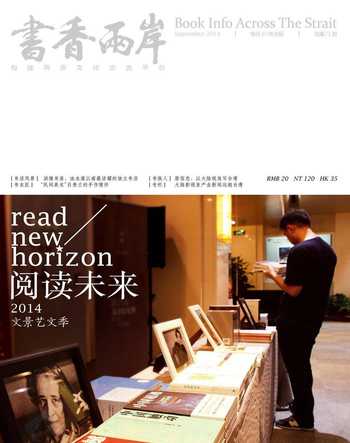中国人如何思考国家、历史和世界?
每年年底都会有一些文章,总结当年中国思想界的几大思潮;而活跃的各大会场上,一些学者都有意无意地被贴上各种标签,这些会议也成为隐形或显性的“宣言会议”;而各大思潮跟我们每个人也相关,像是前一段时间微信上的一个测试,回答十几个问题,测试你在文化、政治、经济各个方面是属于哪一派……面对这样一个喧闹的思想市场,我们不禁要问,对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选择、历史的发展,我们应该如何思考?
十几年前,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张汝伦写了一本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就是想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当下中国人思考公共问题的思想预设是什么?中国人如何思考国家、历史和世界?
张汝伦:“我们如何思考什么?”这首先是一个哲学的问题。
什么是哲学?哲学就是对整体性问题的认识,是在这些基础上对一切的反思和批判。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可信的东西就是具体问题具体解决,比方说人口问题怎么解决,交通问题怎么解决,对天文怎么理解,对地质怎么认识,对昆虫怎么认识,这是学问,大家会觉得这是最有价值的。然而,哲学的突破就在于彻底超越动物,跳脱当下的需要,从整体上把握这个世界。所以哲学实际上就是要整体性地把握世界,把握宇宙,这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哲学体现了人的自由,他能够突破自己当下的需要,去追求一些对他有根本意义的东西。
人站在哲学高度上,考虑各种问题(的方式)就会不一样。但是今天中国人对于国家、历史和世界的认识,坦白来说,还没有进入到哲学的层面,为什么?我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近代中国处于一种功利思维占压倒优势的思维状态。第二,从事哲学研究的人未能真正做到使哲学成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哲学研究只满足于转述而不是消化和吸纳,使它成为自己的东西,所以一百余年来我们的认识、理论水平不升反降。
我们现在的思想史研究,比较缺乏哲学的深度和理论涵养,我们不但没有卡西尔、伯林、福柯这样的思想史家,甚至连剑桥学派的思想史的水准都达不到,当然也不可能出现像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这样的作品。这些作品之所以让我们印象深刻,在我看来是有识有断,识是见识,断是判断。他对自己要处理的对象、问题有独到的体会和见解,这样的研究能打开我们的眼界。我可以不同意他对问题的看法,但是他对问题的揭示很独特,启发我们的思考,这就够了。一个人怎么做到有识有断?这就要多做哲学思考,研究思想史是反思自身思想状况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历史不是仅仅像我们普遍认为的那样,就是过去发生过的事情,历史实际上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就活在历史中。既然这样,为什么可以把历史作为反思的对象呢?因为人有语言,语言可以把一切东西加以抽象化以后,再转化为自己反思的对象,可以让我们和自己所处的环境拉开距离,保持一种批判、反思的位置,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摆脱决定论的控制,才可以说我们有自由的思想,我们是一个自由的存在物,人的自由思想的根本保证就在这里。
为什么我们要从事思想史研究?至少对我来说,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途径来思考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对如何看待这个国家、历史,有一个反思,而不仅仅是把过去别人说过的话再来说一遍。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就要求哲学进入了,但很可惜哲学没有进入现在的思想史研究,现在基本上是一个教条的研究,最大的问题是现代性叙事的问题。认识中国近代的历史,包括思想史,实际上是一个要完成现代化的过程,无论是最初接受西方人讲的把中国近代历史理解为冲击和反应,还是后来讲的这是一个不断现代化的过程,还是时下流行的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等等,所有这些理解的共同特点,第一是把历史看作一个外在事物的发展史,历史的发展方向只有一个,这是一种目的论。这种现代性的叙事,把中国近现代史看作一部历史,那样会隐去很多东西,但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除了社会、经济、制度、文化之外,还有人的主观历史。十九世纪在西方首先兴起对现代性的批判,我们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人的知情意主观被埋没之后提起的诉讼,是对把历史理解为一部人类的制度合理化、理性化的这种历史观的质疑和抗议。我们现在的思想史里边,恰恰缺的是这个部分。人类所有的历史就剩下一件事情,建立一个新的制度,于是很多的东西被淹没、简单化。
我们如果还按照现代性的叙事来看思想史的话,那么中国的历史存在相当一部分,也就是主观世界的部分是没有办法进入思想史的法眼的。比如我读《三十六画品》的时候,不是36种对中国国画的评价而是36种感官,感官世界的方式那么典雅、细腻、深奥,我们现在还有这个思想深度吗?如果我们这样来看问题的话,会觉得这个问题远比现在复杂,更不用说一部批判的现代思想史。
所以我们不但要看到现在的社会经济的世界,也要看到生活世界。这是现代思想史所忽略的,从生活世界的角度看古代,这里的古和今不是编年史的概念,而是历史哲学的概念,这是两种不同的对历史的理解。
我们有没有可能在处理思想史的时候,有一个更基础的层面,在那个基础的层面上古今问题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支撑,又形成一定的紧张关系?我们可不可以说,站在今天看古代,反过来又站在古代看今天?古今互看是超越文化和历史局限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在我看来,如果要达到超越古今对立的思维,如果要更有深度、更全面、更复杂地把握历史的话,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有一个完整的突破。中国人如果在二十一世纪要有所作为的话,在哲学上一定要有一个起飞和突破,否则是没有前途的。一个不会深刻思考自己当前问题的民族,我想是不会有未来的,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今天这个主题,中国人如何思考国家、历史和世界?我想,我们只有站在哲学的立场上,站在哲学的高度上,才能真正理解这样一个命题的意义。
丁耘:中国的思想史的写法,就我自己孤陋寡闻看到的可以分成三类:一种是史学类的写法,原来思想史是历史学下的二级学科。一种是以汪晖先生《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为代表的,称为总体是社会科学的思想史的作品。张汝伦教授则代表哲学对思想史的写法,方向是开辟性的,值得大大表彰,也是值得遵循的。我读张汝伦教授的大作有两个心得,一个是撰写思想史的方法,一个是内容上。用精神状态的方式精准把握历史阶段的思想心态,张汝伦教授是我国解释说的开拓者。在《现代中国思想研究》这本书中,张汝伦教授研究了民主主义、历史主义、社会主义这三种思潮,还介绍了一些重要的思想家们。这三种思潮是建构现代中国思想基石性的东西,我们反省现在支撑着大家去思考关于国家历史、世界,政治、文化、经济等仍然是这三种东西,在历史上表现当然是思潮,但是更多是思想心态、观念心态。
张汝伦教授的这本书出版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中国知识界、思想史研究界发生一些变化,有一些变化是张汝伦教授在书里预见到的,比如说康有为,迟早人们会发现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十年前他说这个话回应的人寥寥,而现在有了“新康有为主义”。
张教授花很大的力气去处理历史主义。历史观的问题中,进步史观肯定是一种直线史观,但是退步史观也是直线史观。现在的主流意识形态里,不管是毛时代还是邓时代都是用康有为重新解释的儒家历史观,这是康有为对中国古代历史观的转化。但是循环的史观和直线的史观可不可以有一个协调?可以有的。我非常敬重张老师的一点,是他对黑格尔抱着不轻慢的态度,“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人的视野是直线的,但是回过头来看确实是循环的。
吴新文:对于张老师的这本书,我有一些新的感想:第一,现在有很多研究是所谓四平八稳,实证主义的,强调作者是超脱的,把思想史呈现给我们。而张老师的研究不是这样的,他是把自己的生命,把自己的浩然之气融入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所以这是非常有活力生命力的一本书。
另外,张老师的这本书,确实做到研究的深和透。对于一些权威的说法,他不是照搬过来就用了,而是带着思考的态度来看待原来的研究,所以很多时候对于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大家,他是抱着争辩的态度看待的。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围绕现代性这个问题的思考。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如何思考国家、历史、世界的问题,中华民族如何自立于世界之林,这是所有仁人志士都关心的问题。他们的思想并不是无缘无故的,这样一种围绕这个问题的不同的呈现方式,我觉得是非常过瘾的思想史研究。
看完张老师的书以后,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这本书前面写思潮,后面写人物,第一版和余英时的讨论,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问题,特别是围绕中国和西方相遇之后,中国所谓的现代化,围绕我们究竟如何看待现代性这样一个问题,当下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仍然争论得热火朝天。我记得张老师的书里面写到过,现代性有点像罗马神话里面的门神,是有光明和黑暗的两面性。
有人认为中国当下需要资本主义解决,西方发达国家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但是也有人说,资本主义是行不通的,有很多灾难性的问题现在都表现出来了,所以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样一个简单化的思潮面前,整个思想界的倾向是大家火气都很盛,都是义气用事,贴标签。在中国当下的情况之下,我们如何对这两个东西及其复杂关联有一个更深的理解,然后暗示中国思想者未来思考的方向?这是这个问题的第一面。
书里面讲到近现代西方的文化和中国的文化深深融合在一起,独立的中国思想和中国文化都是不存在的,西方的文化已经成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思考中国当下的思想,究竟是抱着什么样的意识?说得更高一点就是用一种什么样的趣味来看待这样的东西?我们究竟如何能够避免简单化的选边,又能够有一个方向性明确的思考?这是我要向张老师请教的问题。
洪涛:张老师的这本书刚出版时,我非常认真读了。我觉得这本书在当时没有受到相应的关注,当然也许今天我们再来读这本书,可能会获得更全面更新更深入的把握。
研究思想史,尤其是研究近现代思想史,大体上有三个意图。第一种是传统的研究理论,研究资产阶级思想家、封建思想家,可能是为了证明他们的思想道路,或者他们指出的中国未来所走的道路是不正确的,而现在我们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种近代思想史的写法,我把它叫做政治的写法。
第二种是出于历史的新奇,研究一百年前或者是几十年前,在清末民初,思想家在干什么?这种历史取向的思想史研究,在近代思想史研究当中占据了主导,是一个主流。
我刚才注意到张汝伦教授在发言的时候反复提到哲学,他是从哲学的角度来研究近代思想史。这不仅仅是因为张汝伦教授正好是在复旦大学哲学系,还有更深入的原因,正是他强调从哲学的角度来关照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从当下来看,中国人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我们都是中国人,这是第一个视角;第二个视角,中国有四五千年历史的文明,这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今天中国人生存在这个民主国家当中,拥有这样的历史,我们从这两个视角来考虑中国人当下的生活和过去的生活,根本是为了什么?根本还是为了未来,而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未来,也不仅是作为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的未来,而是中华文明以及中国人充分参与其中的这样一个世界的未来。国家本身是政治视角的,中华文明是未来视角,这个民族、这个文明共同参与创造人类的未来,这是一个哲学视角。因为张老师讲的哲学不仅仅是一个学科的概念,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当下我们是谁,我们的位置在哪里,知道这些可能就知道未来要往什么方向走。这是哲学的根本问题,也是哲学的起点和归宿。
我想今天从哲学的角度,可能会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四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到现在,曾经经过一个重大的转折或者变化,所谓千年未有之变局,这场变局是从春秋后期一直到西汉中期才基本完成。中国文明面临的第二次千年之变,这在十九世纪中期,当时很多先者已经意识到这个情况,所以今天我们恰恰处于这样一个巨大的千年变局当中。要应对这样的变局,我们必须要有高远的哲学智慧,这是张老师反复提到的哲学根源。但凡面临这样变局的时候,都是哲学智慧大爆发的时代。在这样的状态当中,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必须要考虑最根本的问题。从清末到现在的伟大思想家,都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可以帮助我们,或者我们和他们共同思考、面对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这是需要哲学智慧的。张汝伦教授的这本书,主要就是从哲学的角度考虑在这场变局当中,中国先贤对中国历史思想的考虑。
我们现在必须要发挥创造性的智慧,用对得起未来子孙的方式,创造出今天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思想心态,尤其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这是我们今天的责任。
张汝伦:刚才吴新文教授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现代性的问题,我个人的理解,现代性、现代化是一个概念,用来特指一种文明形态。既然是一种概念的话,就是可以突破、修正、质疑的。所以有时候讨论问题时,概念是帮助我们理解现实的工具。反过来,当我们对生活现状不满的时候,也有权利重新批判、修正、否定、颠覆这个概念。我们绝不能把现代性理解成是人类的天命,人类曾经对现代文明形态有这样的理解,但是现在这样的理解不断受到质疑,不断受到批判,也不断得到修正。
我们中国人可不可以讲现代?可以,我们并没有一定要把现代和现代性打扮成妖魔鬼怪,但是对于种种方式存在质疑,有些东西没有答案。比如《秋菊打官司》,按照现在的法律程序,你伤了我的丈夫,你得要给我一个说法,这个官司一定要打赢,要赔礼道歉,但是秋菊官司打赢以后成为全村的公敌,这里面就有一个“情”,秋菊自己都非常的纠结和痛苦。这并不是像是我们想的,现代好,传统坏,西方的东西好,中国的东西坏,法律是无情的,讲情就是反动,这样的说法我们可以怀疑。
真正的历史是来回摇摆的,通过来回的摇摆,把经得起摇摆的东西发扬起来,而否定掉那种现在比过去好、将来比现在好的简单理论。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困难的任务,就是如何打捞中国,如何在世界的文化图景当中加入中国元素,这是摆在我们这代人面前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