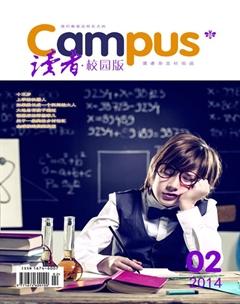关于一条狗的乡村记忆
袁静帆
几年前,二舅从西安带回两条小狗,把公的送给了三舅。
三舅家在农村,和舅妈在服装厂里工作,姥姥一般住在三舅家,三舅还要供两个哥哥上学,生活并不宽裕。那条狗虽说不是农村的那种土狗,却也没有被当作宠物,甚至连名字也没有,它只是一条看门狗,再普通不过。平时三舅只给它一些剩饭剩菜,它却长得很快,两年过后,它立起来时就和上高中的表哥差不多高了。但它一直很瘦,总能清晰地看到它肋骨的凸痕。
表哥从来不拴着它。村子里其他的狗嫌它是外来品种,总是与它为敌,所以它也不常乱跑。姥姥总说这狗十分精明。有一次,它竟然与家中的猫联合起来,偷吃了二姨给姥姥买的烧鸡,姥爷训斥了它一顿,我和弟弟却因此更喜欢它了。
我总要在假期回老家住几天。看着村里的孩子骑着自行车在乡村公路上疾驰,我也开始学起了骑车。学会之后还不太熟练,我总是骑得歪歪扭扭。之后有一天我独自练习的时候,路旁的院子里突然窜出两条凶猛的狗,朝我这边冲过来,我吓得大叫,却没有一个人出现,我不知从哪儿来的力气,疯狂地蹬着自行车,完全没了初学者的生疏。我想甩掉这两条狗,没想到这两只“四轮驱动”的动物跑得还确实快,流着口水的嘴离我越来越近,好像是想把我的小腿给当作午餐!我骑了一路尖叫了一路,最后筋疲力尽打算听天由命的时候,舅舅家的狗却不知从哪里冲了出来,将那一黑一黄两个家伙咬得狗毛乱飞,最后它们狼狈地逃走了。我惊魂未定,恍恍惚惚地从自行车上下来,腿都软了,过了半天才意识到,那个大家伙救了我!我带着狗回家,把火腿肠分了它一半,它好像也很高兴,跑到院子里扒出一只幼蝉吃掉了。
之后几天,我骑车时总让它跟在我的身后,再也没有狗企图咬我了。有时它跑进旁边的田地里,欢快地跳着,一身褐色皮毛在阳光的映衬下闪闪发亮。玉米苗高得淹没了它,它就这样在一片荡漾的碧绿之中起起伏伏,白色的小蝴蝶在它爪子的扑闪间飞舞。
我们一起买烧饼,一起在雨天滑倒,一起在铁路旁看着运煤的老火车呼啸而过。它总想霸道地躺在沙发上,但每次都在被姥姥训斥后,绕一圈又躺在凉席上。我们哭笑不得地看着它时,它却已经自在地睡着了。
对于那个遥远夏天的记忆,只因一条连名字都没有的狗,变得简单、纯粹而又清晰。
很久之后的一天,三舅打电话来说狗被卖了。当时我和弟弟正在吃午饭,我们一听都愣住了,思绪好像在那一刻凝固,迟钝到无法运转,缓过神来后,我们便止不住地哭起来,泪水好像洒进了我的碗里,以至于那顿饭吃起来又苦又涩。
三舅说,狗不小心抓伤了一个小孩,于是被他们拴了起来,后来狗又咬了那个住在东边的叫“郝妞”的老太婆。郝妞很生气,坐在门口的青石板上不停地骂狗。三舅本来因为狗就赔了别人不少钱,闹了许多不愉快,让她这么一骂,只好狠下心卖了狗。
我不敢想那个买狗的人是干什么的,我不敢想狗在笼子里看着渐行渐远的村子是什么样的眼神,我不敢想它是不是成了别人的盘中餐、腹中肉,我只是不停地将碗里的饭送进嘴里,希望饭菜可以让我的思绪停滞,止住我的眼泪。我宁愿相信它还能快乐地生活。
后来又回到老家,郝妞家门前开了几朵很大的花,妈妈客套地说她的花好看,我和弟弟却一直在一旁作呕吐状,发出很恶心的声音。谁让她害了我的狗!
再后来,那辆自行车也老了,铃铛发出的声音不再清脆,铰链还会时不时罢工,有些地方也已经生锈,失去了昔日的光泽。我知道那段时光已经永远离开我了。
每次回去,我都要去看看那片玉米地,默默地想念那个曾在这里跳跃的身影,和那几只飞舞的白色蝴蝶。
(本文作者系我刊校园通讯员,河南省郑州市实验外国语中学九年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