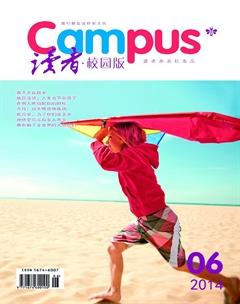英语发芽,汉字开花
路也
行到美国,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成了一只盛满汉字的罐子。那些方块字由于忽然失去了使用场地,找不到及时的出口,只能在我这只高1.58米的罐子里面密封着、烦闷着、膨胀着、挤压着、惆怅着、等待着,仿佛里面关进了一群亮闪闪的蟋蟀,或者里面在日日夜夜地培育着、催生着植物胚芽,跟生豆芽一般……我的天灵盖,也就是罐子上方那只圆圆的盖子,快要被压抑着的巨大的母语力量掀开来了。
有时候,我又感到自己的身体是一部地面上的雷达,里面的导航系统装置完好,却怎么也搜索不到要找寻的飞行目标,灵感不再,甚至连表情看上去都有些发呆了。我想,那是由于汉语的领空换成了英语的领空,我这部中国制造的雷达失灵了。
被英语包围,四面楚歌。可是这楚歌又让我无比兴奋,其实从感官到心理,我对英语都有着类似红杏出墙的热爱,它能带给我城池沦陷般的快乐,它的干练准确和绅士风度让我着迷,以至倾倒。
我疑心英语的每一点进步似乎都在以汉语的退步为代价,身体里的英语也在发芽了,虽然是孱弱的,却正在一点一点地挤走汉语的地盘。于是我很快就开始想念汉语了,30多年来,我第一次在一个没有它的地方想念它。我常常一个人在路上旅行,随身的背包里总是塞着一本唐诗宋词元曲的选本。有一次在从迈阿密飞往费城的飞机上,环顾四周,没有发现一个东方面孔,我忽然想到,此刻在这个机舱里,除了我,没有一个人知道那本书上写的是什么,这差不多相当于在这架波音飞机上,藏了一份用密电码写成的高度机密的军事文件。是的,在英语那连绵不断、蜿蜓起伏的大好河山里,想着古汉语的四合院和画栋飞檐,的确有着很奇特的感觉。在一面镶着字母似的卷涡纹边框的西式的镜子里,在元音和辅音映出的光泽里,照见的却总是方块字里的中国,繁体竖版的中国,声母和韵母拼出来的中国,用点横竖撇捺弯勾一笔一画地写出来的中国,它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清晰。
去看海明威和惠特曼,没有朝拜的心情,倒是有走亲戚串门的感觉。从前看的是中文版,这次我却想把象形文字的它们统统再翻译回去,看看拼音文字的它们——我想知道它们本来的模样。在路上我总是能想到“八里洼”这个地名,地球是圆的,我这样不停地走下去,途经海明威的家、惠特曼的家,途经梭罗的木屋,走过狄金森的窗下,最后一定还会走回到我的八里洼。
诗都是后来写的了。我遥遥地赶回地球的另一边,走在蒙着烟尘的天空下,沿着永远飘散着白菜味的街道拐进小巷,走进光线昏暗斑驳的楼道,回到那个属于我的小小角落,重新坐在那扇有着白杨树的南窗下……我感到自己正面对着整个世界。
那满满一罐子汉字,蟋蟀般蹦跳出来了,每一个汉字都是一个压抑不住的茁壮的胚芽,都舒展开了枝叶,抽出茎干,开出花来,那雷达在汉语的领空重新有了信号,找到了目标。
诗后面标着日期,年和月,我没有像过去那样标上写作的日期,这次我标的是我最初想写这诗的时候的那个日期,我认为对于这些诗,产生想写它们的念头要比真正写出它们来更重要。
诗写的是美国,但更是中国。很多年以来,其实在我心里,常常莫名其妙地吟咏着一句诗:“我的心啊在高原,这里没有我的心。”我还会同样不知为什么,默默地哼起一句老歌,我只会哼这么一句:“美丽的哈瓦纳,那里有我的家。”而这里的“哈瓦纳”,并不在古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