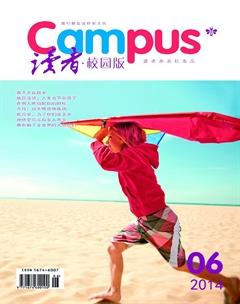在别人瞧得起你的时候
2014-05-14 13:11蔡康永
读者·校园版 2014年6期
蔡康永
我在一所私立学校待了将近15年的时间,从幼稚园一再免试直升,一直升到高中毕业。
我代表这所学校参加了很多比赛——作文、演讲、辩论,从这些比赛拿到的奖状,足够当壁纸用。
我也不间断地当班长,当模范生,当学生会主席,当毕业生代表,可是,我自己心里很明白——
对这些比赛,这些“公职”,我都没有热情。
我从来没有把那些冠军奖杯当成是光荣,我也从来不认为担任那些“公职”是为了“服务人群”。
我只是凭丛林动物的本能知道,这些冠军奖杯和公职头衔,都可以让我更任性,享受更多特权,也更方便地摆脱困住我的课本里的世界。
我很冷淡而有效率地完成一次又一次的比赛,来赚取我要的空间。
爸妈常常困惑,搞不懂我为什么出去比赛得了冠军,回到家却绝口不提。
他们不晓得,我是以这些冠军为耻的。
我的作文、演讲、辩论,全部都充满了我一点也不信的谎言,用尽了我觉得很廉价的表达技巧。我不得不引以为耻,因为这些跟光荣无关,跟热情无关,只是为了换取更多小小的、不被控制的特权而已。
这是我在这所学校从幼稚园到高中,学到的重要的东西:人,在某些别人瞧得起你的时候,你要学会瞧不起你自己。
高中的最后一年,我终于用行动唾弃了自己的特权,我编了说实话的校刊,让自己被学校记了大过,用烂成绩惊险毕业,离开这所学校。
我某种程度地珍惜这段“高度政治化”的少年岁月,我从中体会到不管是腐化的乐趣,还是反叛的快乐,都替后来的我省掉了很多时间,让我没有再耽溺在无聊的权力游戏里。
教育,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把你抛到空中,接近一下星星;再让你跌进沟里,闻一闻自己的臭。
如果你运气不错的话,你会闻得到自己的臭,你会把自己洗干净。
我的运气还不错。我闻到了自己的臭。
猜你喜欢
湘潮(2021年12期)2021-04-15
人民论坛(2018年25期)2018-10-13
幼儿教育·教育科学版(2015年9期)2015-11-16
党员生活(2014年5期)2014-08-12
小猕猴学习画刊(2006年4期)2006-05-24
东西南北(2000年1期)2000-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