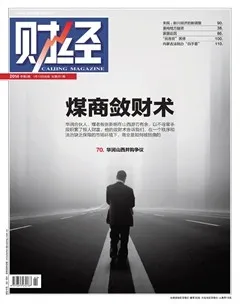伯明翰往事
众所周知,如果没有现代英国文学教授理查德·霍加特,就不会有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未必众所周知的是,倘若没有他的专著《文化的用途》,就不会有旨在揭示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的文化研究。
霍加特自称天生的社会主义者,其职业生涯始于赫尔大学成教部,为工人及其子弟讲授文学课程;他于其间对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观察与思考,促成了1957年出版的《文化的用途》。
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确认工人阶级的政治及文化身份,霍加特选择了以文化变迁为主题,以市场化的大众文化形式对工人阶级传统精神气质的影响为重点,以一种内在分离的结构,分两部分考察了“过去三四十年里,工人阶级文化的变化,特别是因为这些变化正在受到大众出版物的鼓励”。
霍加特认为,随着美国电视、流行音乐、犯罪小说等新式大众娱乐引入,20世纪5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某些重要方面,灾难性地出现了“一种恶化”,即自然、健康、淳朴的“人民文化”变为堕落、时髦的“大众文化”,英国因此成为一个文化上的“无阶级”社会。
这难道不是一幅F.R.利维斯式历史文化景观吗?非也!霍加特查看社会弊端时,通过肯定大众能动性,完成了他对利维斯主义的超越。比如,霍加特反复重申他对工人阶级能力的信任,认为他们能够抵制大众文化的控制。
即是说,大众有能力舒适自在地生活于陋室之中,有能力把家内生活与家外生活相分离、把“真实”生活与娱乐生活相分离。
通过肯定“属于人民”的文化或工人阶级文化、强调工人阶级的能动性,《文化的用途》成为“20世纪中叶的发轫性文本之一”,在催生雷蒙·威廉斯的《漫长的革命》等同样旨在形塑文化研究的著述的同时,赋予了霍加特巨大的象征资本。
1962年,霍加特凭《文化的用途》成为伯明翰大学英语系现代英国文学教授,旋即提出招收文化研究专业研究生的要求,以便继续《文化的用途》所开启和代表的工作。伯明翰大学英语系尽管不愿支持却又不能公开反对,于是给他设置了经济障碍,拒绝为他投入经费。几经努力,霍加特从《文化的用途》的出版社等机构,获得经费,于是便有了他在1964年春宣告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成立,开启了文化研究的学科历程。
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生“应邀”沿着霍加特在《文化的用途》中所开创的跨学科方法,围绕家庭女佣、电影、马克思理论等话题,开展了富含批判性、实践性与参与性的智识工作。
研究中心放弃传统的课堂教学,建立研读小组以组织其日常教学。所以,该中心的研究成果大都载有集体实践的特征。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将其不以学习理论或攻读学位为首要目的学生,培养成了日后驰骋于文化研究疆场的知名学者,包括黑兹尔·卡比、保罗·吉尔罗伊等等;他们与霍加特等老师一起,构成了文化研究领域内至今无人能出其右的伯明翰学派。
必须指出的是,成立之初的研究中心规模极小,除主任霍加特以外,仅有助理斯图亚特·霍尔、秘书迈克尔·格林。三人小团队不经意间成为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长期传统;他们励精图治促成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为英语世界,乃至全世界最著名的文化研究机构。
即使是经年之后,不列颠岛内外的文化理论家或批评家每每谈到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时,赞美之词依旧溢于言表。安东尼·伊斯特霍普认为,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所开展的工作堪称对英国文化研究最重要的介入;在劳伦斯·格罗斯伯格眼中,在以非中心化为特征的后现代语境中,“仍然有一个像中心的东西——准确地讲,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特别是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工作”。
现在,直接联系着霍加特、《文化的用途》、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文化研究已然作为一门学科、一种研究范式从不列颠播散到世界各地,引发了全球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在帮助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置身其间的社会的同时,看到了想象未来的一种别样可能。一个人、一本书、一门学科;人生如此,夫复何求?
作者为社科院外文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