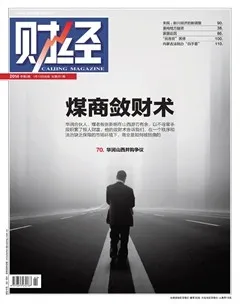吃活食
龙虾上桌,贵客停杯投箸。何故?因为那虾是活的,古人云: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
活着吃,虾也会“眼珠子滴溜溜转,放射出可怜的光”。这菜名叫“龙虾刺身”,刺身者,日本话也,所以这吃法应是从日本引进的。日本菜叫“日本料理”,如今我们也跟着叫,还有叫它“日料”的,哈日之态可掬。
日本料理这种词,还有日本画、日本纸,都是明治年间搞文明开化,引进西洋事物时制造,以示日本所固有,也就是江户时代以前已有之,虽然基本都来自中国。相对于“洋食”,也叫作“和食”。和食难以定义,总之是日本人做的、日本吃的饭菜罢。不久前,这和食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非物质文化遗产。
欧洲人早就非议他们活吃鱼虾蟹贝。日本政府向世界推广和食,开列了怀石、寿司、鳗、烧鸟等,却不提和食的头号代表刺身,莫非怕惹是生非。
我爱吃日本菜,尤其再配以日本酒,乐见和食被列为文化遗产,更提高饕餮的档次,但对于推荐的几条理由却不大以为然。其一是食材多样而新鲜,保持其原味,可是日本大部分食材靠进口,更何况食在广东,那里食材利用之多,以至带翅儿的不吃飞机,带腿儿的不吃桌子。至于新鲜,猴子也知道吃新鲜的东西,恐怕算不上人类的文化成果。
我们说尝鲜,日本叫作“旬”,也就是旺季、应时。日本战败后,经济才见起色的时候有个社会评论家叫花森安治的,写过一篇杂文《不吃日本菜的日本人》。他说,鲐鱼最肥时上不了高级菜馆的菜谱,厨师用的是不合季节的鱼,蔬菜是冬天竹笋、春天茄子、夏天松蕈。物以稀为贵,大量上市的食材不值钱,那就是平民百姓的吃食了。
日本人确实比较有季节感,这是四季分明的自然环境养成的。也因为是岛国,四面八方都是海,海里鱼有汛,跟着季节吃。但随着冷冻技术发达,鱼的“旬”已有些错乱。温室栽培,四季如“旬”。日本俳句是描写四季自然及人事的短诗,格律之一是需要用“季语”表现季节,现代季语有5000多,恐怕季节也就不分明了。
日本饮食文化完全在中国影响下发展起来。稻作远古从大陆传入,17世纪以后普遍用水车为动力,吃上了精磨的白米饭,面食也逐渐流行。自13世纪后半的100年间从中国渡海而来的禅僧,有案可查的就有30来名,他们带来禅宗的“精进料理”(素菜),再传入民间,构成日本饮食以蔬菜豆类为主的基础。茶道从精进料理派生出“怀石料理”,讲究形式,造成日式饮食的审美。餐馆把怀石料理去掉与茶相关的部分,以酒为乐,演变为“会食料理”。这类料理也就是我们说的席。
一部中国史,好像吃是真正自由的。相比之下,譬如675年天武天皇颁布肉食禁令,1871年明治天皇带头吃牛吃猪,日本饮食几乎一向由当权者规定,并非民众的创造。不许吃四条腿,只好大吃没腿的鱼(包括鲸),所以吃鱼的习俗也不全是岛国的缘故。一菜一汤(另外有咸菜),是物质匮乏时代当权者为节俭而强加给庶民的生活方式,甚至有的诸侯国连“一菜”也严加禁止。
一个人,一个民族,似乎最难改变的是饮食,这主要与风土环境有关,习性倒在其次。任何民族的菜肴到了别国,都会与当地的口味相结合而变味,不可能保持纯粹性。
日本把菜刀叫“庖丁”。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日本人切刺身,未见刀功多么了不得,但一刀专能,据说其锋利不破坏细胞,把原汁原味封闭在鱼片里,吃起来鲜美。
历来有一个说法:日本菜是用眼睛吃的。餐饮的第一要求是好吃,摆盘也好,器具也好,形和色须有助于好吃,以致享乐。功夫下在造型,餐桌上常常喧宾夺主。我吃过一次寿司,用的是陶艺家、美食家鲁山人烧制的陶器,价钱贵出两三倍,也吃不出特殊的味道来。
日本菜大致有三种味:盐味、酱味、鲜味。他们觉得鲜,我们吃来是没味儿。
中国的鲜味是创作出来的,而日本的鲜味几乎是生的同义语。人定胜天的劲头儿使中国人非把天然的东西做出不天然的味道不可。日本有各种道,茶道柔道武士道,唯独没有味道。
作者为旅日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