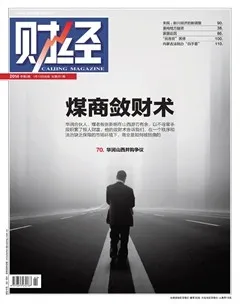公债变公灾
当大清国中央计划发行1亿两公债时,并没有想到,这笔公债会迅速变成一场“公灾”,不仅搅乱了官场,也引发了民间的群体性事件。
1898年3月2日,光绪皇帝批准发行“昭信股票”,以应对《马关条约》的巨额赔款给国家财政带来的压力。
之所以叫“股票”,回避“公债”的名称,是因为在四年前,曾有过一次失败的公债发行,弄臭了“公债”二字。
官员捐款潮
那次公债发行,是在1894年甲午战争期间。为了弥补军费开支,中央决定向民间借款,发行“息借商款”公债,条件十分优厚,月息高达7厘,而且借款在1万两以上者,均可授予虚衔封典,享受相应的政治待遇。但最后只募集到1102万两白银,效果很不理想。
究其原因,除了仓促上马、规则设计粗糙之外,最为致命的是官僚机器将此“借款”演变为“勒索”。当时户部还相当敢讲真话,给中央递交了一个报告,题目就是《地方官借机苛派勒索折》,毫不掩饰地承认:“数月以来,道路传闻,苛派抑勒之风,迄未尽绝。”报告认为,政府的实际借款是有限的,但这一政策却给贪官污吏们勒索提供了无限机会。推出半年后,中央就对这次公债发行紧急叫停。
再度发行公债,改称“股票”,并取名“昭信”,取“以昭大信”之意,就是试图避开四年前第一次公债发行的负面影响。
发行“昭信股票”,最初也将摊派作为主渠道,但是户部担心,摊派“迹近抑勒,窒碍难行”,修改后的方案是以奖励为主:“如派办筹借人员多方劝谕,能借巨款,十万以上准从优奖,五十万以上准破格优奖,以示鼓励。”户部没有想到,这场公债还未对外正式发行,就已经在官场内变身为另一场捐款潮。
将“认购”变为“认捐”的带头者,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恭亲王奕。这位63岁的亲王,在“昭信股票”尚未发行之前,就带头认购了2万两(相当于如今人民币400万元),而且,他宣布放弃领取任何债权凭证,“不敢作为借款,亦不仰邀议叙”,将这笔款项当作自己给国家的捐款。
在恭亲王的带动下,各级官员、尤其是高级干部们,无论是否愿意,都纷纷表态,愿意为国家财政捐款,而放弃领取“股票”凭证。《申报》直言:“得恭亲王为之倡率,则内外诸大臣有不得不勇于从事之势。”
对于这场政治“秀”,光绪皇帝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强调:“缴银领票更于大局多所裨益”——无偿的捐款,不仅改变了发行“昭信股票”的初衷,且在领导干部们解囊捐款后,留给广大商民们“自愿”认购的空间更小了。但政治风向已经形成,官员们哪里还会再去索要“股票”呢?光绪皇帝也就只好“俯如所请”,“毋庸给票,准其作为报效。”
不过,在公开发行“昭信股票”的文件中,中央明确说明,可以接受的“报效”,仅包括正式发行之前“已经认缴之款”。之后认购的,务必要根据规则,开具“股票”凭证。这倒更给官员们提供了一个表演机会:更多的捐款电报飞向北京,既做了廉价的政治表态,又领到了“股票”凭证,经济上并未受损。
更能激发官员们“急公好义”的,是中央组织部门决定,对在这次发行工作中“深明大义,公而忘私”的干部,在提拔和任用上,予以特殊倾斜。这场热闹的“报效”政治秀,具有了更优惠的回报方式。
庆亲王奕之子载振,就在这场捐款运动中,获得了头品顶戴的奖励,一跃进入中央领导级别的行列。
最为成功的则是山东巡抚张汝梅。张巡抚认购了10万两的“昭信股票”,随后宣布将本息都捐给政府,作为“学堂经费”。中央下令,对如此“好义急公”的干部“深堪嘉赏”,而奖品是张汝梅的三个儿子均得到提拔。其中,已经担任兵部郎中的张书兰、工部郎中的张书年,均以知府选用,而三品荫生张书恒则以主事选用。
在认购和捐款上手笔颇大的蒙古王公们,收获也不少。最得意的应该是贝勒车林桑都布,他被封“郡王”衔,而且是“世袭罔替”,这在平常,即令军功也未必可得。至于给其他蒙古王公们颁赐黄马褂、紫貂褂、花翎等等,更是不一而足。一些认购或者捐款者,干脆直截了当与中央谈起了生意经来,某蒙古王公就公开索要双眼花翎、龙缎靠被等。
大面积的奖励,令“昭信股票”的发行实际成了另类的“捐纳”卖官,以致日后梁启超在回顾中国公债史时,将“昭信股票”当作是变相的卖官运动。
摊派出政绩
对于发行“昭信股票”,中央出台的激励政策明确规定:凡能筹集到10万两以上的官员,将给予奖励,而筹集50万两以上的,可得到破格奖励。
重赏之下,“昭信股票”的发行变成了一场横征暴敛。
最早出事的是京畿地区。顺天府“东路厅”和“西路厅”不惜动用警力,“拘集商民,勒令认捐”,激起民众反弹,惊动中央。中央下令顺天府府尹胡“确切查明”,胡很快拿出了处理意见:“东路厅”的问题被归咎于“临时工”,同知刘仲仅被追究“用人不慎”的责任,“交部照例议处”;“西路厅”谢裕楷亦仅被调离,“开缺另补”。
随后,四川总督恭寿被弹劾“好谈嗜利,罔恤民艰,纵容家丁,任用劣员办理昭信股票,令各州县按粮摊派”。恭寿在成都设立了“昭信分局”,给各州县下达发行指标,“或十余万,或十万,或数万不等”,州县则依样画葫芦,层层摊派,最后都落实到底层的农户手上,“按粮摊派”。以每两银子的粮食税为基础,成都各州县的农户要加派5两多,而巴县则要加派8两,这等于是给农民们增加了高达5倍至8倍的沉重负担。为了完成任务,四川官员们在强行摊派之外,甚至还直接将“常平仓谷”(常项农业税)的“本款”划入“昭信股票”之中,挪用了正常的财政收入购买公债,以粉饰政绩。被举报之后,中央两次派人调查,却毫无结果,四川方面一口咬定“实无苛派扰累情事”,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
在山东,安丘县知县俞崇礼为了推行“昭信股票”,“计亩苛派,按户分日,严传不到者,锁拿严押,所派之数,不准稍减分厘”。中央在批转该案时,用了“殊甚痛恨”的重话,要求山东巡抚张汝梅严查并“据实参奏”。张汝梅则报告说,基层干部“涉于急切,究属因公得谤,情尚可原,且在任三年尚能勤政爱民,廉于自砺,应请免其置议”。
河南舞阳县知县张庆麟,发行“昭信股票”的手段更是直截了当,“勒令钱商买银三万两,每两比市价减一百文”,不仅推销了3万两公债,还在白银与铜钱的兑换率上大做手脚。考城县知县周应麟,在辖区内摊派了2万多两的指标,而此地的正常地丁收入仅1万多两,还不惜动用警力“拘传责抑”,结果引发了群体性事件,“商民赴省控诉者二三百人”;拓城县知县丁炳文,强销公债,“监押铺商,几至罢市”;西华县知县马嘉祯,在该县连年歉收的情况下,下令摊派5万两,加上他“常使心腹在周家口贸易贩运,营私黩货”,以至于“民怨沸腾”。
广东等地,甚至有会党组织,以反对“昭信股票”为旗帜,“簧鼓大众”,图谋起事。
不信官与吏
御史徐道在列举强行摊派“昭信股票”的弊端时,特别提及:这一公债已经成为贪官污吏对商民“藉端骚扰”的工具:“力仅足买一票,则以十勒之;力仅足买十票,则以百勒之。商民惧为所害,唯有贿嘱以求免求减,以致买票之人,所费数倍于股票,即未买票之人,所费亦等于买票。”无论是否认购公债,都已经受害匪浅。
康有为甚至认为,发行昭信股票是“亡国之举”,“酷吏勒抑富民,至于锁押迫令相借,既是国命,无可控诉,酷吏假此尽饱私囊。以其余归之公,民出其十,国得其一,虽云不得勒索,其谁信之”。
从中央的角度看,并非没有事先认识到强行摊派“昭信股票”的可能及其危害,已经未雨绸缪地明确规定:“倘各州县印委及经手劝集之人有藉端扰累勒捐者,准人告发,或别经访闻的确,即分别治罪。”中央所期望的,是官民的自愿认购,并为此发动了大规模的宣传动员,但是效果并不好。
康有为曾总结,公债之所以在中国暂不可行,是因为“中国官民之隔膜久已,谁信官者”?梁启超也曾系统地总结了发行公债的条件,第一条就是“政府财政上之信用孚于其民”。
面对着官僚机构将“昭信股票”的发行迅速异化变质,中央十分焦心。1898年,几乎每个月内,光绪皇帝总有几份批示,强调杜绝“昭信股票”的强行摊派现象。但在一个政令已经难以畅通的机制内,中央的雷雨到了地方上甚至都无法留下一滴雨珠。
随着向英国贷款成功,财政危机暂时度过,“昭信股票”真正成了鸡肋:不仅成效很差,所筹集款项极其微薄,而且成为大挖政权墙脚、刺激民怨的大问题。1898年9月,户部干脆提议,停办“昭信股票”,坦陈这是因为“地方官办理不善”:“办昭信股票原定章程,愿借与否,听民自便,不准苛派抑勒。嗣因地方官办理不善……四川山东等省办理昭信股票,苛派扰民。”
中央随即批准停办,光绪皇帝批示道:“朝廷轸念民艰,原期因时制宜,与民休息,岂容不肖官吏任意苛派,扰害闾阎,其民间现办昭信股票著即停止,以示体恤,而顺民情。”
以失败收场的“昭信股票”,已经给政权和国家造成了巨大伤害,大清国的政府信用进一步走低。《申报》感慨说:“自昭信股票之信用失,而国内之募债难。”“此后虽煌煌天语,悬诸通衢,曰革新庶政、预备立宪,毅然欲见诸施行,蚩蚩者氓皆掩耳而走,反唇相讥曰‘是给我也;是我也,是犹之乎昭信股票也。’而莫之敢信,莫之敢应!”
晚清大员汤寿潜直言不讳:“吾民之信朝廷,每不如其信商号。大小商号之设,其就近必有以银存放生息之人,独明诏息借,而吾民反深闭固拒,非民之无良,敢于不信朝廷,特不信官与吏耳!”
作者为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