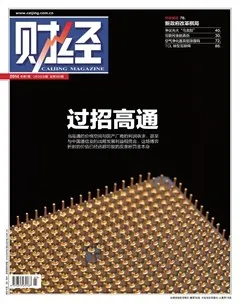高居翰
去年以来,国内外几位著名的中国美术史开拓者相继离世,如牛津大学的苏立文教授,中国美院的王伯敏先生,还有就是刚刚逝世的高居翰(James Cahill)先生。
他毕生致力于中国绘画史的研究,寄托了对中国文化的深切情感。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先后担任弗利尔美术馆中国艺术部主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艺术史系教授,其与台湾、大陆文物博物馆和美术史界的频繁交往,也影响了众多学人。他的主要著作已陆续在大陆和台湾翻译出版,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绘画史学科的发展。
在中国美术史研究领域,高居翰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保持着极高的国际影响力,其对中国美术作品的解读与研究,也影响了几代西方学者。即便受困于语言能力以及作为文化“局外人”的理解局限,他仍确信这些工作值得付出宝贵时光。
他敢于挑战陈旧理念与定论,认为一些被视为正统的观念对人们理解问题并无太多帮助,有时反倒造成障碍。正是基于这一看法,高居翰有意识地站在异端者立场,提醒人们注意被排除在常规讨论之外的艺术家,并对那些宏大的“核心真理”提出异议,试图重新发现那些被刻意遮掩的绘画领域。
高居翰,1926年8月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他于1943年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修习英语文学,后改学日语。此后从军,于1946年前往日本担任随军翻译,还去过朝鲜。正是这次亚洲之行,让他深爱上中国书画。1948年,他回到伯克利,于两年后获得东方语言的硕士学位,1958年获得密歇根大学中国艺术领域的博士学位。
在高居翰早年的研究中,曾得到许多前辈扶持,他不止一次在文中满怀敬意地提及。他年轻时由于喜龙仁推荐,获得写作其代表作《中国绘画》的机会。之后也不吝提拔优秀的年轻学者。
若说影响高居翰终身致力于研究中国绘画史的大事件,则是协助组织了1961年台北故宫艺术品赴美展览——“中国瑰宝展”。此次展览在华盛顿、旧金山等城市获得空前轰动,因为从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陷入变乱,普通美国人再也难以见到珍贵的中国艺术品。
在这之后,他到台北故宫博物院亲自研究和拍摄文物图片,为编写《中国古画索引》打下很好的基础。
高居翰很早就开始收藏绘画,并有许多机会接触原作,作为一名艺术史学者,可以说相当幸运。但与此同时,身兼学者与收藏家的双重角色也让他遭受不少非议。比如,有人指责他对张宏的推崇是为自己收藏的《止园图》抬高身价。其实,高先生收藏的几幅图在20年前一次展览后,便已换给洛杉矶县立博物馆。那以后他对止园的持续关注,则实在是出于一种难以割舍的学术情结。
早在学术生涯巅峰的1978年,高居翰先生就已基本完成专论晚明绘画的《山外山》,同年又受邀主持哈佛大学诺顿讲座,于1979年春以《气势撼人:17世纪中国绘画的自然与风格》为题发表了六次演说,讲稿于1982年结集出版。
高居翰先生历来重视中国绘画图像库的建设,视其为提高美术研究水准的基础工作。他于1980年编写出版《中国古画索引》,为建立国际化中国画图像数据库做了重要的基础性铺垫。他仔细过目古代绘画的图像细节,用英文对画面内容进行详尽描述。这样细致的工作,令该书成为研究中国古画的重要参考工具书。可以说,他对中国绘画图像和视觉文化的开创性研究,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文化在现代学术世界赢得广泛的尊重。
除了已有的学术成就,他还勇于推动学术进步,敢于挑战传统,尽管并不是他的每个看法都被广泛赞成,比如他对后期中国写意画所持的否定态度。前人均认为元朝以后的文人画是自娱自乐,高居翰却通过画家书信的来往和记载,写出一本《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结合画家的生活方式、作品的市场流通,雄辩地说明画家还是要卖画的。
1999年,高居翰对《溪岸图》的质疑在国外引发激烈争论,集中反映出当时美国学术界执牛耳者方闻与高居翰两人的不同观点。他们分据欧美学术重镇,其学生门人各自形成派别,针对该画的真伪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为此,大都会博物馆专门召开研讨会,并出版《溪岸漫步——王季迁家藏中国绘画》的图录,详细介绍了王季迁所藏历代名画的背景,每幅作品都有详细说明,其体例与内容堪称海外中国书画著作之经典。
这场论战虽不乏火药味,但双方择善固执的立场和条理分明的论证,为当下的中国绘画史研究树立了良好典范。
高居翰先生曾经自谦是中国美术“一个旁观的他者”。事实上,他身为外国人,进而成为研究中国美术史的著名学者,走过了一条从“局外人”到“局内人”的艰辛道路。也正是因为他是外国人,才拥有一种观察中国绘画中图像细节的独特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