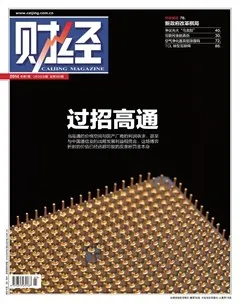非洲病
曾有人说,有一种病毒叫非洲病毒,感染时的症状是对非洲产生无法克制的热爱。许多在非洲生活过的人,都会染上这种病毒。我承认自己是这样,作家多丽丝·莱辛一定也是这样。她的文字就是证明。
以前住在约翰内斯堡时,常常到北方的乡下去过周末,有时靠近博茨瓦纳,有时靠近津巴布韦,那里的景致风物一如莱辛所描述。
莱辛于1919年出生于现今的伊朗,父母都是英国人,5岁时全家迁往南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1964年莱辛在一次采访时说,在她家乡,白人农场主相隔的距离非常远,互相之间很孤立,空间很大,不像英国那样大家挤在一起,需要互相影响、谦让、认同,所以,一些在英国很平常的人,到了南部非洲那样广袤的空间里,能够放心大胆地让个性或怪癖伸展扩张。
南非也是这样,这里能让人大刀阔斧地做一番事情,这里让人荡气回肠,这里时刻有着生与死的较量。从南非看英伦,就觉得北方那个岛国实在很琐碎、很温和,那里的人在乎的事情,实在微不足道。
与40岁以上的南非人交谈,有着自由思想、曾经做过反种族隔离斗士的,都热爱莱辛的作品,并称她的作品对他们影响极大,是她给了他们看世界的另一双眼睛。
我通过读莱辛的自传,解开在非洲住了六年都没能解开的一个谜。我一直想弄明白,当年白人和黑人完全隔离,住宅区、商店、马路、公园、海滨、公共交通等等,都有两套系统,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大多数的白人,怎么就能心安理得?我曾问过一些人,被问者都会用奇怪的眼光看我,仿佛在说:有什么奇怪?现在的南非,在很大程度上仍是这样。
这让人惊心。莱辛所描写的60多年前的生活,让人觉得似曾相识,好像她写的不是往日的罗得西亚,而是当代南非的许多角落。许多对话、许多心情、许多细节,在新民主十多年以后的南非仍很平常,让人发问:在非洲大陆,历史的车轮究竟走得有多快,是往前还是往后?
莱辛在离开南罗得西亚后,因她的政治主张而有25年没能回去。如同每一个在非洲长大的人,她日里梦里都会想念非洲辽阔的旷野。美国作家乔伊斯·卡罗尔·奥茨在上世纪70年代采访她的一文中,就特别提到莱辛公寓墙上贴着的非洲花卉照片。
1980年罗得西亚结束了白人统治,黑人领袖穆加贝掌握政权,国名被改为津巴布韦,首都改名哈拉里,莱辛的故乡才欢迎她回去。1982年至1992年间,她四次重返津巴布韦,于1992年出版了《非洲笑声》,记录她这四次返回故乡的经历。这本书分为四部分,能看出津巴布韦独立十年的各种变化和以后的政治走向。1982年,让她感触最深的是家人和朋友头脑中仍然根深蒂固的对黑人的歧视;1988年和1989年她更多注意到黑人们抱怨变化来得太慢;1992年的那次访问,她的关注已经转向经济衰退、贫困加剧、腐败盛行、艾滋病蔓延、对土地和自然环境的破坏。阅读《非洲笑声》,就像阅读今天的南非。
库切说莱辛是“最有远见的作家之一”。确实,莱辛在1992年就预见到津巴布韦以后十几年的衰退:穆加贝从人民的领袖变成暴虐的独裁者,白人农场主被大量驱逐,肥沃的土地大量荒芜,通货膨胀达到上千倍,津巴布韦从非洲的面包篮变成饥饿的空饭碗。
在短篇小说《老酋长马希朗加》中,通过那个热爱非洲的女孩之口,莱辛写道:“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这是黑人的国度,也是我的国度;这里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我们所有人,我们根本不用把别人从人行道和街上挤掉。”
广阔的非洲土地可以容纳所有人,这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的算术。过去的白人统治者不会算,现在当政的黑人政治家似乎也不会算。记得我几年前采访图图大主教时,问起他对穆加贝的看法。图图说:“我很为他感到悲哀。他曾是极为出色的政治家,我曾非常钦佩他。但现在,我真不明白他脑子里出了什么问题,他完全发疯了。”
独立、翻身、当家做主以后,权力的膨胀让无数个黑人领袖宣称“这是我的土地,这是我的国家”!以一种新的种族歧视代替那种旧的种族歧视,这可以说是非洲这片最美丽的土地上最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