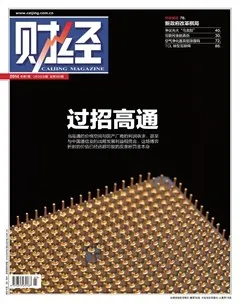改革忌急功近利 调整忌优柔寡断
今年全国“两会”的召开,激发人们对新一轮改革行动落实的热情。而略显疲软的经济走势,又让人们感到些许春寒。如何在改革、调整与稳定之间求得平衡,如何实现稳中求进,又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
这其中,以改革促发展、通过改革释放增长红利,已成朝野共识。此前召开的讨论国务院拟提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即指出,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向深化改革要动力”。
通过改革来修正阻碍市场发挥基础性资源配置作用的扭曲性因素,求得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是深化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同时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改革是一项长期的进程,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缜密的顶层设计和审时度势的推出节奏。从某种意义上讲,改革是利益重组的过程,是去腐生肌的过程,是挥别旧招式学习新路数的过程,其中有阻力,有风险,甚至会有反复,需要有忍受阵痛的能力和咬牙顶住的定力,非如此,不能收获改革红利。
寄望通过改革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往往是不切实际的,更多时候我们反而要妥善应对改革带来的逆增长效应,从而以短痛换取长治久安。关于改革的种种急功近利的想法,一方面会让我们在需要啃硬骨头时裹足不前,另一方面会让我们借改革的名义寻求新的增长“捷径”,不仅贻误改革,更会遗患后世。
更多将长期而非即期增长与改革挂钩,更多将改革努力聚焦到各项支撑中国长期增长的市场要素的培育,方为以改革促增长真义。前述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即指出,要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改革发展,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以创新支撑和引领结构优化升级。要促进教育事业优先发展、公平发展,推动医改向纵深发展,促进文化事业和产业发展,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提出改革重点清单,即体现了以长期改革来谋取发展红利的思路和决心。
改革忌急功近利,关键领域的调整则应力忌优柔寡断。在扎实推进长期改革的同时,必须下决心处理困扰中国经济正常运行的棘手议题,以免迁延时日,令其成尾大不掉之势。当下需当机立断给出解决之道的一是债务重组,二是清理产能过剩。在某种程度上,两者又互为表里。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其新著《动荡的世界》中反思金融“脱实入虚”时指出,金融体系在市场经济中的最终目的,是把一个国家的储蓄加上来自国外的借款,转变为对工厂设备和人力资本的投资,经资本带来风险调整后的最大收益率,并促进这个国家的人均小时产出率的最大提升。
如今我们的金融体系似乎无法胜任此使命。从去年的钱荒到日前的信托违约事件,都凸显巨大总量下的资金饥渴症,表明金融体系正在受累于负债链条紧绷之“不可承受之重”。不尽快求得突围路径,则不仅危及当下的增长,还会累及正在推进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一个“余额宝”即足以让整个银行界叫苦不迭,金融体系在应对这种另类利率市场化压力“测试”中的脆弱性一览无余。
监管层不再往资金池里放水,其初衷是正确的。一方面监管层希望断绝地方政府和影子银行体系借新还旧的迷思,另一方面希望盘活存量将资金逼入实体经济,防止资金空转。然而,正如格林斯潘所指出的那样,“人们总是倾向于通过逐步收紧货币政策,以渐进方式去除泡沫,但在实际操作中,此类渐进政策似乎从来没有奏效过。”此轮债务的形成有着强烈的行政色彩,将板子全打在地方政府和银行身上是不公平的。又要银行出资“襄助”4万亿大业,又要其执行相对严格的存贷标准和资本充足率,银行只能求助于表外业务和各种通道类公司来实现“银政合作”的曲径通幽。债务激增以行政始,而寄望以利率市场化倒逼债务消化终,几近无法完成的使命。
我们必须看到,各级政府的任期制和日前出台的相关离任债务审计的文件,反而强化了地方政府饮鸩止渴的冲动。因此到底该放出多少“适量”资金,以使其既不至于渴死,又不至于重回借新还旧老路,已成为监管部门和市场角力的焦点,其间种种博弈耗时费力,又增加了市场的种种不确定性和金融体系的运营成本。
为今之计,无论是展期,还是清盘,都要尽快给市场一个清晰的信号。债务重组就是中央、地方和银行三方划定责任和权益的过程,需要及早划定盘面。与其大而化之奢谈与债务相关的系统性“改革”,不如以底线思维踏实做好各种计提和拨备等应对方案。
去腐方能生肌,出清才能轻装上阵。通过金融再造恢复正常的供血功能,通过产能重组加快调结构促升级,中国经济才能进行新一轮优质投资,实现创新驱动,进而以合理区间内的经济运行为改革赢得时间和空间,以改革为发展谋得长期可持续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