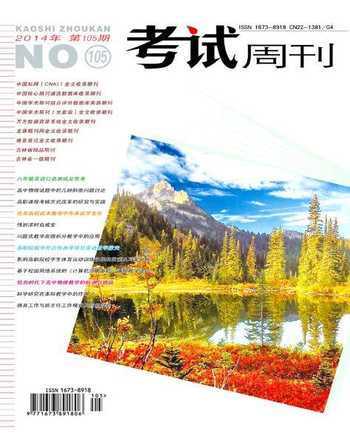卡尔·曼海姆“非理性要素论”研究
文丰
摘 要: 卡尔·曼海姆从“非理性要素”视角为我们揭示了社会内部冲突的重要根源,对于道德本身而言,非理性行为的存在平衡了绝对道德主义对社会不同阶层(利益集团)的伤害。非理性要素具有的特殊含义使社会成员能够在虚无主义的汪洋中找到存在意义的归宿地。
关键词: 卡尔·曼海姆 非理性因素 社会结构
“理性”一词是启蒙运动的核心概念,理性作为启蒙主义哲学家对人类社会生活关切的首要目标而言,在二十世纪初期特别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到了强烈质疑。卡尔·曼海姆着重从社会发展状况出发,深入揭示社会生活中的非理性事实。在十九世纪以来的乐观主义氛围中,欧洲的知识界形成了对于理性引导人类生活的幻觉,这种幻觉在十九世纪末期几乎达到了顶峰。但是,在这种幻觉的背后,许多思想家发现了西方的危机,斯宾格勒的预言几乎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成为现实。但是理性的人类并没有吸取什么教训,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踵而至。卡尔·曼海姆成为第二个现代先知,他试图从非理性历史中寻找当代悲剧的道德根源,他实际上比斯宾格勒走得更远。在深入社会痼疾的根底之后,借由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将非理性要素逐一展示出来。
关于历史哲学的思辨分析,在曼海姆这里成为一种累赘,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依赖大量档案文献进行细节上的区分,而这种方法直接导致历史的碎片化。在历史长河中,各个社会都有自身的顽疾,有些社会未能克服这一疾病,最终病故。那么在现存文明社会中,如何认识社会内部冲突的原因就成为我们医治社会疾病的一条途径。非理性行为的出现,有许多背景因素可做参考,但是有一条根本性因素使我们不得不予以严肃对待,那就是由于人类个体条件先天的不均衡导致的社会资源分配的失调。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首先击溃了社会成员的心理防线,心理失衡导致的恶性竞争始终贯穿自由竞争的主旋律之中。这种心理失衡带来的巨大推动力使一部分人——实际上为数甚少,成为社会成功学的典型案例,这种现象尽管极为荒谬,但还是给更多人造成了心理影响。成功是可控的,这种所谓的理性教化导致的必然论风靡所有“文明社会”,特别是在推崇竞争的社会中。现代科层制在实现社会控制的同时,又将上述“理性主义”强化为社会信仰。功能主义的理性观使人们无法在自我实现过程中去除“功利主义”的暗影,这种自我暗示下的成功合理主义导致了大量社会失衡现象。社会工业化进程是本质上非理性成功学的经济根源,表面上复杂的社会生活,实际上被简化为科层制管理体系与流水线生成体系,对此,有人产生强烈的错觉,即科层制与流水生产线在本质上分明是合乎逻辑的理性化产物,为何反过来成为社会非理性的结构性因素。
为了详细分析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回到理性主义的哲学源头,即人类生活的目标是什么?如果答案是个体利益最大化,那么在文明社会中,经济充分发展,创造出海量社会财富,一旦满足每一个人的生存需要,历史自然走向完结。实际情况比这复杂得多,仅仅物质上的充裕已经满足不了人本身了,精神生活上的追求使一切生活目标都指向一个较为抽象的(相对于物质生活而言)概念,即个体的幸福究竟是什么?理性要素虽然可以在社会生活中被轻易地理解为合理地安排生活,并满足个体的基本需求,但是自我内在的非理性给予了社会心理学取之不尽的研究题材——个体的心理满足成为首要的研究对象。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说,人类的非理性行为都是个人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从各个社会的道德评判标准出发,相互矛盾的行为规范构成了一个相对严密的道德体系。社会成员的生活习惯与这一体系保持着高度的关联性,而这一体系的首要原则就是对于个体非理性行为的控制与调节。控制意味着道德体系必须防止重大的“违法”行为对社会结构本身造成的致命伤害;而调节则意味着道德体系不可能完全根除非理性行为的存在,但这不是道德对于非道德的姑息,而是对非理性的一种妥协。社会控制的强化力度本身就反映了一种集体的非理性,看似合理的控制之下,是社会控制者对于社会生活的无限制干预。他们试图通过各种社会发展计划规范个体的生活,而事实证明,这是做不到的。对于道德的强调,最后蜕变成了对于社会秩序的必然要求,因为道德观念相互冲突,普遍伦理只有在最低限度上才能对个体产生规训作用,在一般情况下,个人行为不存在所谓的道德性,而理性却成为一种天然的选择,贯穿个体的社会生活中。
现代社会对社会内部群体的整合,越来越依赖于各种专业化分工,构成了生产体系,社会成员被按照一定社会生产集团划分为各种阶层,在社会政治生活中,都积极寻找各自的话语代理人。而在社会舆论中,精英阶层不一定能够占有绝对的话语优势,话语系统呈现多样性的同时,对被代表者进行阶层划分,而后将其中最大多数的一个群体作为自己的“后盾”——实际上是一种话语权篡夺行为。大多数成为沉默者,因为话语权并不在他们这一边,在道德领域的制高点上,舆论领袖们高高在上,控制着大众的意愿表达路径。因此,在某些情况下,所谓的社会舆论成为舆论领袖的个人话语,社会就此开始了对个体的行为塑造,即通过高度的话语垄断,产生唯一的认知机制,所有社会成员可以在私下对之进行怀疑,但在公开场合要么保持沉默,要么顺应它的要求。这种认知机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道德至上,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将社会问题简化为道德评判,通过各种专家的“科学”分析,形成所谓的社会共识,如果达成社会共识如此容易,那么就不需要政治控制机关的存在了。社会道德就此成为一种廉价的社会出卖品,尽管十分廉价——可以在综艺节目中任意制造,但还是被牢牢控制在少数人手中。从这个角度讲,社会的非理性行为可以是一种针对“社会共识”的反叛,我们必须清楚,廉价制造的道德不但不能形成社会共识,反而会诱发社会内部的分裂。正由于非理性因素的存在,才使所谓的公共意志、社会共识和廉价道德不会泛滥成灾。
卡尔·曼海姆深刻地揭露了民主化社会中的非理性源流,在西方式危机中,一种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极端个人主义已经成为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个人主义道德谱系中,非理性行为经常成为最能彰显个人自由意志的证据。在大规模社会危机中,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并不是消失了,而是转化成了“集体无意识”行为,也就是群氓主义。在曼海姆之前的哲学家中,不乏预言群氓时代降临的思想家。他们(包括曼海姆)都意识到过度工业化造成人的“非人化”(或者叫异化),这其中最大的心理遗产就是个体的原子化导致对人类存在意义和现实价值的强烈质疑。虚无主义与群氓主义可以说是工业革命创造出的一对孪生兄弟。个体对于社会现实的不满内化为对自我的价值贬低,存在感的丧失使个体的非理性行为达到空前高度,既然没有存在意义,那么对于社会而言就不负有任何责任。虚无主义的一个重大后果就是个人使命感和责任意识弱化,消解的存在意识,使非理性行为有了显著的合理性——个体存在的无意义意味着个人生存目标的无意义,为了存在而存在,成为一种合理的价值归宿。
在社会建构中,任何参与行为都可以给予个体存在意义,这又成为一种轮回式自我证明。个体意义必须从社会活动中获得理解与证实,为了实现理解,就必须放弃或者暂时放弃非理性行为,因为这种行为是个人获得外界证明的否定因素。在描述这一轮回过程时,我们不得不面对如此二律背反的结局,但至少在我们看来,社会本身又回到了“理性”轨道。
参考文献:
[1]卡尔·曼海姆,著.张旅平,译.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研究[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5.
[2]卡尔·曼海姆,著.徐彬,译.卡尔·曼海姆精粹[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