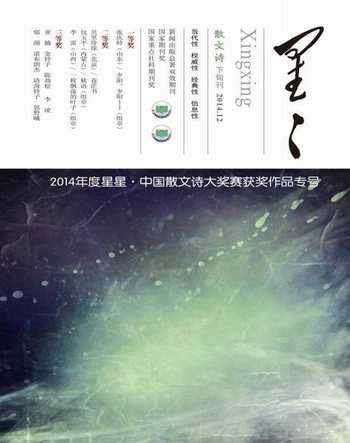描述一只鹰(组章)
郭野曦
“描述是我和鹰之间的搏斗,在这场搏斗中,我越是了解鹰的意图,越是容易失败。”[1]
——题记
一块铁
一只鹰在大野上盘旋,一块锈迹斑斑的铁,比刀锋在肉里游动的速度略慢了一些,却有说不出的冷漠和镇定。
我在用整个身心谛听一块铁在大野上的汹涌和轰鸣。
鹰,鼓荡的羽翼,巨大。苍劲。对灵长类动物的仰望是一种笼罩和覆盖。
高悬于头顶的一个没有炸响的雷霆,让燕雀们在风云激荡的高处,找不到柔曼的抒情散板。
一块铁,楔在闪电与雷鸣之间的一个掷地有声的证词。
犹如鬃尾乱炸的野马群在大野上拱起的一个野性图腾,使我崇尚的野性美在铁与血的交响中得以传承和延续。
血与铁的刀耕火种
鹰,钉死天空的一块铁,囚禁风、雨、雷、电的牢笼。
有铁的雄浑,血的激荡,有灵与肉交相辉映的壮美和大气磅礴。
云罅间不经意漏下一点亮色,洞穿我灵魂黑暗的部分略有剩余,但已足够我饱蘸笔墨,将一只鹰描述得越发亮丽和恢宏。
浩淼的苍穹在鹰的脊背上丧失了辽阔和空旷后,只允许安放一种灵魂,只允许有一个安放灵魂的位置。
为了不让头顶上的天空荒废掉,一只鹰抑或一块铁,在芸芸众生的仰望之上,开始了血与铁的刀耕火种。
骨头拔节的声响
鹰,不管从什么角度去看,都像我失散多年的孪生兄弟。
像我在草丛中埋下的一个伏笔,为了与持刀的螳螂一起在流血的伤口上拦路剪径。
我线条粗糙的描述无意间剥落几片灵魂的伪饰,让我看到自己的狭隘和自私;让我感到羞辱和愤怒,险些丧失描述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在我没有被鹰劫持之前,体会不出一块铁的殚精竭虑和苦心孤诣。
这时被猎猎雄风洞穿的大野,只剩下我对鹰的敬畏和顶礼膜拜;
只剩下一腔热血接近沸点时,骨头在流血的伤口里拔节的声响;
只剩下鹰搏击长空的羽翼折断的一地疾飞的雨箭;
只剩下鹰在闪电与雷鸣之间为苦难的大地挺身而出的警醒和昭示。
低声回荡的音符
借雷电在云罅里挤出的一点光亮,我开始了画框里的拭擦和打磨,直至阴暗的天空在积水的马蹄窝里折射出水的蔚蓝和清澈。
鹰,心底淤积的激情,就这样被激发出来。
鹰,跳下巉岩,舒展羽翼,但不飞翔,只是在苍茫的大地上狂奔。
不,是苍茫的大地在鹰的脊背上风驰电掣。
一只鹰,一块尚未冷却的铁,一个在闪电与雷鸣之间低声回荡的音符,遒劲、苍凉。
是肉体蹈火的独舞,是灵魂飞天的前奏,是天地间大美的回归和复原,以此拉开了野性图腾的序幕。
后记:一只鹰抑或一块铁,不是大音稀声的谶语,也不是大象无形的爻辞,是如歌的散板中触手可及的一张窗户纸,捅破了是色,不捅破,心有灵犀的时候可以在里面焚琴煮鹤、青梅煮酒。不论是英雄还是美人,在画框里都是诗意的留白和虚空。
[1]参见:(法国)波德莱尔《一八四六年的沙龙》第七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