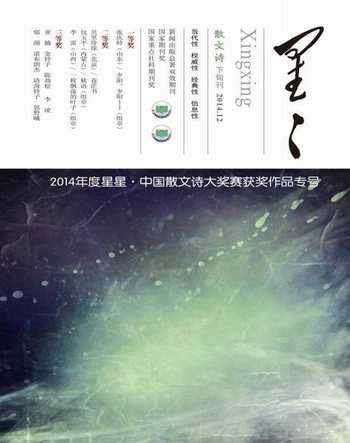我住长江头(节选)
金铃子
1
一个常常迷路的人。
穿越一座又一座大山,总是有一条河流为我指路。
我在一条奔流不息的小河旁停下来喝水。一停下来,就想起母亲。
大河就是我的母亲。
为婴儿哺乳的母亲。我饮着河水,饮着乳汁……鱼群在问好我,有女音、男音,甚至有孩子的声音。水族的精灵,一泓水似的让你一眼见到底。它们舞姿优美,声音古老。似古老的歌谣。
内心独白,娓娓述来。仿佛小鸟已经飞出了这里的疆界。
我曾经在大剧院听到船歌,调式和气韵如此相近。
我找到了声音的源头。来自这条生育我的河流。
唉。我离开过这条河流。游荡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生活在刀叉声和软木塞,喧哗声和辞谢声的混响中。
一个歌王也变得无所事事——和狂人、骗子、凑热闹的一起,用金黄灿烂的水擦面洗脸,活像一只花里胡哨的鸟,活像一个一天到晚寻求干坏事的人……只记得哼痛,早忘记歌词。
我从嘉陵江,长江,到乌江。从乌江,嘉陵江,到长江。
唉。我怎么可以错过一条溪流。错过一个爱人。
2
一只白鹭。
它仰视,一动不动,身躯修长而健美。身上散发出白色的光芒。仿佛一个倨傲的山人,只守护一样东西,青山的葱绿。
我在山脚就见到它古典的脖子,白色的云朵。
我惊异。如同惊异这行将就木的世界的回光返照。美好的事物,用逼真的烙印将一个单独去死的人挽留。
鸟群是无限忠诚于高山的,它们鸣叫……
“我送给你们,无需索取。”
我是为索取而来。
它们知道我全部的弱点。我脉搏里面充满欲望,如同七月的江河奔流不息。我向鸟群跑去,穿过一片片辽阔的森林,抛却时光,一小时又一小时。我向它们喊叫。它们沉默。
沉默是认领一个女人的证明。
一个孤零零的人像只黑色的草鸡在树林里奔跑。我被一种真实和虚幻推动。一种成为鹭的可能。
我听到扑翅之声。它们一小时像一秒的飞走了。
我呐喊。“我想要……”
像是沙漠里的呼声。呜呜地。呻吟地。在茫茫的森林。
3
山峦……我不能睡。我要永远的醒着。
我承认被一些东西伤害而不思索它们,它们在经过时弄脏了我。
我站起。坐下。又站起。
一天接一天积累起来的爱,入骨的疲劳,残缺的自尊让每一个记忆变色。真正需要处理伤口的时候了。消炎的车前草,退烧的树皮。
我只是向大山诉说。
“山,你在和我说话吗?人生就是一场梦,甚至连梦都不是。我常常把几枚珍贵的草叶夹在皮夹子里,它们很快就腐烂。我常常整天劳动,只要天亮就干活,四小时,八小时,二十小时,我呼吸着散发出恶臭的墨汁,闻着不能够理解生活意义的丙烯。我稍有反抗情绪,另一个我就把我蔑视。我不知道爱,爱只会让我看到真相,希望的枯萎。大地,但大地在摇晃,它长啸起来,一种悲哀的长啸。”
我看到子弹,人群变成荒野里的野兽。
“我没有儿子了。”她这样叫着,竟然没有哭。
……我不能睡。我要永远的醒着。
闪亮的启明星,我一闭上眼睛它就会熄灭。人类怎能没有方向。怎能没有美好的爱……在生命中留下。
有一种悲,有一种热烈的悲。
山谷知道。
5
狼林里还有狼么?
我嚎叫一声。呼唤我的同类。来吧。
我用蝴蝶、蜜蜂喂养你们。用头发嘴唇乳房喂养你们。你们是我留下来的许许多多孤儿。太阳一次次沉没又升起。在这个清晨,晨风吹拂,黑暗消散。人们都记得有一个懂法术的人用沉重的斧头将狼击碎。现在只留下爪印,空荡荡的狼林。我像苍白的云雾在林间穿梭。
哪儿去了?那眼睛纯洁晶莹,那叫声可以穿越长夜的漫漫、乌云的密布、快乐和忧伤。穿越我本身的天堂和地狱。
掘墓人,你挖掘的是仪式和罪之美。你埋葬的是如注的血流,声音。你工作非常努力,你戴着一顶粗陋的假发,一张大嘴巴,一张特大号的嘴巴,仿佛一个破旧的皮包,可以装下洋葱片、番茄、菜刀、避孕套。这个章法混乱的世界,你想埋葬什么?
广场上喷刷的不堪入目的广告。动物园里的小动物被无情的屠宰。阴谋论者昨天击落了飞机。安炸弹,泼硫酸,孩子被毒打致死。
狼群不知道这些。它们是朴实无华的姑娘,生儿育女,快乐而甜蜜。
没有了。当然没有。
身上的衣服已经破烂。思想已经破烂。爱已经破烂。
我突然想做一个狼人。森林里的落日撒在我的发梢,一定会长出一牙绿叶来。
或许更多。无法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