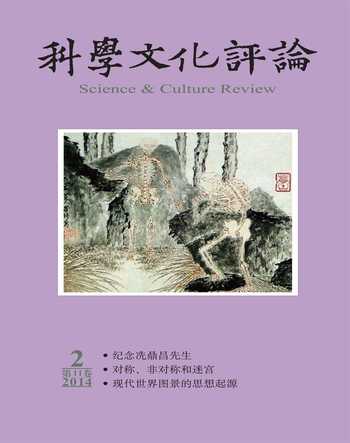无限的思念
胡亚东
“我的朋友”洗鼎昌走了!在对他的无限思念中,一些往事陆续涌上心头,这里记录下来与读者们分享。
我认识老冼不过30年,初识还是在上一世纪70年代末。当时喜欢西方音乐的知识分子又可以从无线电波中,以及可以买到的为数不多的音乐唱片中,恢复聆听音乐的爱好,那欣喜雀跃的心情是今天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洗鼎昌是物理学家,我知道他的物理学造诣很深,我的物理学只是大学水平,不过他后来从事的同步辐射研究却和我的化学专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算能有些共同语言吧。但是我和老冼的正式交往却不是从科学而是从音乐开始的。
那时候弄到一张新灌制的音乐唱片很不容易,我们两人都如饥似渴地到处寻找“雅音”。每人每次获得一张新的唱片,总是立刻让对方转录成卡式录音带拿回家去仔细品味,再次见面时首先就是交换彼此对新唱片的看法。应该说,老冼对西方音乐的理解很深刻,而我广为涉猎却未及他的深度。新世纪之初,福建教育出版社的任争健编辑策划组织出版一套谈音乐的丛书,希望找一些非音乐专业的人士如科学家和文学家来写,目的是,按照她的说法一“可以在他们对音乐梦幻般的感受中去比照他们完整的心灵,比照出他们的创造与音乐欣赏之间的不可言说的审美联系。含混地说,音乐是一种心境,它唤起人的联想和记忆;音乐是一对翅膀,它让人的想象力飞翔……音乐对我们欠缺的情感进行补充,高科技与高感情在他们之间得到了平衡。”(《月光丛书》编前言)为此,编者找到了老冼和我,要我们分别把前些年发表过的有关音乐欣赏的文章搜集起来,又增补若干新文,每人凑成一本谈音乐的小书。老冼的书名为《爱丁堡随想》,我的则名之《听!听!勃拉姆斯》,这也算是我们俩人的音乐交集吧。
如今老冼走了,看着这两本书,我就愈加怀念起俩人一道谈论音乐的情景了。他的书我觉得像散文,而自己的书更像随笔。散文和随笔似乎区别不大,但是从内涵来讲却大为不同:散文是“文”,随笔是“笔”;散文“灵”,随笔“拙”。从老冼的书可以看出他的功底,我则就事论事,好像少了一层未可名状的东西。我虽痴长他九岁,但是无论科学还是文化底蕴都用得上那个“略输文采”。这不是我的谦辞,称其“老冼”,一个“老”字又怎能表尽我对朋友的无比敬意?
我们对西方音乐的兴趣覆盖面颇广,从巴赫的巴洛克到德彪西的印象主义都在交流讨论之列。不过我似乎更多关注各种主义门派发出的声响,他则更多地沉浸在文化的思考中,就此而论他算是技高一筹吧。或许正因为此,我对20世纪的音乐就不怎么感兴趣了,算是保守派吧,老冼则不然,他非常喜欢马勒、肖斯塔科维奇等,谈起这些20世纪的音乐家的作品他会眉飞色舞,似乎比我年轻了许多。我曾在当时的列宁格勒生活过四年,也见过肖斯塔科维奇本人,觉得他的第七交响曲固然雄浑,却无法体现圣彼得堡这座历史名城的全部博大内涵。不过老冼对肖斯塔科维奇的特殊境遇及内心冲突的评论我是赞同的,毕竟我是见过肖、听过肖的。
谈到17-19世纪的音乐,我们的共同点就多了。老冼对宗教音乐的喜爱超过我,虽然我年轻时曾在北京的一所教会学校接受西方音乐的洗礼,从合唱团的男高音到四重奏的小提琴手,还曾连续多年参加由北京基督教会排练演出的《弥赛亚》圣诞大合唱,但是人却一直没有走进“天主”的殿堂中去。老冼谈到在教堂里听音乐和在家里听音响之不同,我是深有同感的。我也喜欢听古典主义作曲家所谱写的安魂曲,那是另一种形式的弥撒。老冼说安魂曲“是表达对于死亡的思考的音乐”,想必他的心灵一再受到安魂曲的抚慰和召唤。
在欣赏音乐方面我和老冼意趣相投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对音响设备的看法就是。现代科技固然创新极多,但是与其购置一套极尽奢华的音响来听亨德尔,远不如在教堂现场的肃穆气氛中听管风琴奏出的一首圣歌。对于这一点,老冼在他的《在教堂里听巴赫》中有动人的描述。再比如对近百年来演奏家的爱好,我俩也颇多相求相应之处:对小提琴演奏家米尔斯坦、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等人的推崇,我们是不谋而合的。还有对大作曲家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以及勃拉姆斯等人的作品,我们总是有说不尽的共同话题。虽然近年见面少了所论不多,但昔日共同论道的场景还历历在目,想到他的突然离去心头不禁黯然。
老冼热爱生活,从《爱丁堡随想》中也可看出他的高尚品味。我和他交往的前20年里,大概以音乐为主干,旁支上却根根叉叉地攀上了许多文化的野果。我们都喜欢养花弄草,也偶尔赏玩一些古物和字画。他住在中关村北区10号楼时,我还专门去看过他养的花,那是一盆很大的什么花,他颇引以为豪,故请我上门观赏。就是那一次我才知道他也是一位美食家,而且品味很高。当时谈的是什么美味佳肴我已记不大清楚了,印象中他对食物的制作及评论都很专业。更有意思的是,老冼还到厨房去做了一些点心来给我们品尝。我印象较深的是他对咖啡的知识,他掌握多种煮咖啡的技艺,我因不谙此道,老冼关于不同煮法及不同风味的滔滔宏论今日已经淡漠了,说实在的当时也没有品出不同煮法有什么不同,真是老“冒”了。不过我却在另一个地方意外地找补回来了。我知道老冼在爱丁堡生活过,于是问他懂不懂苏格兰威士忌,没想到他所知甚少,因为不太喝烈酒之故,而我恰好相反:咖啡我算外行,对苏格兰威士忌我却有些发言权。我对苏格兰的单一麦芽威士忌更是情有独钟,特别对那种陈酿的Double wood、甚至Triple wood品级的特别喜欢,老冼却是一窍不通。
老冼走了,虽已79岁够上了古人所谓耋寿之期,但我一直觉得他还年轻。他身上总是充满活力,有那么多的爱好,渊博的知识背后是深厚的文化底蕴。近年来我和他见面虽少,他那消瘦的身影,深邃的目光、谦谦君子之风度和装不出来的绅士做派,总是浮现在我的脑际。老冼走了,佛家称西方为极乐世界,如今他在那边一定有丰富的西方音乐陪伴着,他应该是满意的。
家里有一幅不知原来出自何人的条幅,抄下来带给老冼:
周鼎汤盘见蝌蚪,
深山大泽生龙蛇。
2014年5月于中关村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