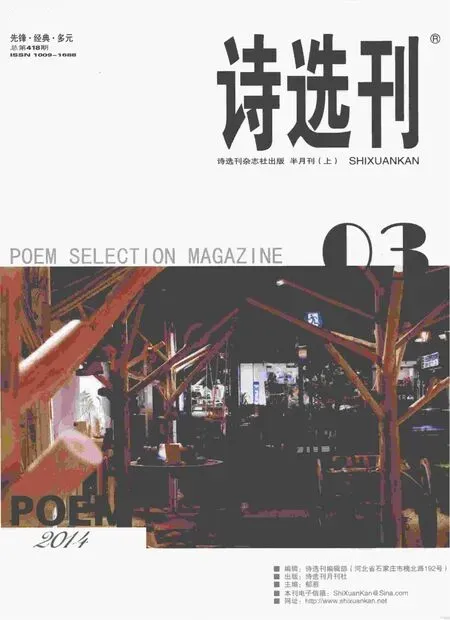阿华的诗
阿华

生活帖
甲地歌台舞榭,乙地癫狂销魂
那些年,在青江县
我经常过这种没有规律的生活
但我早就厌倦了人声鼎沸,摩肩擦踵
相比于庞杂的生活本身,我更喜欢
淬火的人生
于是,有人让我学陶渊明
抚孤松而盘桓,也有人建议我
去金刚经里,寻求智慧
在尘世的光阴里,慢慢修炼
打磨,上漆,抛光
然后就成了一块稀有的金属
但活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不盲目轻信,也不急于表白
只想对习以为常的事物,保持个人的警惕
浅水流沙的时代,人心都是贪婪的
哪里有甜蜜的东西,除了养蜂人和他的蜜蜂
哪里有纯洁的故土。除了沉默的大堤和遍地的芦苇
坎布拉
在坎布拉,我想看到你所说的飞鹰
但没有
在坎布拉,我想看到你所说的杜鹃
也没有
季节和花期都已经错过了
我只能把你写就的诗行,提炼成
抒情的一天
但风还在那里,它和你说得一样
它总是很有力度,把行走的人
吹得歪了
在坎布拉,我还听到了寺院里的音乐
虚无又缥缈
你说:“梵音好听,是因为它像风一样
轻轻把灵魂唤醒,再轻轻拂去尘埃”
——从坎布拉回来,我仿佛又重活了一遍
寺院里的黄昏
寺院里的和尚,都在诵经
他们笃笃笃敲木鱼,一点儿也不拖泥带水
他们诵经的时候,什么也不想?
寺院外的流水,曲折向东
它们或清浅,或浑浊,都因季节而疏密有致
它们流淌的时候,也带着一颗欢腾的心?
吹过悬铃木的风啊,也吹过寺院里的
石兽和碑文,它们越来越粗糙破败
是不是也越来越少爱恨悲喜?
我从一个门厅进入另一个门厅
什么也没说,也许
那个回头的喇嘛,可以看到我的伤口?
时光曲
我走在岸边,我的心散落在江水里
我去上游,只看到连绵的山体
和繁华的落日
春天泄露的天书,一次次被草海淹没
我去下游,迭荡起伏的
不是蓬勃的灌木
枯树上长木耳,琥珀里藏着泪
我且忆且悲,是个颓废的病人
在藤萝树下抄写经书,在草地上沾花惹尘
时光若是拖拖踏踏,摇摇晃晃
我就与它一起,倾斜、起伏、汹涌、动荡
时光若是一团,一卷,像茧子里抽出丝
我就与它一起,发光或照亮
我从来不指望,那些盟誓,泪水,轻怜密爱
还能沿着芦苇的芽孢,重新走回来
春风夜
春风沉醉的晚上,少年路
凉薄寡淡,一滩血正好
漫过了,一条狗的年少轻狂
路边的司机说:我没有倒行
也没有逆驶,它是从梧桐的阴影下
突然窜了过来,它无辜的眼神
带着我不曾见过的悲伤和绝望
没有人向一条狗,索取证供
没有人问一条狗,真实的疼痛
把狗从河南老家带来的赵四
三个月前又去了外省
它是听到了马路对面的乡音
才一路狂奔的
一条狗,在异乡
无法说出生活之痛,相思之苦
春风沉醉的晚上,少年路恢复了宁静
有蔷薇在墙头上开着,零星的几朵
在众多的绿叶中得孤独
香蒲记
我一度爱上了王家皂的黄昏
黄昏中浅滩上的香蒲
我喜欢它,左右起伏
慢慢涌荡,风吹动时
发出的响亮的“嘶啦”声
沿岸居民却不这么看:
“香蒲占据了大片水域
阻断交通,妨碍捕鱼
还引来鸟儿糟蹋庄稼,更严重的是
水生疾病不断增多,不仅有疟疾
还有血吸虫病。”
关于香蒲,我知道的不多
只知它,嫩芽蔬食,花粉入药
叶绿穗奇,可以用来点缀园林和水池
却不知,它饱满的激情
不是福祉,竟是病根
……落日的光辉,像安慰的言辞
我的眼睛里,却满是
舞动的落叶和破碎的霞光
关于香蒲,我已无法言语
这一小段的青春,孤独的潜泳着
这小范围的悲观,让人难以处置
云南开远,碑格乡
云南开远,碑格乡
捕鸟人的身影近在咫尺,但途径
碑格乡地界的鸟儿,却一无所知
因为雾大,能见度低,所有的鸟儿
都迷失了方向,高大的杉树无法参照
低矮的野茶树也没法对比
“从形体到枝叶,它们大体上
都是相似的,寻找总是会令人疲惫”
远离碑格乡之后的鸟儿,全都带着沮
这古老乌道上的捕杀,触目惊心
但好运气非常稀少,逃离人类的捕捉
需要太多的勇气和智慧
在云南开远,碑格乡,大部份鸟儿
死于天罗地网,剩下的几只
也只能在黑暗中,怆惶地隐身
在看不到希望的地方,它们的焦虑
大于孤独本身
在看不到希望的地方,飞翔与降落
都是冒险的抒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