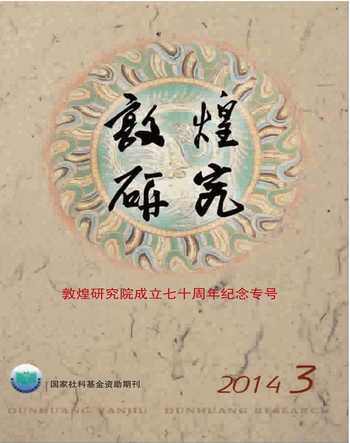莫高窟人的生活往事
内容摘要: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批的年轻的毕业生来到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扎根大漠。他们在常书鸿所长的带领下,艰辛而勤奋地默默工作,临摹了大量洞窟壁画,其中不乏精品。1959年以后,粮食供应出现了困难,莫高窟人自力更生,在戈壁沙漠中种粮,寻找野生植物锁阳、草籽等充饥。1961年,莫高窟人有了几亩自己的淤沙地,在此办农场种地。孔(巩)金和吴兴善功不可没,他俩种地,植树,养羊,保证了莫高窟工作人员的物质生活供应。
关键词:莫高窟人;临摹工作;济食与农事;20世纪五六十年代
中图分类号:K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06(2014)03-0019-05
Past Life of the People at the Mogao Grottoes
GUAN Youhui
(Dunhuang Academy, Lanzhou, Gansu 730030)
Abstract: in 1950s and 60s, a group of young graduates came to work at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n Dunhuang Cultural Relics at the Mogao Grottoes and they took root in the Gobi desert. Led by Director Chang Shuhong, they worked hard and diligently, copying many cave murals, including some masterpieces. Since 1959, the food supplies had been insufficient. People at the Mogao Grottoes began to become self-sufficient. They grew grains in the Gobi desert and foraged for wild plants to avoid hunger. They owned several mu of land, transforming this land into a farm in 1961. Kong Jin and Wu Xingshan greatly contributed to managing this farm. They cultivated the land, planted trees, and raised sheep, ensuring food and material supplies at the Mogao Grottoes.
一净土
1953年9月2日,我们从西安西北艺术学院美术系毕业后,来到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同来的有孙纪元、冯仲年、杨同乐。那时,交通不便,途经兰州、酒泉,买票,换乘候车,七天才到敦煌。又坐了五小时的马车,到莫高窟已是傍晚掌灯时间。段文杰诸先生在等候我们,会议室桌台上摆了许多梨子、西瓜。
莫高窟的人很少。文物研究所有二十几人,还有为保护莫高窟骑兵团派驻的一个班。上寺两个喇嘛、一个巫婆。活动范围集中在莫高窟南区三百多米长的绿洲中。石窟大半还没有安装窟门,看上去像一个个的黑洞布满在窟壁上。窟前林带有杨槐榆柳,还有些沙枣树,竖直横斜形成一道屏障护卫着石窟。窟前地面是鸣沙山吹来的黄沙,走在上面软绵绵的。林带以东是空旷的耕地。耕地自南向北,由高渐低,形成浅浅的梯田。耕地埂边有弯曲的水渠,流水清澈透底,高低落差处可以听到汩汩的流水声。渠埂边长满马兰和多种不知名的野草,散发着清微的苦涩味。耕地中有一块瓜地,刚来的那天晚上欢迎我们桌台上的西瓜就是从这里摘的。还有一片菜地,有番瓜、茄子、辣椒等。两片向日葵地,葵花并不高大,跟现在的油葵花差不多,可以看出有些是人工点播的,有些是自生的。上寺以南的耕地是寺产,上寺喇嘛的自食地,他们有牛、犁、车、石磨,还养着鸡、羊,跟乡下农户无异。上中下三寺各有一处果园,冬果梨、香水梨、长把梨、稣木梨、吊蛋子等各种梨子挂满枝头,压得树枝快要折断了。莫高窟一派自然山乡景象,全不是现在看到的混凝土堆砌的人工造景。
文物研究所设在中寺,前院是办公室,后院是常书鸿所长的住宅。前院正屋是美术组,约二十五六平方米,是段文杰、霍熙亮、史苇湘、李其琼、李承先、欧阳琳、李复先生和我们新来的四个人的办公室。北厢东间约十七八平方米,是文书、财会、后勤事务、行政组的办公室。西间约十平方米,是石窟保护组孙儒僩先生的办公室。与之相对的南厢东间是会议室,西间是常所长的办公室。1954年,李贞伯、万庚育也来到了莫高窟,人员增多了,办公室就显小了。对中寺大门做了翻修,门北侧是保护组新的办公室和雕塑室,门南侧是大会议室,会议桌是一台乒乓球台案,大家就称文娱室,从不说会议室。中寺院北侧是职工宿舍,整整齐齐排列着十间坐北向南的小土房,每间八九平方米,一个土炕,一个土台桌,一个壁橱,与石窟中的僧房窟相似。职工多单身,没有什么家当,一床被褥、两身换洗的衣服、几本书、几卷画纸。住进去并不觉得狭小,出门不上锁,东西落在什么地方,几个月后还在那里,真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文物研究所人员少,设施简陋,但是生活工作一切井然有序。每天清晨,只要听到院中几声轻轻的咳嗽声,准是常所长起床出屋了,他是莫高窟起床最早的人。不一会,中寺老榆树顶端的钟声当当响起,钟声清脆嘹亮,余音萦绕,像唱歌一样,很好听。这是一口铜质钟,钟体不大,造型很美,不知现在还在不。紧接着,大家都来到中寺办公室屋檐下站好,手摇留声机唱片发出: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广播体操开始了。常所长只要在莫高窟,每天早晨必有广播操,几十年不间断。做完体操,有一小时学习。当时没有电灯,太阳还未升高,洞窟内光线暗无法工作,即安排一小时学习。收音机信号不好,听不到新闻,阅读报纸杂志就显得非常重要。业务人员都订了刊物,有《光明日报》、《文艺报》、《新观察》、《文物参考资料》、《美术》等。没有党组织,但人手都有一本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认真学习研究,追求进步。学习之后开始办公。美术组人员各提一只开水瓶走向自己临摹壁画的洞窟,一个人在洞窟临画非常安静。除了偶尔可以听到窟外树叶经风吹动轻轻的沙沙声,就只有画笔运行时发出的气息与心音。临画思想高度集中时,有时会忘掉自己,据说禅僧入定时就是这样。距离中寺较远的洞窟是听不到钟声的。多数人没有手表,莫高窟是东西向的,无法看日影计时,大家也就养成了凭感觉定时作息的习惯,上下班时间相差不了十分钟。当今高科技时代,一部手机无所不知,有时却忘了时间。星期天,洗衣服的人聚集在蓄水池旁边洗边聊,一番热闹。打扑克的有牌友,也有人爱狩猎。莫高窟人少,活动范围小,狼也就大胆起来,一日白天竟闯入上寺院中。一天晚上我在中寺食堂后边也遇见了一只狐狸,两只眼睛亮晶晶。不期而遇,真有点怕。黄羊也常来下寺北边寻水。爱运动的人就去打黄羊。一次,工人老窦竟一弹射中两只黄羊,真神了。我爱串洞窟,去寻找自己喜欢的东西,虽是菩萨像,有的却是生人样,或是曾经见过的,画下来挂在墙上,看着想着,也有乐趣。星期天也要改善生活,炖鸡烧肉,会做菜的人有时也要露一手。一次段先生做红烧肉,忘了看锅,待想起时,锅底已经被烧穿,成了多年的笑料。所里四川人多,餐厅放着一个泡菜缸,李其琼先生就成了志愿者,常去搅搅拌拌,为大家服务。食堂实行同桌共餐,不论吃多吃少,月底结算,按人均摊,其乐融融。平时很少有人进城,日常生活用品派专人采购,届时院墙黑板上有公告“某某某骑毛驴进城”,“某某某赶马车进城”。要买东西的人列出清单,小到火柴香烟、牙刷牙膏、信封邮票,大到面米油肉,付上现金交给经办人。从莫高窟到敦煌城马车往返百里,毛驴走捷径80里,赶早起身,晚上10时才能回来。经办人不厌烦,精心办理。没有听见过因钱物差错争执的事。逢年过节也有庆祝活动,话剧、嵋户、清唱、舞蹈、快板等表演,演员多于观众,自娱自乐,亦然热闹。
壁画临摹是文物研究所的主要业务工作。临摹计划和主题经常所长审定后,段先生即带领美术组全体人员到洞窟参观选取画面,议论临摹之易难,评估所需之时间。经过几天的参选、讨论,最后段先生综合大家的意见,确定临摹哪些,再分配到各人名下。民主自由,心情舒畅。根据自己的临摹工作进度,每到一定阶段,便会主动去请段先生带全组人员来检查,征求修正意见。临摹完成时还需评定等级。段文杰临莫高窟第130窟《都督夫人礼佛图》,史苇湘临第445窟《剃度图》,李其琼临第329窟《乘象入胎与逾城出家图》以及在他们带领下集体临摹的第285窟、榆林窟第25窟整窟模型临摹本等一大批以神韵感人的临本,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如以人数按时间计算,这时临摹壁画的数量也是最多的时期。莫高窟人就是这样宁静平淡地工作与生活着,直到1957年。
二济食与农事
1959年下半年,粮食供应出现了困难。1960年上级号召各单位拓荒种粮。敦煌县文化馆、电影院、新华书店、中学和敦煌文物研究所文化系统被分在南湖国营林坊附近的沙滩上,由各单位派人参加劳动。文物研究所先派去了欧阳琳、傅积庆两人,大约半个月后,又抽调我们年轻力壮的十多人,带上行李、帐篷、工具、锅灶去参加劳动。当车将要到达时陷入了沙窝,车不能动了,我们下车取出搭帐篷用的木椽,垫在车轮底下,连推带抬,使车冲出了沙窝。莫高窟人经过“大跃进”的磨炼,已经适应了戈壁沙漠环境的生活,也有了处理车陷泥潭沙坑的经验。这里本来就没有路,四周全是黄沙。车也是一辆破旧快要废弃的卡车,是“大炼钢铁”时七里镇石油公司送给文物研究所拉矿石用的。车虽然破旧了,如果只是小毛病,司机捣鼓捣鼓,一小时还能跑四五十公里。车到工地,在一条溪流旁安锅扎营。溪水清澈甘美,流量比莫高窟溪流大得多。我们的任务是挖掘一条引水渠,把水引往开拓地,各单位人多,合力奋战,四五天就完成了任务。可是再大再美的水也灌不满无底洞的沙地,最后只好不了了之。当时吃供应粮的人似乎还没有察觉到粮食问题的严重性。到了下半年,口粮供应标准一减再减,最后减到每人每月19斤,清油每人每月4两(合今日2.5两,即125克)。在没肉缺油少菜的情况下,一个人每月19斤粮已难维持身体所需。莫高窟人每年此时都能享用的百十斤美味的梨子也吃光了,大家感到了饥饿,身体不支,业务工作基本停了下来,一些人出现了浮肿。史苇湘先生已经支撑不住了,批准回四川老家异地就食。不能坐等挨饿,得去想办法。一天,不知谁听谁说,锁阳可以吃,莫高窟附近的大泉就有。大家顿时兴奋起来,打起行李,拉着帐篷、锅灶,乘车来到大泉,这里刚下过一次小雪,还留有残雪痕迹。锁阳是一种中药材,我只听说过,没有见过,拿着铁锨,跟着大家去寻找。知道的人说,下过雪后容易找,锁阳性热,雪地如见无雪的圆坑坑,此处可能就有锁阳。寻找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找到了锁阳,有的已经出土一两寸高,圆柱体,紫红色,挖下去最长的有二尺多,直径有一寸多,肉细白脆,味苦涩。第一天共挖了二三十根,洗去沙土,刮皮切成丝,清水浸泡除去苦味,拌上面粉蒸熟即食,但仍旧苦涩。第二天收获就没那么多了,第三天更难寻找到了。冬天在戈壁滩帐篷里席地住卧,寒冷难耐,坚持到第四天又回到莫高窟。过了几天,又不知谁又听谁说,戈壁滩有一种叫沙米的草籽可以吃,南湖有一户采集了不少,很好吃,而且榆林窟也有。这又是一大喜讯。大家又带上行李、锅灶,还是坐着那辆破旧大卡车又向榆林窟奔去。路过安西十工农场时,经交涉,买到二十多斤干萝卜叶子。这种通常当作饲草或垃圾的东西,此刻成了难得的好食物。榆林窟就郭道一人,他从1953年10月被敦煌文物研究所请回榆林窟当看守员,已经坚守了七年。见到莫高窟人来了,他非常高兴,也精神起来。莫高窟人对榆林窟和莫高窟同样亲切。甘肃省文化局听说这里有沙米草籽可食,也派了两女一男三个年轻人来采集。大家住进今日作为库房的大洞里,洞内两边各有一个大土炕,是专供来此进香拜佛的善男信女居住的地方,烟熏火燎,已有百千年的历史。燃起干柴,人多火旺,顿时暖意浓浓,也忘了饥饿。次日开始采集草籽,每人一把铁锨,一根木棍,再带一条床单上了戈壁滩。沙米草确实不少,也是刚下过雪,有些草头还被雪盖着,抛去雪,用锨铲下,放在床单上用木棍捶打,捡去干柴草叶,一人一天能采十多斤。草籽再经过筛洗去沙土、浸泡、煮熟,掺入汤面条,再加那干萝卜叶子,连续饱食了几天。但草籽不易消化,难排泄,不能多吃。
想方设法,几经折腾,总算熬过了最困难的1960年冬天。1961年开春,敦煌县各单位都有了自己的农场,敦煌可开垦的荒地不少,文物研究所去要几亩地是不会成问题的,但最后把目光落在了莫高窟南端的水沟。水沟即莫高窟前溪水流域的谷沟,沟内有多处水泉,还有一些零散的淤积沙地。逆溪水而上,入山约一公里至小拉牌(拉牌,据说是少数民族语,即崖壁凹进处,可挡风避雨),水分为两流:一流来自南边水沟,沟内一片沼泽,长满芦苇,水苦涩,不可食;一流来自东边大谷沟,流量较大,可食用。逆流水上行约两公里到大拉牌,这里有淤积沙地三四亩,是水沟最大的一块淤沙地。1958年公社化之前经营这块土地的是一位俞(音)姓的农民,之后由公社生产队经营,1960年困难时期放弃了。从此再上行约一公里,山脚下一片沼泽,多处泉水涌出,是今莫高窟前溪流的主要源泉。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曾先后两次到此掏泉。再前行约一公里许出山,折向南行约两公里到大泉。大泉古称宕泉,泉水较大,流入山谷与诸泉相接,现在泉水已经很小,不出百米即干涸了。此处有淤沙地五六亩,两间小土房,据说早年曾有人在此种植罂粟居住。较大的一间土房是1950年敦煌县邮电局为敦煌县城—莫高窟—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党城湾)邮路修盖的邮递员途中住宿房。山口向东南约一公里有一小泉名叫条湖子,泉水甚小,有沙地两亩多。这些水泉是莫高窟的生命之泉。为保护这些水源,莫高窟曾设卡阻止农民入山砍伐红柳,我也曾被派值勤通夜守护,但最终都是不了了之。考虑到莫高窟水源日后长期保护,利用水沟淤沙地种植作物即能解决眼前食物困难一时之需,也有利于水源保护。敦煌文物研究所即向甘肃省文化局(厅)呈报,经批准,与敦煌县政府协商,以购买的办法,将水沟内、大泉、条湖子所有大小树木如数折价,以及淤沙地开垦所用工费,一并买来成为莫高窟保护区的一部分,由文物研究所执行管理。就这样,莫高窟人有了水沟几块淤沙地,加上莫高窟前的几亩,总共十几亩,算是有了自己的农场。
办农场种地,有两个人我们不应忘记——孔(巩)金和吴兴善同志。孔金是敦煌人,家贫,长工出身,后被抓兵当了警察。1949年10月敦煌和平解放,警察改编为公安队。1954年秋,驻莫高窟骑兵班撤走,由县公安队派孔金带一个班接防。1956年夏莫高窟公安队班撤防时,孔金和两名队员转调到文物研究所当工人。孔金不识字,孔、巩读音不分,大家以为他姓孔,呼他“孔班长”,这一叫就几十年。老孔言语不多,善良,为人诚实。
先说1959年那一件事,国庆十周年,敦煌壁画摹本要在北京展出,榆林窟第25窟整窟模型临摹还留些“尾巴”,需要补充,所里派史苇湘、何治赵和我,还有老孔去完成这一工作。史先生头上有“帽子”,我正在受处分期间,何治赵是新分来的一个年轻人。老孔是党员,在当时形势下,他不轻视“有问题”的人,真诚地协助我们临摹壁画工作,做饭,干杂务。粮食供应开始紧张,我们三人月供各28斤,他是体力劳动者,月供30斤,清油四人月供1斤。一日三餐,每餐每人只有3.3两面粉,每天四人清油17克,缺油少菜,这饭怎么做呢?他埋头不语,有空闲时间就去找野菜,请郭道帮忙去拔沙葱,早餐稍清一点,午餐略稠一些,让大家吃好。他总是先放下碗筷,不多吃一口。这事过去多年了,我总是不能忘记。当下要办农场种地,他自然是行家,他成为组织者、带头人,也是最主要的劳动力。耕、播、收、打均需他亲力去做。粮荒当前,上级号召“广种博收”。购回了水沟的淤沙地,但春播时节已过,凭他的农事经验,种植了大量洋芋、红萝卜、糖萝卜,获得了大丰收。糖萝卜最大的有十斤重,一时吃不完的煮熟晾干蓄存起来,红萝卜、洋芋可蒸烤吃,各家都散发着萝卜香味。“文化大革命”中,莫高窟也有“派”,无论哪一派,无论多么艰难,都不离开莫高窟,都死守在莫高窟,正常业务搞不成了,就去种地。老孔不以“派”划线,只看身体强弱、是否会干农活、责任心如何,有分别地使人派活。开春,活多为活杂,疏通渠道,平田整地,播种。夏季,作物管理,灌水,除草,收割。这里有麦田、菜地。有的活需集体突击,有的活只要少数几个人干。他的话不多,把大家的活安排好后,就埋头去做活。做活总是先别人早到工地,下班最后一人离开。播种是他,收获打场是他,菜地经营管理还是他,菜地活需细心,太阳未出传授花粉、掐尖打枝,太阳高升,又去除草灭虫,从不释闲。在他的带动下,那几年莫高窟人的农事搞得有声有色,职工膳食得到很好的改善。
再说,吴兴善。老吴是武威人,家贫,从小就出外打工谋生,后辗转到敦煌信了道教。他不识字,也不会念经,实际是道教会中的跑差苦力。1953年到莫高窟文物研究所当了园林工人。1956年经他师父同意落发还俗成了家。在多年的相处中,我觉得他虽不会念经,但有信仰,且牢固。莫高窟被他看作仙山灵境,为莫高窟植树育林是做功德,行善事。莫高窟前河床对岸1954年之前没有草木(据遗迹,古代曾经有植树),老吴来了之后,开始向对岸扩展绿化。对岸地势高,为把水引上对岸,筑起了一道三米高的拦水坝。没有黏土,更没有混凝土,只能用沙石、树枝堆垒叠压。但不能防渗漏,经常溃坝。沙地植树灌水,水小,边灌边渗,永灌不满;水大,沙埂会被冲垮。盛夏是最需用水的时候,水因流途大量蒸发,中午12时即断流,到晚上12时才能流下来。为营造这片林地,灌水时,老吴拿着锨围着地埂四边来回巡视加固,晚上,提着一盏马灯,披着一件老羊皮袄睡在地埂边。1958年又种植了苹果、核桃、葡萄和柏树苗。那时没有塑料薄膜,种出的柏树,冬天还得埋入土中,春天再挖出来,经三年才长成越冬树苗。中寺办公室摆放着多株一米多高的盆栽石榴和两米多高的夹竹桃,还有无花果,都由老吴亲手栽培。
他还是老孔的农活帮手,帮耕地,帮打场。种地需要肥料,那几年,养羊积肥又成了老吴的主业。有一段时间,我住大泉为麦田灌水,他在放羊,他视羊如人,精心看护。我俩同锅吃饭,每顿都是没油少菜的稀汤面。有羊下了羊崽,我要他去挤羊奶,面条加入羊奶非常香。挤了两次,第三次,他再也不去了。事后我发现他是为羊羔留有足够的奶。一天,突降大雨,在邻近放牧的公社农业生产队的羊死了七八只,他的羊无一损伤。我们的小土屋到处漏雨,只好戴上草帽,卷起被褥,坐在上面避雨。一小时后,雨过天晴,他的羊又出圈了。一年冬天,所里派我跟老吴住条湖子放羊。一个晚上,我们已经上炕躺下,但还未入睡,老吴两只眼睛直盯着屋顶,过了一阵儿,忽然说,丢了一只羊,这使我感到很吃惊。老吴看羊是很负责的,我也是个小心的人,羊群二百一十几只,出圈入圈都点数,怎么会丢?空旷戈壁滩,两人四只眼,目及数百米,有脱群的羊也会即时发现,不可能丢羊啊。可老吴说的很具体,是一只未产过羔崽的母羊,长得什么样子都详细说了,这使我不能不相信是丢了羊,而丢掉的是哪一只我还是不知道。过了几天,一天早晨,老吴说他梦见了丢失的羊还在,还活着,要到水沟去寻找,我们把羊群赶进水沟放牧,当羊群快要到大拉牌时,老吴喊住了我,指着远处的山头说“看,羊!”山头上一只羊定定地站着,凝视着羊群,似有点惊恐。老吴让我蹲下,不要走动,以防惊吓了羊。一会儿,山上的羊左右跳动起来,很像久失的孩子看到了母亲,非常激动。又一会,羊慢慢地从山顶下来进入了羊群。这时,老吴也笑了。从此,我也开始注意观察每只羊,看多了,就发现羊同人一样是有特征的,有的羊个性还特别突出。两个多月过去了,按计划,羊群要返回莫高窟。12月的天气很冷,过了大拉牌溪流渐渐成了宽大的冰河。在冰薄处,不注意就会掉进冰冷的深水中。冬季是羊产羔时,老吴挎着一只红柳筐,巡视着将要临产的羊,将产下的羊羔装入筐内。一路上共产了三只,可谓丰收。天黑到莫高窟南端,老孔等不着,有点着急,赶来接应,羊群安全入了圈。我也算是完成了任务,将要离开时,见老孔叫住了老吴,旁边还有两人,说:“明天是(1970年)元旦,今晚一定要把肉分到大家手上。”不知他们又辛苦到晚上几点钟。
这些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老吴2000年过世,享年80岁。老孔去年也走了,享年90岁。
收稿日期:2013-03-25
作者简介:关友惠(1932—),男,山西省临猗县人,敦煌研究院副研究员,美术研究所原所长。
Keywords: People at the Mogao Grottoes; Copying; Food supplies and farm work; 1950s-60s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