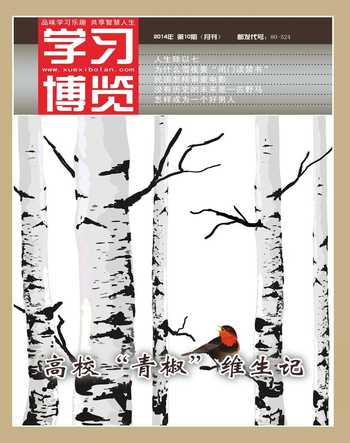吸毒,以艺术之名
醉丐
艺术家大抵都对灵感有着不懈追求,即便这是病态的追求。
宁财神因为吸毒而被拘留,他的解释是:“每次大密度写作的时候,我就会吸毒。”以艺术之名,听起来荒谬,然而,纵观艺术史就可以发现,一切永远不是那么非黑即白。
由鸦片幻觉形成的城市和庙宇,曾被昆西形容为富丽堂皇的巴比伦;超现实派画家达利曾宣称能以一种“临界偏执狂状态”的方法,在自己的身上诱发幻觉。同样对于不少创作者来说,艺术需要跳出日常状态之外的极限体验,而毒品带来的刺激和麻痹,无疑为众多艺术家敞开了便利之门。
所以,艺术早已放下了道德审判的负担,毒与尽善尽美的崇高理想并不矛盾。那些狂热的情绪,如痴如醉、放浪形骸的精神状态,某种程度上催生了艺术史上不少巨擘人物,无论是达利、毕加索,还是披头士,都完成了在“非理性状态”下的伟大创作。用福柯的话来说,“疯癫在各个方面都使人着迷”。
爱、和平、迷幻药
“我肯定有过一千次迷幻经验。”
“是真正有一千次还是——还是好几百次?”
“不,还要更多。我习惯从早吃到晚,但在录音室里绝对不用。我想乔治也用得很凶,我们两个也许是最疯的,我想保罗比起我跟乔治要稳定许多。”——约翰·列侬《迷幻经验》。
披头士对于迷幻药的使用并不讳言,其著名歌曲《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明显是在向LSD“致敬”。
当瑞士化学家艾伯特·霍夫曼在一次实验中无意合成LSD的时候,他并没想到这将成为艺术家的灵感之泉,或者预测到几十年后“毒品文化”造成的轰动。1943年,霍夫曼决定做一次自我测试,他在事后觉得LSD的迷幻经验与一般药物中毒现象有极大的不同,特别是在视觉所产生的效果上,他在备忘录中记载:“我充满恐惧,觉得自己要发疯了,我好像到了一个异样的世界,一个不同的时代……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扭曲,就像站在哈哈镜中一样。”
而LSD在艺术界大行其道,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在西方社会蔓延的嬉皮士运动脱不了关系。
嬉皮士是美国规训社会的逃逸分子,在那个复杂而迷惘的时代,年轻人在生活的百无聊赖和社会责任感的日益增强中渐渐迷失了自己,开始过着反主流、波希米亚式的社区生活。嬉皮士始终在批评政府对公民的权益的限制、反抗传统道德的狭窄教义,而正因如此,他们对毒品也采取了与主流社会截然不同的态度:他们并不认为毒品将导致自甘堕落的消极生活,恰恰相反——“LSD是困顿世俗的耶稣”。
于是,LSD被视为一种类似宗教团体告解时扩展心灵的药物;嬉皮士提倡通过使用毒品、东方宗教,甚至灵修来“提升灵魂”,打开自我的内心之门。如此,LSD不再仅是艺術家的万灵丹,还被视为进入天启的钥匙。正如霍夫曼在一次访谈时说:“我们无法再采用过去‘神居于真实之外的宗教想象,而必须从内在去追寻,自觉每个人都是‘神的一部分,单独冥想,或以LSD来冥想,都能启发这种新的宗教情操。”
摇滚音乐则迅速地把嬉皮思想传递开来,在演出台前,一切的混乱与疯狂在嬉皮的质朴情怀下显得高尚起来,爱、和平、性开放、迷幻药、反战呼声和几十万嬉皮共同出现。在欧洲,革命思潮和喧嚣后的虚无同样撞击着这个脆弱的年代,从伦敦到布拉格,欧洲街头很快就成了迷幻药与摇滚乐蔓延的沃土。
毒品=灵感?
毒品是否真的有利于艺术创作?20世纪60年代,心理学研究人员对迷幻药和创造性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大量研究,然而,研究人员得出的观点并不一致,无法对迷幻药和创意之间的关系做出强有力的结论。
加州大学的奥斯卡·简尼格在一次研究中,邀请了约100名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并让他们画两幅霍皮印第安人的克奇纳神像,在服用迷幻药之前画一幅,在服用迷幻药出现幻觉期间画一幅。之后,一位艺术史学家对他们各自画的两幅画进行了仔细检查,发现受迷幻药影响的画作“更抽象、具有象征意义、更明快、更能表现强烈情感、更具有美学冒险性,而且是非具象的。他们还往往充分利用了油画布上的可用空间”。
但是,在这之后,大部分对非艺术人士进行的测试都让提倡使用迷幻药的人感到失望。1967年的两项研究通过一系列游戏来衡量创造性,结果表明,迷幻药并没有对创作能力带来明显的变化或改进,尽管那些测试对象反映自己在使用迷幻药期间更有创意。
毋宁说,伟大的艺术家并不是盲目地追求迷幻状态下的创作灵感,而是希望从亢奋状态中释放出内心已拥有的东西。如列侬说:“它只不过是另外一面镜子——它并不是一种奇迹。你听到了音乐,但它并没有写出那些音乐……是‘我写了那些音乐,在我身处的环境里,不管用的是迷幻药还是白开水。”
(摘自《财经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