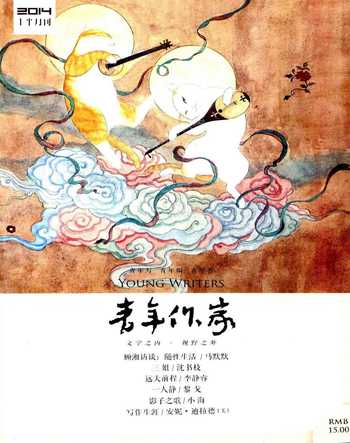人静
黎戈
【云的名字】
卢克·霍华德是一个职业药剂师,业余气象学家,虔诚的教徒,世界上第一个给云彩用拉丁语命名的人。至今气象学界仍然在沿袭他的分类法。每到周日,霍华德都会去英国汉普斯泰德原野。雨天,他在橡树下踱步,晴天,他就在青草丛生的草坪躺下,仰面观察天空,思考着和云彩有关的事。他把像猫的爪痕或是马的鬃毛一样的云命名为卷云,把密实的堆积在天边的云彩称为积云,把那些连成片的大片不定形的薄云称作层云。每次在草坪上看完云,卢克-霍华德就起身回家,回到亲人、家庭和喧闹的伦敦市井生活中去,并且在心中感谢上帝让他看见如此之美的云,及赐予他给云彩命名的荣幸。
莎拉·梅特兰在《我自静默向纷华》中写道:“云有很漂亮的名字,积雨云、堡状积云、卷云、荚状云、马尾云、雷雨云玷、鱼鳞天,它们天天来临,却从不重样,没有完全相同的云彩。它们是我们身边一种静默的力量,一路经过向我们宣告静默自有其深长的意味”,当她名目琳琅地列出这张云朵清单时,是否想到,这世界上最早给这些白色絮状物命名的那个男人,他唯一并且发挥到极致的天赋,恰是沉默。当你只想安静地与自己相处,云是一个稀薄却恰恰好的介质和陪伴者。
还有,当莱斯利在《笔记大自然》里说自己无论驾车、遛狗都会观察云彩时,当她细细地画下这些云的时候,当她告诉我们“松软的卷积云带来晴日,马尾云是雷雨的前奏,乳状云提醒你该回家”时,她是否想到:两百年前,也有个男人,在他的生命里,只有神和云朵,唯一能让他放下云彩的事,就是去战场和需要福音的地方传道。他行进在传教的路上,远远看到一片从未见过的云朵,突然他明白了:那是被尸体的恶臭吸引来的成群的苍蝇和鸟。
有次这个男人重病,邻居家的女孩过来给他读《圣经》,他们自此相爱,但被家长阻止交往,他就给她授课,并在之后十二年的两地分居里通信,去看云。他们毕竟还在一片天空下。真是美好,是小说家的杜撰么?在维基百科上查到的卢克·霍华德资料只有以下这些骨感的信息: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十九世纪英国制药学家,业余气象学家,创办了知名制药企业。生于1772年11月28日。完了,没有了。哦对了,还有人说:此人是试管婴儿之父罗伯特·爱德华兹的先祖。这个……云,试管婴儿,都是某种生命流动又物质轮回的神迹,冥冥中的契合?
【珍宝人生】
少女时代,很喜欢亦舒,收了她很多的书,师太语录自是朗朗上口。她书里的女人,自强自立,睥睨男性,洞察世情,这种降温醒脑效果,对混沌的初心很有助益,又有物质气息,有助于培养高雅之品位。
她当然是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对我的性格有过某种程度的塑形。
但现在觉得西西更投契,我喜欢这个跑到慕尼黑看玩具熊展,花一本书的稿费去买只手工熊的老太太,她去英国,也是坐地铁到市区看看鸽子,买本最新译本在公园里晒着太阳看……去动物园看大象、骆驼和狒狒,在乐器店买个名字奇怪的乐器,回家去查音乐辞典研究。到了西安碑林,一个人静静地把石头上的《诗经》拓下来,带回去。
我想,这种随心所欲、很自得的感觉,才是真正的自我,它有松弛感,无对峙欲,不是角铢必较的斗智斗勇,不是心机丛生的人际搏杀。它的格局大得多,更“多情”,这个情,是对天地万物之情,远不限于男女爱恋的狭隘天地。
我是个多疑的天蝎座,我仔细看了,她的《缝熊志》《时间的话题》《猿猴志》,都是得癌症以后写的,里面没有戾气、晦暗、自弃、诉苦。那本让我欢笑不止的《我的乔治亚》也是,那本书最后从右手写到左手,因为手术的后遗症。
看过一张莱尔拍她的照片,附文是:“我是在桑给巴尔拍到的她,我猜想她也是游客,正在非洲独自旅行,她的朴素自然,让我想到一些经历世事仍保持优雅大方的女人,她们是散落在这茫然尘世的珍宝,我喜欢在路上偶尔一瞥遇见她们。”
【阿赫玛托娃:情感生活】
最近稍有闲,又重读了《阿赫玛托娃札记》,真心觉得,利季娅对阿赫玛托娃的感情,可能胜出她的任何一个男人:她不但爱阿赫玛托娃——少年时代就背熟她的每首诗,杂志发表时少了一行,她也能看出。而且,她的爱,在近距离地接近阿赫玛托娃之后,并没有被后者与声名完全不配的简陋生活所影响,生出鄙意。这种饱含怜意、积极理解及对内在肌理的认可,才是高质量的爱。
之前对阿赫玛托娃无感,就是因为她老是被塑造成一个受难缪斯的形象,终究少了维度。而在利季娅深情又细致的笔端,这个善感脆薄、不拘小节、出言无忌、小毒针乱飞的阿赫玛托娃是多么真实可爱啊。阿赫玛托娃在冰结的冬夜非要利季娅去聆听陪伴,又避而不染心事,转而论析起文学来……她真是既脆弱又骄傲。
阿赫玛托娃不喜欢托尔斯泰,直言“他觉得安娜是个婊子,瞧他怎么写她的死……卑鄙地张开双腿,简直是侮辱尸体”,这个锋利!她谈到冈察洛夫,“他笔下是细密纯粹的生活流,而在屠格涅夫笔下从未有过,屠格涅夫是浮在表面的小品文”,评舍夫涅夫是“多么冷淡,对一首诗而言,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语调,而这诗里的语调是别人的。好像他自己从未谈过恋爱似的”——阿赫玛托娃的诗歌是室内和耳语风格的,而她的私谈,也有这个风味。
想想吧,在利季娅的笔下,没有那个时代强劲的背景音:大清洗,枪毙,流放,审查,监听,倒全是这些文学话题。阿赫玛托娃有时随口向她吟出一首诗,利季娅马上拼命地在心里背下,唯恐流失。她已经不忍心和这些句子分手了。有十年时间,阿赫玛托娃不能发表诗歌,有次利季娅无意问“你还在写诗?”随后就为自己的残酷和愚蠢感到羞愧。那个时代把阿赫玛托娃当泡菜坛子一样摔摔打打,而在利季娅眼中,她却永远是传世瓷器一样的金贵。
我一直在想“友情”这个事情,它和很多事一样,不仅是意向,也需要勤劳。就是:它得有连续不断的动作,永远清鲜的敏感度,对对方的好奇心,孜孜不倦的研究欲望。它不能又重又空又黏着,像冬天的一件湿雨衣。女陛很容易狭隘、短视,思考半径小,无法调离她的注意力到别人身上,而且精神维度单薄,如果利季娅念念不忘阿赫玛托娃送给她的一双袜子,那性质就不一样了。有的友爱是让人想哭的,就像射箭时不停地听到耳边响起“脱靶,脱靶,又脱了!”
布罗茨基曾经在《文明的孩子》写到诗人的爱:“任何一首诗,无论其主题如何——本身就是一个爱的举动,这与其说是作者对其主题的爱,不如说是语言对现实的爱。”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日子里,阿赫玛托娃也在执著地用语言爱着她的生活,而利季娅,则是这些爱最珍视的收集者。
她的感情多折,一生眼瞎,专遇烂人——以至于楚科夫斯基说她“我爱着一个人,可他不爱我,有一个人爱我,可我不爱他——这就是阿赫玛托娃的职业。在这个领域她无人匹敌,她是第一个发现不被人爱也是种诗意的美”。
而她的婚姻生活,都无法与她的才情相配。和第一任古米廖夫分手以后,她提到对方并不珍视她的价值,阿赫玛托娃说,“有六年时间我无法写作,他只是想要一个我月收入四百卢布,且能当主妇的妻子”,而阿赫玛托娃在生活中又极其低能:住在猪窝一样乱的房间里,地板也不拖,去探视儿子,连缝袋予也不会,做饭当然勿论。三年饥荒时,她没有勺子,没有叉子,连锅都得向邻居借——俄战爆发时,阿赫玛托娃和古米廖夫在车站遇到了波洛克,一想到波洛克也被遣送到前线,古米廖夫就震惊不己,嘟哝着说:“这不是油炸夜莺么?”我倒觉得阿赫玛托娃的一生,很配这个绝妙的比喻。
第二任丈夫希列伊科则直接把阿赫玛托娃的诗稿扔进了火炉,第三个……没有了,因为蒲宁长期未与前妻离婚,阿赫玛托娃和他只算同居关系。她长期住在墙壁斑驳、连床单都没有的破烂屋子里,椅子是断腿的,一只鞋跟是烂的(所以阿赫玛托娃走路总是跛着),动乱禁语时期,她只能靠翻译和研究为生。和儿子寄身于蒲宁的家,并且和他与前妻的孩子们生活在一起。她自己的儿子只能睡地板,多吃一块肉都得看脸色。
在她与诸多男性的纠缠怨怼之中,这个可能已经是爱的巅峰了;那就是和蒲宁恋爱时,当时阿赫玛托娃正处于名望的顶峰,尽管病体支离,瘦骨嶙峋,一举手一投足仍然像个女皇,但普宁猜测她的内心就像自己一样阴暗。他写道:“这样的空虚——不是指她的外部生活,而是她的内心,是这样的空虚,以至于时常吓着我”。他认为她应该得到一种简单朴素、开诚布公的爱,他时常惊讶于她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获得的欢乐“她经常为我们习焉不察的小事所惊喜。我很喜欢她为杯子、雪花和天空发出的惊叹”。
阿赫玛托娃和曼德尔斯塔姆,倒是有种惺惺之情。曼德尔斯塔姆时曾经写过阿赫玛托娃有个姿态体系,云云,是很妙的比喻。阿赫玛托娃谈到曼德尔斯塔姆时像说起可爱的孩童,“《时代的喧嚣》是以五岁孩子的明亮眼睛看出的世界。他是最出色的交谈者之一,他不聆听自己,也不回答自己,从不重复……他眷恋妻子到令人难以置信……有次他和妻子到火车站接我,他起早了,直打寒战,情绪很坏,我从车厢出来后,他说:‘您是以安娜卡列尼娜的速度来的?”曼德尔斯塔姆夫人回忆录里说,这两人喜欢斗嘴和打趣。
1946年1月3日,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从英国来到圣彼得堡,寻找苏联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他们在阿赫玛托娃的寓所谈了整整一夜,柏林称其为“悲剧女皇”。事后,柏林在回忆录中写道:“她有一个看得见庭院的小房间,空荡荡的,连窗帘都没有,只有一张小桌子,三四把椅子,一只木头箱,一个沙发,火炉上方是一张阿赫玛托娃的画像。”他们那次谈了一个通宵,房间里灯光幽暗,他们各居一隅,仿佛隔了一个世纪的老友重逢。阿赫玛托娃在诗里写道:“那一夜,没人敲我的门,只有镜子梦想着镜子,寂静守护着寂静,呵,一九四六年一月四日。”
——致阿赫玛托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