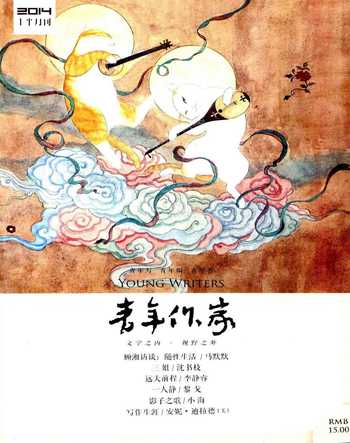写作生涯(节选)
安妮·迪拉德 李静滢(译)
致鲍伯
没有人把一天一天都当成神灵。
——爱默生
【第一章】
莫匆忙,莫停歇。
——歌德
写作伊始,你列出一行文字。这行文字就犹如矿工的鹤嘴锄、木雕艺人的凿子、外科医生的探针。你驾驭着它,由它探索出一条前行之路。没过多久,你就发现自己置身于新的领域。这会是一条绝路吗?还是说你已经发现了真正的写作主题?或许你明天就能知晓,或许要等到明年此时。
开拓道路时义无反顾,沿路前行时却心怀忐忑。道路通往何处,你就走向何方。在路的尽头,你看到山壁陡峭的封闭峡谷。你在此反复推敲,锤炼出报道,发出公告。
转瞬之间,写作就在你手中发生了转变,从最初的概念表达变成了认知世界的工具。新的领域吸引着你,原因就在于你对它的认识并不清晰。你全神贯注,谦逊审慎地铺排词语,从不同角度观察揣摩。此时,先前写出的东西看起来变得苍白草率。过程并不足道,你要抹去留下的踪迹;道路并非成品,我希望你的足迹不断拓展,我希望鸟儿能把碎屑啄走,希望你把它全部抛出,不再回顾。
这行文字犹如锤子。你用它敲打房子的墙,轻轻地在墙上四处叩击。经过多年的留意关注之后,你已知道该倾听什么。有的墙是承重墙,它们必须保留下来,否则整个建筑都将坍塌,拆除其他墙体则并无妨碍。你能听出两种墙体的差异。只可惜,必须拆除的往往是承重墙。别无他法。这是唯一的解决途径,即使令人惶恐,你也只能这样:用力敲击,闪身躲避。
你勇气十足地期望,这些文字如此精妙,正是作品所需抑或是世界所需。然而勇气和你的期望背道而驰。消耗殆尽的勇气建立在这一无情的现实上:你写下的文字恰好弱化了作品的力度。你必须毁掉作品从头再来。你可以保留某些句子,如同保留建房的砖瓦。然而,不论某些文字多么绝妙,多么煞费苦心才构思出来,倘若能保留某些段落,那就真称得上是奇迹了。你可以耗费一年时间为此忧心忡忡,也可以现在就动手拆建。(嘿,你是犹犹豫豫还是胆小如鼠?)
必须舍弃的不仅仅是写得最好的那一部分,而且是原本确定的最核心的写作内容,这令人奇怪。这些内容是最初的重点段落,是作品得以展开的基础,也是你自己鼓足勇气开始写作的起点。亨利·詹姆斯(HenryJames)深谙此情,也对此进行了极为贴切的表述。在《波音顿的珍藏品》(The spoilsof POynton)的序言中,詹姆斯用了引人发笑的两句话表达对作者的同情,这两个句子升华成一种呼告:“在哪部作品中,他不曾极端艰难地放弃本想保留的最佳内容?在哪部作品中,他不曾在做这可怕的事情之前问过自己:一切都为了‘将要走到最终那美好的理由,可是那最佳内容的最终结果又是什么呢?”
或者说,一位作者写了很多作品,他在每本书中都曾设想出若干亟须表达、鲜明生动的要点,其中大多数都不得不在作品成型的过程中舍弃。这恰如梭罗的喟叹:“年轻人把材料堆积到一起,来建造通往月球的桥梁或地球上的殿堂。而中年人最终只会用这些材料搭起个木棚放柴薪。”作者会重返这些材料,重返这些洋溢着热情的主题,如同重拾未完成的工作,因为这是他一生的成果。
作者抛掉的是作品的开头。
一幅画的成品遮掩了绘制过程的痕迹。绘画是从画布底层开始的纵向过程,每一笔的叠加都会逐层覆盖并取代先前画出的内容。写作则与此不同,是从左向右的过程。可以舍弃的章节总是先完成的,一部文学作品的成稿始自作品中间的某个地方,并逐渐向结尾过渡成型。先前写下的内容单调乏味,仍然留在原处,作品的开头以错误的方式面对读者。哪个读者都会在阅读开篇几页或几章时发现,文中富有想象力的跳跃落入空无,豪迈开始的主题中途搁置,此处奏响的音调随后杳无声息。读者会看到陷入僵局的叙述和偏离主题的描写,也会在深入阅读后明白,作品的背景原来并不正确。
若干错觉会削弱作者舍弃己写内容的决心。己写的章节经过翻来复去的阅读,就会让人觉得这些内容非常重要,不可或缺,如同熟稔在心的诗篇。它们完美地回应着自身熟悉的韵律。作者会保留这些内容。如果某些内容具有某种优点,比如说有内在的感染力,作者就会保留它们,哪怕它们缺乏与作品主旨相关并相协调的基本要点。有时作者会带着感恩之心保留早期写下的章节,因为每当他思忖或重读这些内容时,总会重温当年的感受,想到自己最初写下这些文字时内心是何等畅快,终于能够落笔写出开篇又是多么令人如释重负。毕竟,没有最初的起步就没有如今抵达的境界。那么读者想必也会需要这些作为奠基的字句吧?然而,并非如此。
有位渴望成功的摄影师,每年都会带着一大堆照片去拜访一位年长的资深摄影师,请他评判照片的优劣。每一次,这位长者都会认真察看照片,一丝不苟地把照片按好坏分成两部分。每一次,这位长者都会把一张风景照放进较差的那堆。终于有一天,他转身问年轻的摄影师,“每年你都拿来同样的风景照片,每年我都要把它放到不好的照片里。你为什么会这样喜欢这张照片呢?”年轻的摄影者回答说,“这是因为,我必须奋力爬上山才能拍出这张照片。”
在纽约,一位出租车司机给我唱过他写的歌。有些歌是我们一起唱的。他关掉了计时器,然后一边唱歌一边在市中心兜圈。有首很长的歌他唱了两次,只有那首歌让我感到乏味。我说,你已经唱过一遍了,我们唱别的吧。他说,“你不知道我用了多长时间才拼凑出这首歌。”
我们读到的书,有多少出自缺乏剪断脐带的勇气的作者之手?我们拆封的礼物,有多少来自于忘记取下价格标签的送礼人?让接受者了解你为之付出了多少,这难道是恰当贴切符合礼节吗?
你写下这行文字,在文字的末尾发现答案。这行文字就像一束光纤,又如电线般柔韧,它照亮了纤细尖端前面的道路。你用它小心探查,纤弱一如蠕虫。
尺蠖的一生如此盲目,其荒谬的程度几乎无可比拟。尺蠖是几种蛾子或蝴蝶的幼虫,甘蓝银纹夜蛾就是其中一种。我经常见到尺蠖,这长约一英寸的鲜绿色小虫如同叶脉般纤细软弱,看起来丝毫不适合在这世间生存。尺蠖的全部时光都是在不变的惊恐中度过的。
我见过的每只尺蠖都困在长叶草丛之中。悲惨的尺蠖悬在草叶的一侧,不停地左右摆头,似乎要发出哀鸣。怎么了?不能前进?!它的后足紧紧贴在草茎上,三对前足悬在空中向后乱摆,显然是在寻找落脚点。怎么了?不能前进?!怎么了?它在广袤世界里四处搜寻这片草的余下部分,可是草其实就在它鼻子底下。这个笨蛋运气还算不错,它的前足触到了草。它悬在草上,躬起绿色的身体,后足挪到前足后面,整个身体就弯成了环形,像绳圈一样。现在它所要做的只是把前足沿着草茎滑向前方,然而,它又一次茫然失措。它仰起头抬起前足,把上身伸向空中,再次陷入惊恐。怎么了?不能前进?!到了世界的尽头?如此反复,最后它居然爬到了草叶叶尖,此时它细小身体的重量或许会把草压得倒向其它草叶。叶尖伴着它的末日祷告摇摆,把它甩到别的东西上。这番情景我见过多次,这盲胃慌乱的蠢笨小虫离开了身下的草叶,落到另一片草叶上。之后又是几个小时歇斯底里般的爬行,每一步都会把它带到世界边缘。怎么了?不能前进?!到了世界的尽头?哇,这里可以落脚。怎么了?不能前进?!啊呀!
“你为什么不会跳呢?我厌恶地对它说,“让自己从痛苦中脱身吧。”
我钦佩那些十八世纪时的哈西德教派信徒,他们知道祷告具有风险。拉比尤里·斯泰利斯克(Uri of Strelisk)每天早晨走出家门时总是心怀悲伤,因为他要去做祷告。他告诉家人,如果祷告为他带来杀身之祸,他们该怎么处理他的手稿。同样,一位祭司每天早晨和妻儿道别时总会落泪,仿佛此后再也无法相见。朋友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回答说:每次开始祭祀时我都要向主呼唤,然后祈祷“请怜悯我们”。在我向主呼告之后和祈求怜悯之前的那一时刻,谁知道主的威力会带给我什么呢?
如果你被困在一本书的写作中,如果你写到半路,明明知道下面要出现的是什么却又无法继续,如果你连续一星期或一个月每天早晨都进入它的领域却又转过身去,那你遇到的问题就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是结构出了岔,叙事或逻辑出现了细如发丝的裂隙,整部作品终将一分为二。或者是你正走向一个致命的错误。你之前规划的写法根本行不通。假如你沿着现在的道路继续前行,遇到的就将是爆炸或坍塌,而你现在还一无所知。
1987年4月的一个清晨,在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一栋在建的六层建筑突然倒塌,造成二十八人遇难。根据《哈特福德报》(Hartford Courant)的报道,就在大楼倒塌之前,街对面楼上的一位妇女倚着窗户对一个过路人喊道,“那栋楼突然开始摇晃了。”“夫人,”过路人回答,“你脑子出毛病了吧!”
你只需注意到这一点:你的雇工,你唯一的雇工,让你为之骄傲、得到你的喜爱、具有责任感的雇工,不想去做那份工作。他不会妥协,哪怕是为了你这个雇主。由于投身其中已久,他能闻得出空中怪异的气味,能感受到鞋底传来的震动。你说这是无稽之谈,这里非常安全。但工人还是不去,甚至看都不会看工地一眼。我心脏出了问题。宁愿挨饿。抱歉。
你能够做什么呢?首先,确认自己并非无计可施。铺排已有的结构,用x光搜索细如发丝的裂隙,找到它,用一周或一年的时间进行思考,解决无法解决的问题。或者让遇到障碍的作品下一部分接受严厉的考验,这一部分包含着未经审视的错误的前提。某种看似完全必要的东西是错误的或致命的,一旦你发现它,并且能够接受所发现的,那当然就意味着重新开始。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有经验的作家要求年轻人学习一门有用专业的原因。
每天早晨,你都要爬几段楼梯,走进书房,打开落地玻璃门,把书桌和椅子挪到半空中。书桌和椅子悬浮在离地三十英尺的空中,周围是枫林的树冠。家具已经就位,于是你回去拿咖啡壶。然后,你退回来,再次迈进落地玻璃门,坐到椅子上往桌子下面看。在冬天,从你的位置可以清晰地看到河流。你给自己倒了杯咖啡。
鸟儿在你的椅子下飞过。在春天,枫树树冠萌发出新叶时,你的视线停留在桌子旁的树顶上,黄莺在高处的嫩枝间窃窃私语,捕捉飞虫。你开始工作。你的信念如同引擎,让你和你的书桌一直悬在空中。你的工作就是让飞轮不停地旋转,带动齿轮,从而快速传动引擎上的皮带。
写一本书的过程趣味横生,令人兴奋,同时又足够困难和复杂,需要你投入全部的才智。这是最自由的生活。你作为作者所享有的自由,并非脱口而出的任意表达,你不能信马由缰。如果你足够幸运能够试着写书,你就会拥有最自由的生活,因为你可以自己选取材料,构想要完成的任务,并为自己设定进度。在民主国家,你甚至可以随心所欲地写作并发表有关任何政府或机构的任何作品,哪怕所写的内容显而易见是错误的。
当然,这种自由的另一面就是:你的写作毫无意义,完全只是为了你自己;你的写作对世界毫无价值,除了你之外再没有谁会关心你写得到底怎么样。你可以在一天里自由地作出数干种接近的评判裁定。你的自由是你生活中琐碎事情的副产品。鞋子推销员完成的是其他人布置的任务,必须对两三位老板负责,必须按照老板们的要求工作,必须让自己听凭他们差遣,在他们的地盘,遵从他们的时间安排。然而,鞋子推销员的工作却是实用的。如果某天早晨鞋子推销员没有按时出现,就会有人注意到并惦念他。而你为之呕心沥血的手稿却没有任何需求或祝愿:它并不知道你的存在。同样,没有人需要你的手稿,但每个人都需要更多的鞋子。世间已经有了很多份手稿,很多有价值的手稿,发人深省的手稿,感人至深的手稿,充满机智的手稿,有感染力的手稿。就算你相信《失乐园》(Paradise Lost)是优秀的作品,你会把它买回家吗?与其说带给世界一份比《失乐园》更优秀的手稿让世界缄默,为什么不给自己一枪呢?
要想找到一棵有蜂蜜的树,先要捉住只蜜蜂。要在蜜蜂的腿上粘满花粉时捉住它,因为此时它正准备飞回家。捉住落在花朵上的蜜蜂非常容易,只要拿个茶杯或玻璃杯从上方罩住蜜蜂,在它飞起来时用一块纸板盖住杯口就可以了。把蜜蜂带到附近的空旷地点——最好是高出周围的地方——放走蜜蜂,观察它飞向什么地方。要目不转睛地盯着它,直到它飞出视线之外。蜜蜂在哪里飞出视线,你就要赶紧跑到哪里去等待,等到在那里再看见一只蜜蜂时,同样捉住它再放掉它,然后观察它飞向何处。这样,一只接一只的蜜蜂会把你带向有蜂蜜的树,直至你看到最后一只蜜蜂飞到树上。梭罗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一过程。一本书也正是以这样的过程引导作者的。
你或许会感到疑惑,不知如何开始,如何捉到第一个猎物。该用什么来做诱饵呢?
你别无选择。欧内斯特·汤普森·西顿(Ernest Thompson Seton)讲过一个并非发生在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是个酷寒的冬天,在北极,阿尔冈昆族一个营地的人们都在饥荒中饿死了,最后只剩下一位母亲和她的婴儿。这位母亲走出营地,在一座湖边发现了一处贮藏物品的地方,里面有一个小鱼钩。要把鱼线拴到鱼钩上并不难,但她没有鱼饵,在冰天雪地中也不可能找到鱼饵。婴儿在哭叫。她拿起一把刀,从自己的大腿上割下了一块肉。她用自己身上的肉做鱼饵,钓到了一条狗鱼。她吃掉了鱼肉,喂饱了孩子,当然也留下了鱼的内脏作为鱼饵。她靠吃鱼活了下去,直到春天来临才再次出发去寻找别人。向西顿讲述这件事的人亲眼见到了她腿上的伤疤。
对于那些因自己的写作速度感到失望沮丧的朋友,你可以用下面的话安慰他们。
写一本书需要几年的时间——通常是两年至十年。有人不到两年就能写出一本书,但那种情况太罕见了,不具有统计学的意义。一位美国作家在六十多年里写出了十二本主要作品,其中一本堪称完美的小说是在三个月内完成的。然而他在谈起这些时仍然带着敬畏之心,从不会高声谈论。谁愿冒犯让这些书问世的那个精灵呢?
福克纳(Faulkner)只用了六个星期就写完了小说《我弥留之际》(As I LayDying),他说自己每天要从事十二小时的体力劳动,这本书是他在休息时匆匆写出来的。在其他地区和其他时代也有类似的例子,这就如同人群中有时会出现白化病患者、暗杀者、圣人、巨人和侏儒。在这世界上的数十亿人中,或许能有二十个人可以在一年内写出一部严肃的作品。有人能徒手抬起汽车。有人参加持续一周不间断的雪橇狗竞赛,有人乘着大桶顺尼亚加拉瀑布而下,有人驾着飞机穿过凯旋门,有人不会感到生育之痛,有人声言吃掉汽车。没必要把极端的例子视为常规。
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注意到,由于一本长篇小说“或许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作者写到结尾时已经与开始动笔时的自己不同……就仿佛这部小说是他从孩提时代开始写作的,等到作品完成时他已经步入老年了”。约翰·贝里曼(John Berryman)说,长诗的写作耗时五到十年。托马斯·曼(ThomasMann)是创作天才。他专职写作,每天写一页。而他的确是每天都要写作的,这就意味着每年写出三百六十五页,每年写出一本篇幅可观的书。每天写一页,他因此成为迄今最多产的作家之一。福楼拜(Flaubert)不间断地写作总是使得自己劳顿不堪,其程度令人惊骇。他在二十五年里每五至七年写出一本长篇巨著。如果一名专职作者每五年写一本书,就意味着每年要写七十三页可采用的内容,每天要写五分之一页可采用的内容。传记作者或其他写实文学作者需要几年时间收集和整理素材,长篇或短篇小说的作者需要几年时间架构一个完整可靠的世界来呼应那些虚构的事件,二者所用的时间可以相提并论。有时作者可以在很多日子里每天写出三到四页的内容,但是一段时间后他就会认为自己必须删掉这些内容。以上事实可以安慰那些备受煎熬的写作者。当然,这绝不意味着用更快速度写出来的书质量更差,而只是说,大多数作者不必因为写作进度平常或缓慢而苛责自己。
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引用过这一例子:“圣波尔·鲁(Saint-PolRoux)睡觉前常把‘诗人此时正在工作的题字挂到门上。”
有人认为,人们在某个季节写出的东西会比在其他季节写出的更好一些,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把这种观念称为“在舒适愉快中生发出来的想象力”。闲散想象力带来的另一种舒适愉快,就是作者对自己作品的感觉。然而,就正在创作过程中的作品而言,作者对它的评估与它的实际价值之间的关系既不成正比也不成反比。不论觉得作品很宏伟还是很拙劣,两种感觉都如同蚊子,应该或驱逐、或忽略、或消灭,而不是沉湎其中。
原创的写作塑造出作品的形式,因此一篇散文要在写作的过程中得到完善,要在架构文章之前先写出每个句子。一切从一片空无中渐渐显现。从一个细胞到另一个细胞,从树干到树枝,从枝桠到树叶,慢慢生长。每个精心考量的词语都可能昭示着一条道路,触发一串隐喻或一系列事件,并以此为基础继续发展出大部分或全部内容。作品一步步走向完美,从第一个词到最后一个词的落笔,都展示出这种写作方式唤起的勇气和恐惧。作者的笔触会赋予作品活力,推动它走向最真实的结局,就如同画家贾科梅蒂(Giacometti)用铅笔寻求精确和真实一样。已经写下的那些严肃内容哪怕很少,也会燃起作者的希望。豪情赋予他勇气,激励他前进。在华盛顿的一位写作者查理·巴茨(Charlie Butts)无比珍视写作的动力而又惧怕自我意识,于是他想出了一种急速写小说的独特方式。他先是找些事情离开家,然后匆忙跑回家门,连外衣都不脱就径直坐到打字机前,把小说己完成的全部内容用最快的速度重新打出来。写作的冲动驱策着他,在他有意识地进行写作并停下来思考之前,他往往已经比原来多写出了一两个句子。而后他再次离开家,重复这一过程。他跑进家门,用打字机重新打下整个故事,希望能再挤出一个句子,就像某辆车熄火后引擎还在转动,又好像华纳动画片中的大笨狼怀尔(wile E.coyote),刚从悬崖上跌落时要在空中继续跑几步路,才发现自己已经摔下了悬崖。
不要在写作过程中完善作品,原因同样是,原创的写作塑造着作品真实的形式。这一形式只有在作品的写作过程中才能发现,因此最初的落笔都是无用的,不论它们看上去多么光辉炫目。一个段落在整部作品中的作用必须是清晰的,作者在构思时才能让细节的复杂性强化作品的结尾。
小说作者笔下的人物如同流氓一样凭借蛮力“接管”作品时,作者只有无助地朝上甩动手臂,神灵又能做什么呢?我认为,这些小说的作者可以参考影响任意一本严肃作品的结构的奥秘,不论作品中是否会出现从内部引发混乱的第五纵队式的人物。有时一本书的某一部分就只是起身离去,作者无法强迫它回归原位,它只是脱离整体的结构,离开,失去生命。这就像也可称为星鱼的海星那样。海星这种常见的生物令人称奇,它有多条触手,每条触手都如同一道星光。海星时常断掉身体的一部分,没有人知道原因。一条触手就这样扭动着从身体上脱落,落到一边。蒙克斯博士(Monls)这样描述过生活在多礁石的太平洋沿岸的一种海星:
“我倾向于认为海星……不论遇到什么刺激,都会自己断掉触手。海星在环境改变时断掉触手,这有时只发生在把海星装进罐子的几小时之内。……不论受到什么诱因的促发,这种动物都能够也的确会断掉触手。……常见的情况是,海星身体的主要部分留在原地不动,管足搭在要断开的触手一侧,为了让这条触手能朝着与身体成直角的方向缓缓离开,它会变换位置,不停扭曲,主动做出各种必要的动作。”海洋生物学家埃德·里基茨(EdRicketts)这样评论道:“在一种有意让自己分裂的动物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事物所能达到的极致。”
写出来的词语是苍白无力的,很多人更看重鲜活的生命,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活,美好的人生。写作只是写作而己,文学只是文学,它们只调动最精微的感官——想象的视觉和想象的听觉——以及道德感和才智。你从事的写作让你如此紧张如此震撼如此兴奋,似乎你正随着乐队的伴奏翩然起舞,可是其他人却什么都没有听到。读者的耳朵必须作出调整,从生活的喧嚣鼎沸转向书面文字发出的假想中的微弱声音。普通读者刚拿起一本书时还什么也听不到,要过半个小时才能跟得上作者音调的抑扬顿挫和高低起伏。
一项有趣的昆虫学实验显示出,雄蝴蝶看到画在纸板上的蝴蝶时,如果这只纸蝴蝶的个头够大,超过了雄蝴蝶,超过了任何一只可能存在的雌蝴蝶,那么雄蝴蝶就会更喜欢这只纸蝴蝶,却对身边的同类视而不见。他会反反复复扑向这只纸蝴蝶。而就在旁边,雌蝴蝶正徒劳地扑扇着翅膀。
电影和电视同样通过把物体放大的方式刺激着身体的感官。银幕上放大到九英尺的英俊面庞和三英尺宽的笑容,总是令人无法抗拒。那男士迈着墙一样高的长腿,径直朝你的方向走来。音乐响起,荧屏上耀眼的移动影像冲击着你的感官。你不喜欢电影中车辆的急速追逐吗?难道你能转身而去,难道你能移开视线?即使明知不由自主,你仍然会紧盯着银幕,如同那只身不由己受到纸板画吸引的雄蝴蝶。
电影就是如此。那是它们的领地。在电影的领地,纸上的字词不能也不该与之竞争。你可以描写美丽的面容,描绘汽车的激烈追逐,或者满山谷骑在马背上的印第安人,但是就算穷尽你的词汇,你的叙述仍然比不上电影的壮观场面。在写作时如果念念不忘电影的场景,写出的小说只会带着虽不明显然而确定无误的迹象通向绝路。我无法确切指出,文本中的什么内容会提醒读者去怀疑作者动机不纯,我也无法详细说明,一些书中的哪些句子让我越读越失望,越读越怀疑作者,直至最终合上书不想再读。这样的书似乎不安于成为书籍,而是渴望甩掉外衣跳上荧屏。
为什么有人更愿意阅读书籍,而不是观看银幕上移动着的那些放大了的人物形象呢?因为一本书可以成为文学作品。这精巧的东西微不足道,然而属于我们自己。在我看来,一本书越是纯粹地运用文字,每个句子的安排越是巧妙,内容越有想象力,论述越详尽越深邃,这本书就越有文学性,而一本书的文学性越强,就越有可能让人喜欢。毕竟,不论文学究竟意味着什么,读书的人都是喜欢文学的。他们喜欢或需要独属于书籍的东西。如果他们晚上想看电影,自然就会找电影看。如果他们不喜欢读书,自然不会读书。阅读书籍的人并非懒得打开电视,他们只是更喜欢书而己。我能想到的最可怜的事情,就是耗费几年时间努力写一本书,试图取悦那些根本不想读书的人。
你爬上长长的阶梯,直至可以鸟瞰屋顶或云朵。你正在写一本书。你看到自己的脚一步步踩过每个圆形的梯级,不匆忙也不停歇。你在又高又陡的梯子上用脚感受着平衡,绷紧大腿的肌肉阻止梯子晃动。你稳步攀爬,在暗处悄悄完成工作。你到达梯子顶端无法再往上爬时,阳光扑面而来,明亮宽阔的空间让你吃了一惊,你已然忘记了终有尽头。你回头看着脚下远处草地上的两条梯子腿,惊异之情油然而生。
这行文字从你心上抚过。它侵入动脉,猛地一口气闯入心脏。它轻压一开一合的厚实瓣膜的边缘,触碰到奔马般结实的暗色肌肉,它继续摸索,但不知道会发现什么。奇异的图片如同包在囊内的蠕虫一样深深嵌入肌肉——某种模糊的感觉、一首已经遗忘的歌曲、昏暗卧室中的场景、林地的角落、恶劣的餐厅、高出路面的人行道,这些碎片无不负载着意义。这行文字剥去它们的外壳,进行剖析,露出来的组织会发光吗?你想把这些场景暴露在光线下吗?你可以探明它们,离开它们,也可以用力戳刺那个地方,直到那痛处流出的血滴在你的手指上,然后用血书写。如果伤口并不致命,如果伤口不会扩大并造成阻塞,你可以在多年里一直运用它的力量,直到心脏把它再吸收为止。
这行文字在苍穹探寻裂隙。
这行文字踏上征程,今晨掠过木星。它以每秒150公里的速度前进,悄然无声。巨大的黄色行星和它那些白色的卫星在旋转。这行文字快速掠过木星和它那令人炫目的滞重轨道,既不向左看也不向右看。它很快就要离开太阳系,目标专一,全神贯注,灵魂一般在太空猛冲。你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看着监视器。眼前的模拟画面上,这行文字在静静等待,不言不语,充满渴望地指向目标。巨大的黄色星体如同投出的球一样向着它旋转,低低地从外侧经过它的身旁。木星如此巨大,边缘的弧形在屏幕底部看起来似乎是平坦的。探测器向前盘旋,不羁地从那些看上去有如小圆点的白色星体之间穿过。这些星星纷纷向两侧退去,如同隧道墙壁上的灯光。
现在你看着符号在显示器上移动,你盯着探测器发送回来并转换成你的语言和数字的信号。或许今后你将会猜出它们的意义——关于太阳系边缘的空间,或者关于你的仪器设备,它们可能具有的独特意义。此时,你正在飞翔。此时,你的工作就是凝神屏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