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共的陷落
黄修毅

张志忠原“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武装部长。1950年被捕,在牢房里被监押到1953年底,后被枪决。曾与他同监的狱友石聪金记得,他临行前劝慰:“两万五千里长征,失掉联络的党员,二十年、三十年再联络上的也有;不要大家都去当烈士。”
接头
1946年,位于台中闹市的大华酒家,自开业后觥筹交错、夜夜笙歌,被当地名流视作“上档次”的交际场所,不时有官厅要员现身。女主人虽年过四十,依旧面容姣好,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台语和北京话,嘴里镶有一颗金牙,让人过目难忘。
酒家由女主人的“弟弟”出资盘下,楼上有一道专用楼梯直通一个临马路的房间,是女主人避客时的居所。五月的一天夜晚,一位身材魁梧、面目黝黑的四十岁左右男子,专挑顾客盈门的钟点,直上大华酒家的阁楼而来。
女主人似是等了来人多时,情急之下口齿凌乱:不久前,在国军某团团长谢懋权的欢送会上,谢趁与她共舞之机,直勾勾瞪着她的眼睛说,“我们这次回大陆,一定要把共匪全部消滅……”
来人劝慰道:“不要紧,我们得到了重要情报,反动派开始从台湾抽掉匪军回大陆,准备打内战……你以后有这样的机会,要继续争取参加”。
几句话稳住了女主人的心,也传递了组织给她的任务,“做(岛内)中、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和秘密地下工作的党员切断联系。”
在台湾民间,关于大华酒家女主人的传言已神乎其神:她的姓名是“谢雪红”,本是台中一个商人的姨太,早年随夫到上海办货,在旅馆里和一个青年姘识,即同该青年以手枪威吓其夫,索得巨款同游苏俄。
谢雪红与共产党的联系可以上溯至1924年,她在上海结识了瞿秋白的台籍学生蔡孝乾、翁泽生等人,在他们成立的“台湾自治协会”中表现活跃,“万绿丛中一点红,特别博人激赏”;此后,她又成为莫斯科东方大学唯一一名台籍学生,当时同行者中的张国焘夫人,日后忆及她“会说国语,日语讲得更好,到了莫斯科,就入日本学生班上课,(在班上)是非常受欢迎的。”
时过境迁到了1946年,她与共产党关系如何,外界莫衷一是。倒是此时她刚刚重新申领了国民党党证(1925年国共合作时期即在杭州入党),其入党介绍人还是“政学系”巨头陈果夫;而谢常携一只掉漆的旧皮包,据说是当年在莫斯科时,日共领导人德田秋一所赠“信物”,从牢中到狱外,一直追随在她的身边。
直到这名黑皮肤来客在大华饭店现身,几个星期里岛上的风言风语才算逮着了影子。从南到北都有人宣称见过他,但他的行事似乎特别谨慎,从不透漏关于自己动向的口风。有人注意到“他的一副小腿肚圆滚饱满,在台湾只有人力车夫才有”。
他也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显示出早年在台接受过教育。在他短暂逗留嘉义朴子乡间,见他面熟的乡亲们也不敢确认:这位自称“张志忠”的来客,是不是十多年前离家的“张梗”?那个当年在厦门跟着共产党办报抗日、在日警搜捕下装疯撒癫的“野小子”,如今轻易就能“从手提包里掏出一打国际贸易通行汇票”。
在台的共产党四位主要领导人当中唯一一个拒不自新,而遭枪决的是张志忠。他的妻子季沄,被以“与老郑(蔡孝乾的化名)有通讯往来”的罪名同遭枪决。

不管他叫“张梗”还是“张志忠”,都不复为吴下阿蒙。此次回台,他身边还添了一位长相体面、常着旗袍的新娘相伴,说是从海外留学回来,在台北的中学当教员。这番巧心经营,在老台共林樑才之妻柯秀英眼里,却露着一丝破绽:“这位远看俏丽的新娘,近看却发现脸上有白麻点,这是天花留下的痕迹,当时台湾人一出生即种牛痘,稍加分析便可知她是从大陆来的。”
潜伏
“张志忠”携妻重归故里,似与过去的“张梗”斩断了联系。邻人们告以“在他偷渡到中国大陆后,日本人常抓他的老母在街上长跪”,他不动声色。过去的老同志在街市撞见,他只装作不认识。亲近他的人,私下里却叫他“老吴”。
从妻子季沄寄回大陆的家书里,可知他们抵台后的婚期也一拖再拖,从1946年“双十节”改成了“十二五台湾省光复纪念日”。约定这个日子,是因为“他十年未和家中通讯,母亲逢年过节都哭哭啼啼纪念他,全家以为他早被秘密处死”。
张志忠这条命是捡回来的,1928年日警在上海租界、东京和台湾同时展开反共大搜捕,他沿中国东南海岸一路北漂至青岛、大连,侥幸得脱。滞留岛内的台共及其同路人,在这十数年的漫长岁月间,几乎无一幸免牢狱之灾。
其间,岛内秘密召开的两次台湾共产党代表大会,都是在重要代表缺席的情况下举行的:1928年8月的台共第一次会议,谢雪红取消了缺席者蔡孝乾等人的党籍;而在1931年5、6月间召开的台共第二次会议上,谢雪红又反过来遭开除出党。
这来回往复的拉锯,也是台共党人自1920年代在厦门、上海、东京三地渐成气候起,埋下了此后岛内左翼势力难形成合力的先兆。
谢雪红和“表弟”林木顺早在台共“一大”筹备期间就被指定为与日本方面的联络人,依循当时国际共产(第三国际)的指示,在日共领导下开展“台湾支部”的工作,甚至不分疆界地吸收过朝鲜的独立运动激进分子。
而在厦门读书时接触到共产主义的那批人,其中就包括张志忠,最早甚至还集体学习过蔡孝乾编写的《新兴经济学》,他们试图在岛内籍民族主义的兴起鼓动共产运动。
这两股施之于台湾共产党人的影响,在上海积聚又交错。瞿秋白在遭党内批驳之前,他被谢雪红、蔡孝乾、张志忠等人共奉为师。1928年日警反共大搜捕,台共党人四散后,蔡孝乾、张志忠踏上流亡之途;而滞留东京的共产党人陈来旺,在被日警破获的一份报告中曾写道,“中共支部的成员,竟不知道台湾共产党的存在”。
1945年8月,国民政府接手台湾后岛内政治气象突变,不出半年,张志忠奉派秘密潜回,此时的他已颇有革命履历,抗日战争期间他参加了苏北的新四军,此后在冀南军区从事“敌工工作”;而晚他三个月抵台的蔡孝乾更是资历显赫,作为惟一一个参与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台籍党员,他在中共中央“以少数民族代表身份”居于高位。
经历了日据时期十数年的“失联”,共产党再次踏上这个形势复杂的岛屿,不由得格外小心翼翼。
先期抵达的信使,是一位《大公报》记者李纯青。1945年10月5日下午五时,伴随着三架从重庆九龙坡起飞的美军运输机在台北松山机场降落,他身为记者代表团的一员,混迹于国民政府受降长官的随员之中,实则肩负着周恩来亲自嘱托的“排摸”任务。
他捎回的信息是“老台共的人(在日据时期)全部被捕,全部转向(变节),只有谢雪红一个人是可靠的。”此后便有了谢雪红与张志忠接头的一幕。
同样為了核实张志忠的身份,谢雪红特意派出一名台北市郊老农,在李纯青的带路下去上海找“组织”。证实了1946年初,经中共华东局同意,设立了归上海局领导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工委”),并任命蔡孝乾为“省工委”书记,乃岛内共产党活动的最高领导;张志忠为武装部长。
谨小慎微的接头工作,佐证了旁人的眼光:张志忠那圆滚滚的小腿,确是长期行伍塑造的。此时已铁路贯通南北的台湾,很少有人再靠一副腿帮子东奔西突了。而回归乡里的他,仍沿袭着他在大陆养成的习惯,光着脚丫子,出没于城市边缘的山林地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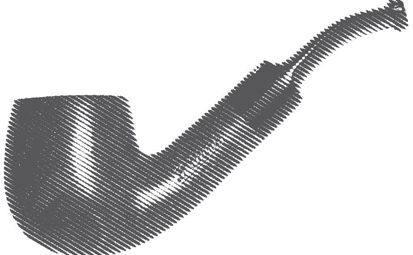
“二二八”事起,刚在岛内立足的共产党人,即在“省工委”领导下形成了分工,“一部分党员全力准备武装斗争,另一部分党员进行宣传工作”。此时新被吸收入党的青年,大多是没有在内陆革命经验的学生与知识分子,他们常常是白天忙于“寻枪”,夜里“听广播”刻蜡版。
从妻子季沄写给大陆亲人的家书里,尚能嗅出这对夫妇“潜伏”期间的生活气息。季沄几番劝说家里人来台一游,并言“台湾受教育普遍”、“铁路交通方便”,只是“台湾女人都是穿洋装”,她“领教不了”这里的中装剪裁,特意要家人从上海做件旗袍带来。
在她家书中,“从诊所拿药”几个字频繁出现,而又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此“诊所”特指位于上海南京西路上的“伟光医院”,其业主打着“上海台湾同乡会”招牌,实为中共和台湾共产党人活动之间的联络站和补给线。因当日岛内物价腾贵,由上海的组织供给的地下党活动经费,大部分置换成药品,再通过“救济署”申领,既扛货币贬值,又便掩人耳目。
火药味
陈仪入台湾后经济措施不力,岛内物价节节蹿升。再加之官员贪腐枉法,在台湾民众间激起巨大怨怼。据统计,陈仪当权不到两年,查禁刊物836种,超过日本都政府时期的总和;而在民间收藏木屐,甚至也被列为留恋皇民统治的罪证。
时至1947年,国共两党在东北陈兵百万,内战已不可避免。乡下人当中甚至开始传说,林彪是台湾人(误为谢雪红的“弟弟”林木顺),等他带兵打垮了东北的蒋军,就要回来解放台湾。
改变岛内政治走向的“二二八”事件,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一触即发。1947年2月29日中午时分,群众涌往电台,要求广播台北流血事件,号召全省响应抗议斗争。云集了岛内左、中、右三派的人士的临时决议机构“处委会”迅即成立,“二二八事件”的火苗在全岛瞬间成燎原之势。
台湾的非武装政治运动素有渊源,早在1907年,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维新派”领袖梁启超曾与岛内的进步士绅林献堂见面。梁语于林,中国在卅年内必无力拯救台湾,台人当效仿爱尔兰之抗英,以议会路线手段争取权益。
“二二八”事起,刚在岛内立足的共产党人,即在“省工委”领导下形成了分工,“一部分党员全力准备武装斗争,另一部分党员进行宣传工作”。此时新被吸收入党的青年,大多是没有在内陆革命经验的学生与知识分子,他们常常是白天忙于“寻枪”,夜里“听广播”刻蜡版。

谢雪红在台中领导的武装暴动,声威最是壮大。这个老板娘摇身一变成花木兰,挺一支手枪,挥一面小白旗(示意让道),站在满载武装警察的卡车车头,带领群众包围警察署、生擒了当地的贪腐官员。她的这副形象,1947年4月7日登上美国《时代》周刊,成了外媒报道中Snow Red的定妆照。
时常孤身跑进山里的张志忠,此时统领着一队武装青年,正准备从南部山区挺进台北西边的桃园。他征募来的人手,有从日据时代被调去南洋从军、或做军夫经受过专业军事训练的闲散归台人员,也不乏地方上的义勇,已在山中跟着他练枪多时。
事变后四五日内,起义军几乎攻占了嘉义机场,用“处委会”委员、曾是台共同路人的作家杨逵的话说,“当时连议员也弄不清怎么回事……只消几个钟头就可以把宪兵和军队的武装解除。”
待到3月4日,蒋介石派出正规军从基隆扫荡过来,临时凑集的部众面临土崩瓦解,此刻“老郑”(蔡孝乾化名)突然现身大华饭店,也是他回台之后首次与谢雪红见面。
故人相见,却是五味杂陈。如今这俩人,一个是大陆派遣台湾的共产党组织最高领导人,一个则是以公开身份活动在岛内颇孚人望的老台共。但深埋了二十年的恩怨过从,让两人之间仍有散不去的火药味。
经过长征的洗礼,蔡仍不改他的绅士派。圆框眼镜配白色毛料西裤,一副文弱模样,谢见了劈头就问,“为什么不早点来见我?”
蔡沉默不语。冷场很快转变为激烈的争吵:日益危殆的局势,组织上的混乱,武装力量的指挥权,都成了双方争论的焦点。
僵持不下时,历史旧账就被翻上台面,谢的党龄问题(1925年入党,后因长期失联而未获承认)至今没有解决;而蔡咬住不放:除非谢先写一份自白,清楚交代日据时期台共变节的经过。
意见分歧挟着难言的私怨,让两人的见面最终沦为一场无法做出关键决定的妥协。蔡依仗他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资格,要求部队分散到山里去打游击,同时不放弃在城市的正面宣传战场,“要办日报”。反诘者如杨逵等则认为,“台湾太小了,坚持不了多久”。
瓦解

领导意见的分歧,使得撤退至山区的部队各自为战,据台湾“保密局”档案,“台中之谢雪红部,及嘉义之张志忠部,因无联络配合,又互存依赖心理,各自为战,致遭全部覆没”。
在蔡孝乾的坚持下公开办起来的报纸《光明报》,在台北街头散发时被国民党情治机构查抄,最终却成了整个“省工委”被破获的关键线索。
局势的急剧恶化,使得组织下令以公开身份活动的谢雪红,先批撤出台湾,被推举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后,再也没有涉足故土。她与蔡孝乾、张志忠的最后一次晤面,已是在1948年6月的香港,秘密召开的“台湾工作干部会议”上。
据台湾“国安局”档案228-E-3-(14)披露,此次秘密会议规格甚高,参与其事的除了老台共谢雪红、派遣干部蔡孝乾、张志忠等人之外,广东与海南两省也各派出一位代表列席。会上,蔡孝乾检讨了“对形势过于高估”;但他也同样头痛于中共机构在岛内的“双轨制运作,领导台籍同志是一条线,大陆派遣同志则是另一条线”。
尽管在“二二八”以后不到半年时间里,共产党在台湾的组织,从1946年初的70余人扩充到了约400人,但“本省籍与外省籍党员的关系”“如何扩大党在工、农中力量”的问题迭出,直至惊动了上海局的领导人张执一出面发话,“谁是谁非,要到台湾解放,掌握了充分资料后方能作出分析……”
在蔡孝乾的坚持下公开办起来的报纸《光明报》,在台北街头散发时被国民党情治机构查抄,最终却成了整个“省工委”被破获的关键线索。
在国民党情治系统的相关报告里,甚至指出“中共在岛内未及建立电台”,而中共地下组织的“双轨制运作”,后来竟成国民党间谍瓦解“二二八”后岛内组织残余力量的惯用伎俩。
1950年2月的一个夜晚,有陌生人来到尚在三湾坚守的台共组织支部,把一只眼熟的皮箱交给了当地同志。来人信誓旦旦地说,“老吴叫我把这个皮箱交给你们,老吴要我告诉你们,台北的形势很紧张,希望你们赶快把竹南、苗栗地区的主要干部集中起来,二月十五日,他会下来,跟你们讨论重要事情”。撂下话,来人即不见影踪。
三湾的同志打开皮箱检查,发现里面有张志忠常穿用的西服一套、收音机一只、一把勃朗宁手枪和三十余发子弹,悉为他平日的随身物品。当他们几乎据此认定来人是“老吴”的信使时,一个机敏的同志,拆解了手枪,才发现撞针已被锯断。“这是老吴在向我们示警,他很可能已经被捕了。”
1950年3月,从四川派遣来担任“省工委”宣传部长的洪幼樵,刚在基隆登岸,误以为遇上了接船的“自己人”,即束手就擒;而以半公开身份活动的蔡孝乾,则在厦门街的家中被埋伏逾月的特务逮捕。再加上半年前《光明报》事发后,遭叛徒出卖被捕的“省工委”副书记陈泽明,在台的共产党四位主要领导人至此悉数落网。
狱中,以破获“省工委”机关邀获大功的国民党保密局上校谷正文,刻意安排了一桌酒席,让四人相对而坐。最早被捕的“省工委”副主任陈泽明,按耐不住冲蔡孝乾发难,“我们的失败都是你一个人造成的!回台湾之前,你从未交代自己的老台共身份……”
在同志逼问下,这位台共领导人从此竟一个人躲进狱房角落,没日没夜赶写自白书,稿纸堆垛成半人高,碰倒了,他也无所知觉。最终谷正文把他的写字桌,从保密局监狱搬进了台大精神病院。
四人当中唯一一个拒不自新,而遭枪决的是张志忠。他在牢房里监押到1953年底,鹿窟的最后一熄武装斗争被掐灭之后,才被押赴刑场。曾与他同监的狱友石聪金记得,他临行前劝慰:“两万五千里长征,失掉联络的党员,二十年、三十年再联络上的也有;不要大家都去当烈士。”
他的妻子季沄,被以“与老郑(蔡孝乾的化名)有通讯往来”的罪名同遭枪决,在国内的家人直到1950年代晚期才闻此噩耗,但从未得到“烈士家属”的待遇。曾为女儿的天花痊愈四处求拜观音的季同老太,一直到死都难以释怀:“领导不该派她去台湾做地下工作的”。
此后蔡孝乾變节加入国民党,直到1982年10月在台湾病逝前遭长期监视。先一步撤出岛内的谢雪红,也未能逃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陆政治风波的整肃。她早年与日共乃至国民党纠缠不清的关系,日后都成为了指摘共产党人在岛内失败的口实。倒是1930年代她被日警抓捕时的当庭审判一语成谶,蔡孝乾等台湾的共产党人“大多是与实际运动疏离的日本及中国留学生,他们训练组织程度之贫乏,乃是不争的事实。”
(感谢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口述史组秘书沈怀玉先生提供的帮助。参考资料:《戒严时期台北地区政治案件口述历史(全三辑)》;陈芳明《殖民地台湾:左翼政治运动史论》《谢雪红评传》;蓝博洲《台共党人悲歌》、《幌马车之歌》;杨克煌、吴克泰、张执一、李伟光、谷正文、李世杰等人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