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在台湾
黄修毅 许智博

八十八岁的陈炳基回台探亲,执意拉着老伴到马场町走一走。当地人提到“马场町”三字难免蹙眉:那里风水不好。
“1949年,要不是組织下令我们撤离,我十有八九就要在这块地方‘扎根了。”老先生顿了顿手中的拐杖,突然狠劲地敲打地面。
此地如今已修成一条沿江步道,铅灰色的淡水支流新店溪绕行过台北城南。一处七八米高、坑径十多米的坟丘荒草芜生,突兀在暮色四合的城市夜景中。昔日这里曾是国民党政府用来处决政治犯的著名刑场,冢边立于2000年的“马场町纪念公园”碑文,模糊地提到“追悼千万个在台湾牺牲的英魂”。
老先生肃立江边,声音里掩不住颤抖:“当时从监所的视窗可以望到这里,一大片无人的江滩,除了惊鸟怪叫就是枪声,我每天在里面记数,一个月不到,就听见了五十几响……”
台湾“安全局”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丛编》载,1948年10月“侦破之匪外围组织爱国青年会(新民主同志会)陈炳基一案,所获得之线索,运用关系深入侦查……扩大破案”。此案勾连出的《光明报》案,成为日后在台共产党组织“相因相循,被完全摧毁”(据《中央日报》1950年5月4日报道)的序幕。
这起在海峡对岸一度被夸示宣扬的“剿匪功勋”,在大陆却是长期湮没无闻,当事人的恩怨缠结,也因背负着“失败”之名而鲜有善终。直到去年底“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落成,使得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国共两党对峙的局面下,共产党人在台潜伏活动的历史,浮出冰山一角。
“隐蔽战线”的挫败
在台湾已世居七代的陈炳基家,祖上从福建晋江移民岛上,到了他父亲这一辈,已在台北市里开出一家“瑞发”布号,过上了殷实的生活。家里人怎么也想不到,在法商学院(后改制为台大法律系)读书的长子陈炳基,1949年的一别之后,竟有近半个世纪未曾踏上故土。
1949年台湾“四六”事件(1949年4月6日,当天共有100多名学生遭逮捕入狱,其中有7名学生被捕后枪决,此事件后部分学生纷纷出走中国大陆,一般被认为台湾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滥觞)后,“陈炳基”的名字即上了法院的通缉名单,他的身影从此在亲友面前消失;而名单上另外几个名字,再见到时,竟大多化为在墓碑上的铭文。
当年以学生领袖身份在台被吸收入共产党的陈炳基,在“二二八”(1947年2月28日,台北市民罢市、游行请愿,遭国民党当局的镇压,爆发了大规模武装暴动)前后以“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学生委员会筹委之名秘密发动师友、参与台北的武装斗争,事败后成员多遭逮捕。“最惨的是那些加入‘忠义服务队在台北维持治安的学生,一周之内就被当局集体屠杀了。”陈炳基说。
若非4月10日得了“组织”上提供的一张基隆到上海的三等船票,他自知也将和大多滞留岛内同仁一样,难于幸免。
此后,台湾国民政府颁布了《惩治叛乱条例》和《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赋予国民党情治系统以加大对涉共嫌疑者的搜捕和打击的借口,众多仅左翼倾向的学生、知识分子也牵涉其中,致使1950年代岛内相继有9万人被捕,4千余人遭处决,酿成了一个整肃扩大化的“白色恐怖”时期。
这是国共双方绵延三十年的角力过程中,鲜有的中共在“隐蔽的战线”上遭遇的沉痛挫败,也阴差阳错地开启了岛内的一段“惨史”。 北京西山纪念碑的铭文可资印证:“1949年前后,我军按照中央关于解放台湾的决策部署,秘密派遣1500余名干部入台,被国民党当局公审处决1100余人。”
此次由总政治部联络处筹措的工程,也是大陆官方首次敞露这一湮灭了六十多年的往事;这段说不清、理还乱的历史,此前长期在民间滋养着丰澹的想象,甚至一度热播的谍战剧《潜伏》也被视为以“对台工作特工”为创作原型。
在公开的历史记述中,能找到毛泽东在1949年7月发表的讲话,“我们必须准备攻占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和空军。”足见对台潜伏工作,曾被赋予极高的战略地位。而直到1950年5月,美中央情报局还曾对国民政府重申,“中共可能在年底以前夺取台湾”。
此后朝鲜战场形势的突变,扭转了历史的走向。部署在沿海的解放军三野三十七万大军掉头往中朝边境进发;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1950年初,潜伏在台准备“接应解放军攻占台湾”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在岛内遭毁灭性打击。
面目模糊
初春的北京西山,风劲草长,援山而建的“无名英雄纪念碑”掩映在松柏丛中,突入眼帘的是四尊人像雕塑,他们被一一辨认为“以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为原型的英雄塑像”。带着好奇神色的瞻仰者,甚至一意要从“吴石”塑像里认出《潜伏》男主角余则成的轮廓。
此次镌刻在西山纪念碑上的846个名字,经《南都周刊》记者核实,有189个与台湾六张犁公墓(1993年在台北市郊被发现,乱葬有大量白色恐怖时期被处决者的骨灰)的遇难者名单重合。其中不乏如“二二八”前后著名的“基隆中学案”中涉案的台籍共产党员钟浩东等人,他们于1946年“省工委”在台建立后方加入组织,严格说来,并非碑铭上所指称的“大陆派遣干部”。
因为组织工作需要,地下工作者生前大多几经改名易姓,且生前极少留下影像资料。据台湾历史作家蓝博洲考证,比如当时的台湾共产党武装部长张志忠就曾用过“张梗”、“老吴”等多个名字,而他抗战期间在冀南从事“敌工工作”又曾化名“张光熙”。这也给二十年前,台湾开始清点“二二八”及“白色恐怖”时期受难者名单时,造成了很大困惑。
有些仅是同情共产党人的左倾学生和知识分子,在“白色恐怖”的整肃扩大化时期也遭冤案枪决,在台湾被列入遇难者名单,并铭刻于绿岛纪念碑,也不乏被一并收入北京西山纪念碑的烈士铭文。
半个多世纪后,像陈炳基这样的当事人也很难对于当年繁复的组织架构,给予清晰的复盘。他涉事其中的“爱国青年会”一案,另两人林如堉、李薰山的被捕缘由,也只能停留于渺遠的猜测,“当时正是组织在台疾速发展的时期,可能是一名刘姓印刷工人经手的‘党章,把我们的秘密泄露给了军统特务。”
半个多世纪后,像陈炳基这样的当事人也很难对于当年给予清晰的复盘。他涉事其中的“爱国青年会”一案,另两人林如堉、李薰山的被捕缘由,也只能停留于渺远的猜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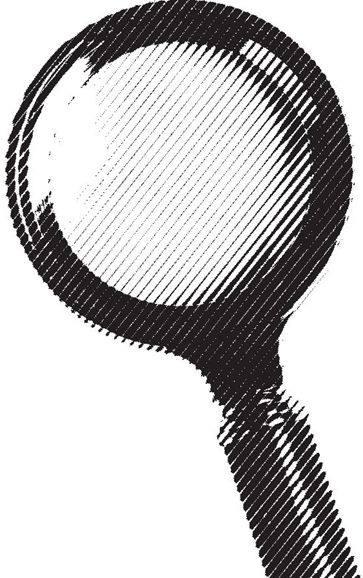
时至今日,当年岛内革命形势的瞬息起落和整个组织连遭破获,仍被归结为个别叛徒的“变节”。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就曾发文称,“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以致形迹过于暴露之外……蔡孝乾叛变导致台湾工委下属组织全部破坏”。
“蔡孝乾”这个名字因而也成为耻辱的记号,被排除在西山纪念碑的追认之外。这位当时在岛内的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早在1920年代初期即在上海组织了台湾青年的共产主义性质小组,直到1946年奉派回台前,他屡任江西苏维埃政权中央委员、八路军敌工部部长等职,曾是党内地位最高的台籍干部。
据台湾“国安局”解密文件,蔡孝乾在1947年初、1948年6月和1949年4月三次向中共中央报告,岛内的共产党组织已从最初的70余人发展壮大至400人、1300人。而随着1950年代初形势的风云突变,台共及亲共者向国民党当局自首人数,分别达到了570人与629人(据台湾“保安司令部” 1951年3月及“国防部”总政治部1952年1月的两次报告)。
个别成员的“变节”,是否是1950年代中共在岛内工作陷于瘫痪的主因?民间书写“二二八”历史第一人、持中共同路人立场的蓝博洲即称,“把地下党的失败推诿给一个人,肯定是不符合事实的”; 而台共创始人谢雪红的研究者、担任过民进党宣传部长的陈芳明则认为,“此举过分简化了中共在岛内发展受阻的障碍”。
早在1946年蔡孝乾被派遣回台领导共产党组织之前,台湾的共产主义运动即已在中共、日共的交互影响下断断续续存在了近二十年,用老台共苏新的话说,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共产主义在台湾的出现“是个怪物”,“说它是日共的一个支部,不像;说它是第三国际的一个独立支部,不像;说它是中共的一部分,又没有组织关系,也不像。”
待到1940年代后期,国共在大陆的胜负形势已然见出分晓之时,陆续复苏和潜伏入台活动的共产党人又受困于老台共的历史或对此的无知,尚处农业化社会的大陆革命经验难以直接套用于日据时期已进入工业化的台湾社会。在台湾“保密局”档案中载定:台共与中央组织缺乏直接联系、与华东局联系亦时断时续……在工农群众中毫无斗争经验,均属失败之主要因素。
后半辈子在大陆度过的陈炳基,每年回乡探亲,都习惯于居住在台北郊外的内湖,那里他曾度过了“二二八”以后在山间躲藏的日子。如今不见故人音容,只落得他孤身独吊山影,他那敛藏在墨镜后的眼里,是迟迟不见光的悠久心绪,“只有到两岸都能充分公布这部分历史真相的时候,我的这些老战友,才能瞑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