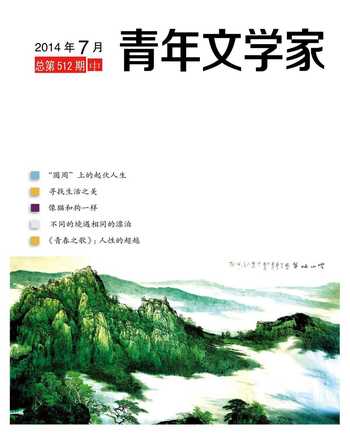用悲剧美学的视角重读余华《活着》
摘 要:小说《活着》是余华转型期的重要作品,作者用朴实无华的文字探寻底层民众的生存真相,反思生存的意义,自该作品问世以来,就被评论界反复言说,被赋予了种种解读的可能性,本文试从悲剧的审美角度出发,探索作品中所蕴含的另一种可能性。
关键词:活着;死亡;悲剧世界观;悲剧美学
作者简介:郭亚伟(1987-),女,山东高密人,鲁东大学文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汉语国际教育、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20-0-02
一
小说用不到13万字,叙述了福贵艰难困苦的一生。他的年少轻狂给自己换来了倾家荡产,“败家子”的名声远近闻名,后来他改邪归正,却又目送身边所有的亲人一个一个死去,然后再亲手一个一个将其掩埋。他背负着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坚忍地活着,踽踽独行。整部小说如同戏剧一般,将生活高度集中化,所有的矛盾冲突、一生的荣辱得失并收于十几万字之中,作者用十分极端而又冷静的笔触描写了一连串的悲剧。
其实人一旦来到这个世界上,一定不可能再活着回去,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情。可是当人活着的时候,一切又都是不确定的,只有将死是确定的。既然人生来就是走向死亡的,人注定要死去,而且死活由不得自己主宰,死亡随时都可能降临到自身,那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人明知自己的最终归宿是幻灭与虚无,为何还要不停地繁衍生息,自己承受苦难还不足,还要让后代继续品尝苦涩。说到底,活着是一个比死亡更沉重的话题。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四百多年前,莎翁笔下的哈姆雷特不经意间的一句话成了穿越时空影响深远的至理名言,这应该是哈姆雷特预想之外的,也肯定是莎士比亚所始料未及的。“生存还是死亡”,这的确是个令人烦恼的问题。实际上不只在四百年前,从几千年前开始,哲学家们就一直在锲而不舍地探索着这个问题的答案,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依然是哲学上的终极疑问。
二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奥西安尼德斯之歌仿佛可以述说一下福贵的命运或者人类的命运——朋友啊/看天意是多么无情/哪有天恩扶助蜉蝣般的世人/君不见孱弱无助的人类/虚度着如梦的浮生/因为盲目不见光明而悲伤/啊/无论人有怎样的智慧/总逃不掉神安排的定命。伟大的波斯王泽克西斯在看到自己统帅的浩浩荡荡的大军向希腊进攻时,曾潸然泪下,向自己的叔父说:“当我想到没有一个人还能活在世间,便感到一阵突然地悲哀。”他的叔父回答说:“然而人生中还有比这更可悲的事情。人生固然短暂,但无论在这大军之中或在别的地方,都找不出一个人真正幸福得从来不会感到,而且是不止一次地感到,活着还不如死去。灾难会降临到我们头上,疾病会试试困扰我们。使短暂的生命似乎也漫长难捱了。”[1]这些话并不是一两个人的哀叹,在历史中在现实中时常可以听到人们为人世间的苦难而呻吟。
而在这部作品里,作者余华将人世间的苦难最大化、集中化地安放在福贵身上,但是当福贵晚年回首往事的时候,却有一种茶余饭后的闲适和波澜不惊的心境,自己于自己一生的悲剧中体味到的不是苦涩,反倒是幸福。从惯性思维来看,文本中作者所设置的死亡事件的过于密集已经让人难以承受了,可是经历了所有事件的主人公还仍然坚韧且达观地活着,这让人觉得更加的不可思议。但事实上,同名电影在法国戛纳电影节上获了大奖,小说本身也在1998年获得颇有影响的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并且当我们真正以一个读者的身份进入这部作品时,也被那接连不断的悲剧给说服了。站在他的立场上来看待自己的痛苦和毁灭,这样,现实的苦难就化作了审美的快乐,人生的悲剧就化作了世界的喜剧。[2]
三
在美学中,关于悲剧的特征是这样定义的:首先通过对人生存在的否定性体验,从而展现对人生存在的价值的肯定;其次,悲剧的审美冲突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社会及自身的冲突和超越;最后,悲剧的情感体验是一种人生实践存在的深层体验。鲁迅先生对悲剧有一句精辟的概括:悲劇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悲剧向来被认为是最高的文学形式,能够将悲剧成功书写的作家都是很有修为的作家。《活着》是一部典型的悲剧之作,而余华对《活着》的书写显得十分驾轻就熟。悲剧把个体的痛苦和毁灭演给人看,却使人生出快感,这快感从何而来?一个平凡“小人物”的悲剧史如何就演化成了了一部经典,我们不妨从尼采的悲剧世界观出发,用悲剧的审美眼光来观照这个故事,以尝试求解。
在人性恶的前提下,从他人悲剧表演中所获得的快感就是幸灾乐祸。当巨大的灾难降临到我们自己头上时,便成为悲痛的根源,但降临到他人头上时却给了我们最大的快感。[1]福贵由养尊处优的地主阔少一夜之间变为一穷二白的穷光蛋,之前的风光无限,之后的颠沛流离,他的故事之所以吸引我们,就是因为在表现各方面都比我们强的人所遭受的痛苦和灾难时,它大大突出了我们的命运比他们的好。这也是为什么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在向人哭诉自己的悲惨故事的时候,听者“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3]
还存在一种与前者截然相反的解释,这种解释是以人性善为前提的。这种解释可以归纳为两句话或者两个命题:一、我们对受难者的同情产生观看痛苦场面的快感;二、观看痛苦场面的快感加深我们对受难者的同情。[1]但是这种解释并不比前一种更有道理,因为纯“旁观者”类型的观众很少体验到审美同情,然而他们却照样能以自己的方式欣赏悲剧。
福贵的悲剧史能够激发出我们的怜悯与恐惧。悲剧中的怜悯绝不仅仅是几滴眼泪活着多愁善感的东西,它是由于突然洞见了命运的力量与人生的虚无而唤起的一种“普遍情感”。在读《活着》的时候,我们先是感到压倒一切的命运的力量带给我们的那种恐惧,然后那令人畏惧的力量又将我们带到一个新的高度。换句话说,悲剧在征服我们之后,会使我们振奋鼓舞。首先我们感到自我的渺小,之后会突然产生一种自我扩张感和惊奇赞叹的感情。
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一书中对悲剧中的人物性格与命运做过总结:“悲剧人物不应当太好,否则他的不幸就会使我们起反感;他也不应当太坏,否则就不能引起我们的同情。理想的悲剧人物是有一点白璧微瑕的好人”。[1]我想在这一点上余华将其高超之处展示得一览无余,小说中的主人公福贵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好人,也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作者对福贵的性格与命运的设定达到了最理想的悲剧人物效果,所以才会引起无边的共鸣。
此外,叔本华说,悲剧快感是认识到生命意志的虚幻性而产生的听天由命感。尼采用一种形而上的慰藉来解脱我们,他提出,看悲剧时,一种形而上的慰藉使我们暂时逃脱事态变迁的纷扰,我们在短暂的瞬间真的成为原始圣灵本身,感觉到它的不可遏止的生存欲望和生存快乐,也就是说,通过个体的毁灭,我们反而感到世界生命意志的丰盈和不可毁灭,于是生出快感。肯定生命,连同他必然包含的痛苦和毁灭,与痛苦相嬉戏,从人生的悲剧性中获得审美快感,这就是尼采由悲剧艺术引申出来的悲剧世界观。[2]从尼采这一悲剧世界观出发的话,对于余华所说的“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理解起来仿佛也变得容易了。
四
死亡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永远都不可能是风平浪静一帆风顺的,但是我们要清楚,“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4]哈姆雷特说过这样一段话:“因为你虽饱经忧患,却没有痛苦,以同样平静的态度对待命运的打击和恩宠;能够那么适当地调和感情和理智,不让命运随意玩弄于指掌之间,那样的人才是真正幸福的。”[5]
参考文献:
[1]朱光潜. 悲剧心理学[M]. 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2]周国平译. 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M].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
[3]鲁迅. 彷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4]海明威. 老人与海[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5]朱生豪译. 莎士比亚经典悲剧[M]. 北京:京华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