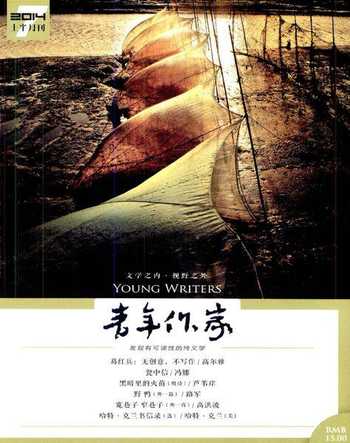老歪
我们常说,一个人的绰号最能看出这个人的特征,这话用在老歪身上,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到现在为止,没有哪一个人能够把老歪恰好地归类于某一类型之中。
可以看出,老歪不是他的本名。可他的本名叫什么,除了少数的几个人,如单位里人事部门的有关同志知道,没有人记得。说来也怪,与人见面认识,自我介绍,老歪也会告诉对方他叫什么,可过不了一小会,对方就像别人那样,喊他老歪,而把他刚告诉的名字忘得一干二净了。
老歪出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身高一米八九,山东人,今年三十六七岁,颇瘦。为人侠肝义胆,做事却随心所欲,甚至有些虎头蛇尾。
老歪最常说的话是:“人一定要有所敬畏,有敬畏了,才会虔诚,对生命,对宇宙,对自然万物。否则,即便有生之年得到许多,心里也不会安生。”听起来,这话很有哲理,甚至大义凛然,但单位老总却这样评价他:做事总不上路,能把人活活气死。我们几个熟悉老歪的人,认为这样的评价,最贴近他。
大学毕业,正赶上国家最后一批分配工作,为了能分到一个好单位,他的父亲动用了一生的积蓄,就差围栏里那头耕牛没卖了,给他谋得了一份在县卫生局工作的差事。可他倒好,屁股没坐稳,还没把椅子暖热,就在当年的冬季征兵时报了名。气得他父亲差点吐血,扬言要与他断绝父子关系。
随着运兵车来到西安,由于本科学历,他被授予了副连级中尉军衔。他写信给父亲,这才让父亲的气顺了一些,认为儿子目光远大,自己错怪了他。在部队老歪很争气,获得过二等功两次、三等功六次,没到复员就混到了副团级。按此级别转到地方,最不济也是个正科,他的父亲正等着享清福时,他却选择了放弃。父亲一下子血涌大脑,中风了,差一点就抢救不过来了。
他的放弃,自然成全了别人。那位战友谋得科长之位后,弄了两瓶“特供酒”,请他喝,他左一杯右一杯,很随性,却不醉。他的酒量在全团是出了名的,那人眼看着酒几乎被他一人全喝了,急红了眼:“老歪,你多吃菜,酒给大伙留一点!”
他笑笑,以水代酒,仍与大伙喝了个尽兴。
酒散后,他跳上火车,只身前往了西藏,自此后,那帮战友再也没有见过他。他的父亲卧病在床一年多,也没有收到他的半点消息。
在藏区,他进入一所小学,当了老师。那所学校同他一样与世无争,在地图上你根本就找不到它,就连附近的小村子,也寂静得让人以为这儿的人都不食人间烟火。老歪却很享受,课余,就跑到山里,躺在草地上看蓝天。看着看着,他的心就跟着飞了,就像他后来在一首诗里写的那样:
身体是透明的玻璃
盛开在纯净的天空
没有人在我和它中间
也没有一只动物,或行走
云朵间的风
就这样飞翔,饮完一壶冰凉的河水
爱与恨,都留在了黑色的大地
从此都与我无关
……
他写的都是自己的心路历程,很细腻,却不追求意义,更没有想过发表,写完就丢了。
一场罕见的地震袭击了四川,许多座美丽的城市,一夜之间变成了废墟。虽远在藏区,这儿的人也明显感受到了余震,屋顶的电灯晃来晃去,藏在暗处的老鼠,也明目张胆地跑了出来。
学校接到通知,放假,是无限期地放假。到底啥时候开学,通知上没写。
老歪没有告诉任何人,就走出了山区。山里到山外,有五六十里的路程,老歪昏天黑地地走,脚心被路上的石子磕得生疼,他也没有知觉。
在山外的公路上,他搭乘了一辆运输汽车。坐在汽车上,他没有像常人那样,回头再望一眼山村。他也没有像要决绝这里似的,把眼睛闭上。他只是望着前方,眼睛像一只死鱼眼,平静,没有光彩。
前方的路被封了,司机说什么也不愿往前开了。老歪二话没说,把他的帆布背包一背,就下了车,徒步前行。他走了两天一夜,终于进入灾区,看到卡车一辆一辆地往外运尸体,那些尸体都大大地睁着眼,他的手心里不自觉地冒出了冷汗。
工厂、学校、银行、商场……所有的建筑都如蜂窝煤那样易碎。到处是人,各种肤色的搜救队。老歪加入了其中一队,随他们一起,在废墟中搜寻可能存在的生命。
在路边一座倾倒的平房里,老歪听到了微弱的求救声。“这房子里有人。”他立即向大伙吆喝道。
“不可能!”领队断然说道,“那么多支搜救队都过去了,如果有人,不会不被发现的。再说了,这是平房,对人也造成不了多大伤害,即使有人,也早就自己出来了。”
即便是这样说,领队还是侧耳细听了一会,可是什么声音都没有。
“前行。”领队发出命令。
可是,那求救声却在老歪的耳边,真切地存在着。“你们先前行吧,我再看一下。”他对领队说。
站在废墟上面,老歪又一次听到了那种声音——藏区的生活经历,让他的听觉比常人更为敏锐——他确信下面还有生命存在。队伍已经前行了很远,他无法再让他们回来。他用双手搬开砖头,搬了很久,发现了一双受到惊吓的眼睛,他仔细地看了看,竟然是一个四五岁的女孩。他下意识地把头探过去,又听到了一声稚嫩的呼救,那个女孩居然还动着。
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把压在女孩身上的楼板抬开,幸运的是,楼板压在了沙发上,并没有砸在女孩身上。他把女孩抱在怀里,带到医疗队检查是否受了伤害。女孩仿佛把他错认为自己的父亲,死死地抓住他的衣角,说什么也不肯放手。
老歪只好留下来照顾她。
或许,女孩已经意识到,地震把她的家人都带走了,她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便只有跟着老歪,做了他的女儿。无论是谁问她,她都指着老歪:“他就是我的爸爸。”
老歪哭笑不得,总不能把她送到孤儿院吧?女孩的称呼让他百口难辩。
就这样,老歪在他三十而立这年,还没有结婚,却无端地多了一个女儿。
当笑容重在女孩的脸上绽放,老歪给她洗干净、换上新衣服之后,女孩竟然异常的漂亮可爱,每天在他的身边,像一个贴心的小棉袄,爸爸长爸爸短地叫着。老歪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苟言笑,就连女儿叫她,也不会露出半点笑容。他的同学问他:“老天平白无故地赐给你一个千金,你咋就没一点儿高兴的样子?”
他说:“谁知道她是不是来折磨我的呢?得,我单身的日子看来是要结束了,以后有得罪受了。”
同学不解,他又接着解释:“我总不能一个大老爷们,带着一个小丫头过日子吧?现在她还小,还好一点,等再过几年她长大了,那就很不方便了。说不定,还会惹来闲言碎语呢。”
这是老歪的一点小心机。一旦他成了家,给女孩应该享受的父母之爱,女孩也就真的成为他贴心的小棉袄了。
其实,老歪还是在信奉着他的一个原则:人应有所敬畏。有敬畏,才会得到应有的回馈。他相信女孩就是大自然的回馈,他要继续保持这种虔诚,即便是意外所得,也不能得意,要隐忍,继续谦卑。
老歪带着女孩来到深圳,在同学的帮助下,进入报社做了一名记者。他有这方面的天赋,他对文字的感觉,对事物的锐敏,使他在记者这个职位上,得心应手。在他入职的第二个月里,一场雨使红花路人行道出现了塌方。这是一件常见的事情:每逢大雨,总会有这样或那样塌方的消息。只是,红花路前不久刚刚重新修整过,还架起了一座人行天桥,天天车水马龙人流如注。老歪感觉这件事背后大有猫腻,他以一个军人雷厉风行的作风,查阅了许多建筑方面的资料,最终认为这个塌方事件,可能是由工程质量引起,那就是这条道路还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
老歪决定追查下去。生命是平等的,他不容忍因工作错误,而造成对别的生命产生威胁,更不容许自己对这件事有所察觉却假装视而不见,最终酿成更大事故的情况发生。
毫无疑问,采访工作并不那么顺利。有人拉拢他,有人威胁他,就连介绍他进入报社的同学,也找到他,对他说:“有些事情知道了,并不一定非要报道出来。在深圳,靠的是人脉,多结识一个朋友,就多一条路,何必非要跟人家结仇呢?”
同学是为了自己好,老歪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这一点。只是,他像是钻进牛角尖,出不来了。他说:“我不会刻意与任何一人结仇的,但如果别人非要这样认为,我也毫无办法。”
听他的话茬,好像有慷慨赴义的悲壮。
老歪掌握了足够的数据,支撑他的报道。报道出来后,整座城市都掀起了轩然大波。一项造价数千万元的工程,经过层层转包、层层克扣,最终只以数百万元的成本完成施工,这样的工程质量如何确保人民的生命安全?
一系列的黑幕被揭露,多位领导被查处。老歪因此被升职加薪,荣登金牌记者行列。办公室内,同事们向他表示祝贺,他只是诡秘地一笑,走进了领导办公室。
“我申请调换岗位,希望您能考虑,把我调到编辑岗上去。”面对领导,他开门见山。
“你这是怎么啦?”领导吓了一跳,“你刚刚荣升为报社的金牌记者,怎么就想换岗了呢?要知道,许多人用几十年,也拼不到这个岗位呢!”
“天晓得我还会捅出啥样的窟窿来!”他说,“通过这段时间,我发现更适合做编辑,当然,我这也是为了孩子着想,我自己倒无所谓,但总不能让孩子也跟着我担惊受怕吧。”
他的请求理由充分,领导不好驳斥,只好应允。他转职为副刊编辑,薪水也相应地跟着降了不少。
同事们说他傻,有着高工资的活不干,偏偏要干不被人重视没有任何好处的副刊编辑。他像个没事人一样,兀自开始了朝九晚五的工作,好像他的价值并不是用工资高低来体现的。
副刊编辑是个闲职,专门编发本地作者写的散文随笔之类的小文章,每周二四六三个版面。老歪总是提前一个星期就把稿件编好,这样,他就有许多时间,用来思考、阅读、陪女儿。
同所有的副刊编辑一样,老歪身旁很快就聚集了一帮文学青年。他们常常以文学的名义,邀请老歪喝酒、打牌、桑拿、逛公园。每到这个时间,女儿就像受到了天大的委屈,噘着小嘴,满脸的不高兴。老歪明白,他的确该考虑个人的婚姻大事了,就是为了女儿,也要这样。
老同学出面帮忙,给他安排了几次相亲。每一次,他总是显得忧心忡忡。他说:“我现在都不敢给爹娘打电话了,每次,他们总是会问:什么时间带媳妇回家。人生在世,啥时间才能真正为自己而活呢?”——一场大病,使父亲豁然开朗了,儿子的路就由儿子去走,走成什么样子,是他自己的事。可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还是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抱得上孙子。
但抱怨归抱怨,老歪还是打扮得整整齐齐的,去见对方。
有那么两年多的时间,老歪常去相亲,几乎每两个星期都会相亲一次。这令我们大为不解,这么多的女孩子中间,没有一个让他满意的?
老歪说:“也不是完全这样,还是有两个在保持交往的。”
老歪说的这两个,我都见过,其中一个是我们的同事,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另一个是位中学老师,戴着一副高度近视镜,斯斯文文的。
“与她们在一起,根本就体会不到爱情的激情,她们都过于沉闷了。”老歪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几近麻木,似乎选对象这件事情,他压根儿就不愿意干。
“那这两个中间,你更倾向于哪一个?”
“半斤八两吧,谈不上倾向。她们两人给我的感觉就像鸡肋,丢又舍不得,不丢又没啥味。”
这个老歪,相亲都相出味道来了。
一天,我们正在一起打牌,一个年纪看起来二十三四岁的女孩走进来,站在一旁直勾勾地盯着老歪。他吓了一跳,问她:“你好,你有事吗?还有,我们认识吗?”
那个女孩长得真是青春。她好像刚从健身房出来,一身运动短装,暴露出她洁白的肌肤。见老歪这样问,她并不急着接话茬,反而,像观赏艺术品似的,从上至下把老歪打量了一遍。
在女孩几近挑剔的目光中,我们又打完了一把牌。洗牌间余,女孩才开始说话,她是对着老歪说的,她说:“我喜欢你,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处对象。”
这算什么事情,把我们都当成透明的了?谈情,也应该找个私人一点的地方呀!我们极为不满地盯着老歪,其实是羡慕嫉妒恨地看着他。
老歪几乎是用斜睨的眼光看了女孩一眼,继续发牌。人都说,情场失意,赌场才会得意。可老歪,一边赢着我们的钱,还一边享受着这“飞来的艳遇”。他笑着说:“哦,就这事儿呀?”
我们几乎想冲上去揍他一顿了。什么叫就这事儿呀?
女孩眼里含着泪水,反问道:“怎么了?你嫌我长得不够漂亮,还是觉得我这样直接,不够矜持?”
“都不是,”老歪把牌发完,直接捡起底牌,头也不抬,就开始理他手中的牌了,“爱情是一件很郑重的事情,怎么能在打牌的时候谈呢?”
“要不然,我们今天先玩到这儿,你先处理正事。”我们建议他。
“打牌也是很郑重的事情。”老歪说,“我开始出牌了,你们要小心了。”
女孩一听,知道跟这样的男人谈爱情是没有希望的,便反过来安慰他说:“老歪,我就不让你分心了,你们先玩牌吧。”
老歪毫不羞愧地笑了,“嗯,这样的女子才对我胃口。”
面对着这找上门来的艳遇,老歪表现出一副欠揍的模样。
虽然他看起来吊儿郎当,做事儿也总不上路,一年后,他却组建了一个温馨的三口之家,且这种温馨让我们每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都很气愤——
他的老婆,就是那位青春靓丽的健身女孩,年纪比他小十岁,还是个典型的“富二代”,父亲是本地的一位建筑开发商,身份以亿来计。她自己更是刚从海外留学归来,在一家高新技术企业任财务总监,出入都是奔驰宝马的。他的女儿,那位上天赐给他的孤儿,该读小学了,在别人都为一个学位挤破脑袋时,某位校长却主动找到老歪,说学位这是小事情,根本就不用操心……感受到父母之爱的女儿,更像个贴心小棉袄那样的知冷知热,嘴上甜甜地叫着“爸比”“妈咪”,让他们夫妻俩高兴得嘴都合不上。
这幸福而甜美的生活,让老歪感到很满足,周围的人每一问到,他会随口说道:“呵,这都是命数。”
有人会撇着嘴,说:“你有啥资格这样?你现在拥有的,哪一样是你自己挣来的?不全都是因为你有一个有钱的老婆!”
老歪说:“你这是羡慕嫉妒。不是咱的魅力,这老婆能跟着咱过?”
那人不服气,就找到他老婆,问:“老歪那吊儿郎当的样子,你到底看中了他那一点?”
“善良,正直,不随波逐流,”她又加了一句,“关键是他帅。”
那人学老歪老婆的语气说这句话时,周围的人似乎得到了心理上的平衡,态度有些暧昧地笑了,只有老歪,似乎听不出话中的玄机,依旧一副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
去年,接上级通知,报社要由事业单位改为企业,这意味着所有的岗位,都将进行新的考核,而个人的收入,则与其岗位绩效紧紧挂钩。领导找到老歪说:“你的工作以往太轻松了,现在准备重新分配些新闻版面,由你来负责,你有什么想法?”
老歪说没什么想法。他就真的担起了那些工作,啥怨言都没有。工作量一下子增加了许多,他经常加班到深夜才回到家里。不仅如此,以前上班不用打卡,实行岗位责任制,无论人在不在岗,只要把事情做完,就可以了。现在,所有人员,都得按时打卡上班,哪怕是加班到深夜,第二天仍然要依时到岗。
他的老婆看不下去了,在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时,一边为他准备宵夜,一边嘟囔道:“你们领导,真是不通人情,你入职这五年,每年都给他捧回一个全国百佳副刊的奖牌,现在工作增加了,就应该多请些人来做。”
老歪说:“现在报社改为企业了,领导也要为企业的盈利考虑,增加人手,就增加了开支。每个人,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领导也是没有办法。”
他老婆说:“既然要考虑盈利,那就好说了,明天我去找一下你们领导,让他们给你减些工作量。”
“那就不必了,现在这些工作,我还能应付过来。”老歪回答道。
第二天,他的老婆真就走进了领导办公室。她是有这个能力让领导改变想法的。同事们对此议论不已,认为老歪如果真减轻了工作量,而他又安然处之,那他真就是“吃软饭”的男人了。
老歪并不理会同事们的议论,他快速地忙碌着,他知道妻子走后,领导就会找他谈话,他要在领导找他之前,把当天的工作做完。
领导叫他时,同事们立即把目光聚集在他的脸上,他仿佛视若无睹,笑眯眯地走了进去。
领导有些哭笑不得,“你怎么从来就没有提起过,你的老婆是我们几个重要的广告客户之一?”
老歪说:“说了又能如何?毕竟,她是她,我是我,我的工作不可能由她来做的。”
“你这个人呀,真拿你没办法?工作量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你就不抱怨?”
“有啥好抱怨的?对于这次调整,同事们大多有意见,可这仍挡不住改革的步伐。我们都知道,工作就是在不断的妥协中进行的。”
“真是要被你气死了。别人抱怨可能不见得有用处,你如果抱怨,我们一定会认真考虑的。”领导说,“其实,跟你实话说了吧,我们一下子加重你这么多工作量,是别有用意的。我们希望你吃不消,跑来发牢骚,这样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把你调回记者岗位了。你不知道,一名金牌记者对报社会产生多大的影响。要不,你认真考虑一下?”
“我看没有必要了,目前的状况,我挺知足……”
老歪的工作量始终没有减少。
不就是多一点工作,经常免费加班吗?别人能够做下去,我怎么就做不下去?面对妻子的质问,老歪理直气壮地说。
一个单位,无论工作分配多么不合理,但总体工作量是确定的,一个人多干,另一人就会少干。每个人都明白,老歪的工作量如果减了下来,他们中的某个人就会增加工作量。只是,我们在暗笑老歪有些“傻”的同时,也在暗暗庆幸自己有了这么一位“傻”同事。
可是,他真的傻吗?如果他傻,又怎能一次次在不同的岗位上,取得同事们所无法企及的成绩?只是,能不让自己这么累时,仍选择了加班加点的繁重工作,这不是傻是什么?
我们发觉,老歪这个人,似乎越来越不可理解了。
老歪依旧埋头工作,有空时,依旧会同我们打牌,会同一帮文学青年聚会,逛公园,桑拿,或者侃大山。
只是,我们悄然发现,在做完所有的这些事情,他一个人休息时,他会捧着一本书阅读。在我们的报社图书室里,他出入的频率之高,更换图书的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不过,若你因此而认为老歪是一个沉默无味的男人,除了工作与阅读、该有的应酬之外,回到家里会像大部分中年男人那样,坐在沙发上,霸占着电视,却不怎么对老婆孩子讲话,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他的骨子里有一种别样的浪漫。不加班及没有应酬的时候,晚饭后他会陪着老婆、女儿到公园里散步,陪她们玩游戏、捉迷藏。
一进入阳春三月,深圳的各个角落,都开满了鲜花,空气里充斥着一种好闻的芳香。老歪就会休假一个星期,陪着妻子带着女儿,游遍深圳每一处值得去的地方。
在他编辑的副刊上,第一次出现他的作品,是一首这样的诗:
牵着她的手,我们在冰封的原野中穿过
从深圳的这端到那端,一只红蜻蜓
逗留在常青藤上
再也不希望有突然发生,不希望
一只手离开另一只手
我们向前走着,风掀起
姑娘们的裙子,奇怪的是,它
从不惊扰那只红蜻蜓
已经很久了。有些人已经远去
熟悉的木质把手,无人再来转动
我的爱人,请不要担心
那只红蜻蜓,那溢满空气的花香
会陪伴着你,带着你经历
更多不被理解的最好的事情……
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同事们因此而调侃他。每次见到他,都戏称他为“大诗人”,他依如平常,淡然一笑,便走开了。
或许,在自己负责的版面上,刊发自己的作品,多少有点以公谋私,有点让人不耻?
只是,谁都想不到,这是他唯一一次在自己的版面上发表作品。在他进入报社的第六个年头,他向领导递交了辞呈。
他离开了深圳,带着女儿,还有他的那个帆布背包走了。
他去了哪里,没人知道,报社里传出了各种各样的猜测:有的说他的妻子给他带了绿帽子,他忍受不了,只有选择离开;有的说,他本就一无所有,老婆是大户人家的千金,肯定在一起不长时间,不被甩才怪;还有的说,他一定是不甘心“吃软饭”了,离开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所有的猜测,无一例外地把矛头指向了他的妻子,把老歪看成了弱者。只有我们几个牌友,才真正了解,在他的这段婚姻中,老歪才不是弱者呢。但我们没有一个人出来为他解释,我们认为,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可不是,他悄然离去,不同任何人说一声,不是也认为没有必要吗?
两个月后,我接到了一封信,里面装有一张卡片,用一张照片制成的。照片上,老歪与一帮衣服上带着补丁的学生,在一个破旧的木头篮球架前,坐在坑洼不平的操场上。他们的脸上都带着笑容,那种笑容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我看到了他们眼睛中的清澈。照片上,有老歪的亲笔题字:本性。
卡片的背后,是手工绘制的图案,从那笨拙的笔画与颜色不一的笔迹上可以看出,这幅图案是多人共同完成的,只是,令我惊奇的是,图案上显示的却是一个温暖的三口之家!
一个念头进入脑海,我猛然间如触电一般。迅速打开电脑,登录支教网站,在上面我查到了想要的信息:老歪与他妻子的名字都赫然在列,而且是去往同一所学校,某贫困山区小学……
所有的猜测都不攻自破。领导得知此事,意欲组织人员前去探望慰问,然而,信上却没留地址。领导打电话到支教中心,对方以保护个人隐私为由,也没有透露任何有用的信息,慰问这件事,最终只好不了了之。
只是,在报社内部,老歪的故事重新流传开来,这一次的版本,充满了不少神秘与传奇色彩,虽然我们都知道,老歪所有的选择都如他在卡片上的题字一样,是出自本性,然而,对于传颂这样的故事,却乐此不疲。
[作者简介] 阿北,本名张传奇,1982年生,河南郸城县人。曾就读于中山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深圳大学作家研究生班。90年代开始诗歌写作,2009年尝试小说创作,目前,出版长篇小说《易翔的王国》《心理咨询师》,诗集《流塘·小事件》等。中短篇小说散见于《山花》《大家》《天津文学》《北方文学》等刊物。广东省作协会员,现居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