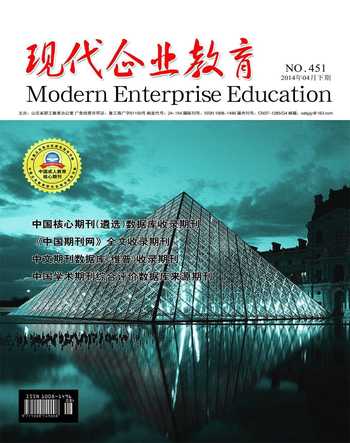解析张爱玲小说中的男性形象
纪忠璇
在张爱玲的小说世界中,涉及到了来自不同家庭,不同领域,有着不同性格的男性形象。而这些男性人物形象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活在过去的男人。第二类是活在当下,却矛盾痛苦的男人。第三类活在未来,沉沦在无妄幻想中的男人。这三类男人构成了张爱玲小说中的整个男性世界。而张爱玲也通过这些生动鲜活的形象表达了自己的男性观。可以说张爱玲的男性观概括起来是:批判中带着些许无奈的理解。
首先,在张爱玲复杂男性观的理念下,她作品中对男性形象批判解构的成分是显而易见的。第一类男人,活在过去。他们因为在已经逝去的宗法世界里有辉煌的背景,有丰厚的家产,这样的出身让他们沉溺在享受中。当时代改变,他们虽然想适应环境,但却惊慌的发现,自己根本没有立足社会的一技之长,于是他们久久地站在旧社会的舞台上,不肯下来。当他们在新社会毫无立足之地时,他们在慌乱无措的挣扎:玩弄女性,借以成为爱情中的绝对掌权者,重温大权在握的感觉。例如《金锁记》中的姜季泽,每天忙着花公帐的钱逛窑子玩妓女,妻子对于他,只是摆设。玩弄女人,是他情感的常态,甚至包括自己的嫂子。当七巧说他最近没出去胡闹是新娘子留住他时,季泽笑道:“是吗?嫂子并没有留过我,怎见得留不住?”轻佻之情溢于言表。当七巧向他倾诉自己的遭遇时,他仍旧轻蔑地笑了一声,俯下腰,伸手去捏七巧的脚道:“倒要瞧瞧你的脚现在麻不麻!”小小的一个动作细节展示了季泽浪荡公子、风流成性的本性。
此类形象还有《倾城之恋》中的白老爷、《多少恨》中的虞老先生、《小艾》中的席五老爷、《十八春》的沈啸桐和《怨女》中的姚二爷、姚三爷。
第二类男人是活在当下,却矛盾痛苦的男人。他们是一群有着良好背景或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的男人,看起来开放新潮,顺应时代,但却有着最旧式最传统的内心。中西方对撞的文化嬗变中,没落文化对人性已有的侵染和这种人性从旧文化系统中剥离出来的艰苦过程在他们身上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了。例如《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的乔琪乔,他是矛盾的化身,他既有西方的拜金主义,也有东方落寞文化中的“寄生虫”精神,他生活的理念是及时享乐。他的身世比较特殊,是混血儿,他受到的教育和中国传统式的教育不同,他似乎在生活中找不到同类,走到哪里都像异邦人一样,没有人懂他。于是他不肯好好做人,与丫环调情,在梁太太面前争宠,他说:“我没有钱,又享惯了福,天生的是个招驸马的材料。”多无耻的嘴脸!其实他考上过华南大学,他有在社会安生立命的能力,可是为了可以轻松享福,他可以贡献肉体,抛弃尊严,放弃理想。他对梁太太暗送秋波,想哄骗这位有钱的阔太宠爱他、供养他。和薇龙结婚,看上的是薇龙能赚钱供养他的能力,他无耻的把薇龙当成摇钱树,当成供他享乐的工具,等过了七八年,薇龙失去了赚钱的能力,再抓住,或干脆制造出薇龙犯奸的证据,把她一脚踢开。他视女人为玩物,能和他扯上关系的女人,他都想调戏或是染指。
此类形象还有《留情》中的米晶尧、杨先生,《心经》中的许峰仪、龚立海,《年轻的时候》中的潘汝良,《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卢兆麟,《殷宝滟送花楼会》中的罗潜之和《五四遗事》中的罗先生等等。
这类男人是张爱玲所处时代的代表,西方文明与东方腐朽的封建文化夹杂的畸形产物。这类男人很难挣脱掉他们的命运,这段乱世是时代进步所必须要付出的牺牲。
第三类男人是活在未来,沉沦在无妄幻想中的男人。之所以说活在未来,是因为他们是对现实不满的,是对未来有期待的,然而理想和期待只能在幻想中,一旦他们将幻想赴之行动了,等待他们的是足以让他们性格错乱的残酷现实。例如《多少恨》中的夏宗豫,他是药厂老板,虽事业有成但却婚姻不幸,他和妻子媒妁之言,没有感情,常年分居,过着没有爱的生活。当他喜欢上女儿的家庭教师虞家茵,他突然觉得自己重新活了过来,崭新的爱情坚定了他反抗旧式婚姻的决心,他下决心要离婚开始新生活,并且他买了新餐具放在家茵的家里,要常常在那吃饭。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最终女主人公却因难以摆脱夏宗豫已有的无爱婚姻和自己父亲厚颜无耻的纠缠,远走厦门,他们的爱情应了“上上中下下下莫欢喜总成空喜乐喜乐暗中摸索水月镜花空中楼阁”的悲哀预言。夏宗豫对旧式婚姻的挣扎也宣告结束。
这类人物还有《心经》里的龚海立,《十八春》里的沈世鈞、许叔惠、周慕瑾。
这类人物是悲剧的、值得人们同情的,开始他们的生活是有理想、有追求的,但作者用丰富的物象,烘托气氛,暗示了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也让人觉得这样的挣扎是枉然的。
综上所述,我们再看张爱玲塑造的男性形象时,是不应该孤立看的,而是要把这些形象和张爱玲所处的时代,她的人生观,尤其是男性观联系起来,才会更深刻。一方面我们看到张爱玲对男权的批判与解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张爱玲对他们的理解。其实张爱玲不是极端的女权主义者,痛恨的同时,是含有宽容和理解的。她笔下大部分都是不彻底的人物。
她笔下三类不同的男人,她的创作理念以及所侧重使用的塑造方法和所怀的感情是不同的。对于第一类活在过去的男人,代表过去时代的遗老遗少们,一如张爱玲对自己的父亲,虽然批判是严格的,但感情也是复杂的。第二类男人是活在现实,但矛盾痛苦的男人,他们找不到同类,孤独而寂寞。他们代表的是张爱玲对中西文化混杂的现代社会的批判,在这些人物中,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朴素。他们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有缺点的男人,不是以往文学作品中惊天动地的大英雄。第三类是活在未来的,对现实社会的强烈不满,对未来的憧憬支撑着他们,他们是有理想的、有挣扎、有奋斗的,但现实却是残酷的。张爱玲对他们寄予了同情和理解。
张爱玲笔下的男人更像是时代的负荷者。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东方腐朽的封建文化与西方拜金主义碰撞时对人性的摧残。这些男性形象深深的刻上了独属于那个特殊时代的迷茫、挣扎与堕落。张爱玲以批判否定的形式从哲学意义上对文本中的男性形象加以冷静的解剖,为中国人的社会进步与完善提供了一面具有“自鉴”的镜子。但张爱玲不是狂热的女权主义者,虽然在她的人生中有着堕落无能的父亲、不争气的弟弟、自私的舅舅、风流的丈夫,但她的男性观依然是温和是慈悲的。这些人物身上的坏,她是痛恨的,但她更愿意把这些归于人性、归为时代。这使得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超越了自身,成了当时特殊社会的缩影。
参考文献:
[1] 李欧梵,夏志清,刘绍铭,陈建华.重读张爱玲的[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2] 肖进.旧闻新知张爱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 仝祯.张爱玲勾描出的百丑图——浅析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J]. 池州师专学报, 2006(6): 78-81.
[4] 于青.张爱玲传[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