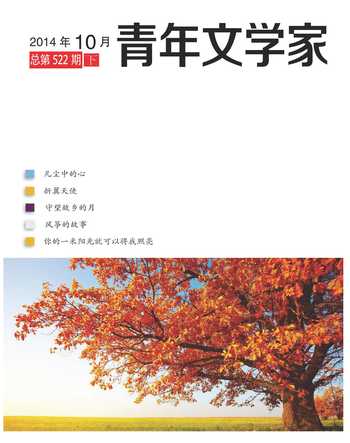论翻译审美距离在诗歌翻译中的体现
赵弘阳
摘 要:在诗歌翻译过程中,译者所不断追寻的译作是审美距离为零且能让译诗读者亦能体会到原作者当时的“意境”与“心态”,“意”与“言”的融合。当然由于文化差异和受众差异,这一目标几乎无法达成。各种不同的元素导致文学翻译中审美距离的产生,因而导致不同的审美境界。
关键词:审美距离;《无情仙女》;翻译距离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30--02
一、介绍
文学翻译过程中,出于文化环境和历史时期的差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往往会对作者的本意,即“言外之意”作出不同的阐释;为了缩短读者与原作者的审美距离,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会采取不同手段,如张若谷先生在翻译《德伯家的苔丝》过程中,采用了大量山东方言,如“不能,俺豁着死也不能这么干” ,这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等值,缩短了审美距离,也突出了原作的地域性。
二、翻译距离论
罗兰·巴特在《写作的零度》(1953)中首次提出了“零度写作”这一概念巴特认为语言与形式都是呈现概念上的常规,而不完全是创意的表现。形式,或者是巴特所称的“书写”是个体选择以独特的方式操作形式上的常规来达到他所想达到的效果,这是一个独特且创造性的行动。把这一说法转移到文学翻译中看来,“零度翻译”,译者要以一种高度理性,趋于零度无感的态度对待翻译,将内心的观点和主观性降至零度。
三、《无情仙女》
《无情仙女》(“La Belle Dame Sans Merci”)是浪漫派诗人济慈的代表作品之一,目前较为普遍常见的有查良铮,屠岸的译文,本文将就查良铮的译文作翻译审美距离方面的解读。
四、审美距离解读
(一)诗歌形式与内容
(1)诗歌形式
济慈的原作采用了歌谣诗节,即由多段四行诗组成,尾韵押ABCB,五音步抑扬格和四音步抑扬格交错出现,奇数行有四个重读音节,偶数行有三个,给读者一种缓慢递进,抒情充足之感。而在诗歌翻译过程中,往往出于保留内容的需要,许多韵律无法保留,在查的译本中,ABCB的尾韵已丢失,且采取了长短迭句交替出现来力求重现交替出现的五音步和四音步。以第一诗节为例:
“Oh what can ail thee, knight-at-arms.
Alone and palely loitering?
The sedge has withered from the lake.
And no birds sing”
查译作“骑士啊 您为何哀伤
孤独彷徨 悲伤烦扰,
湖中之草都已枯败,
鸟儿 也匿声了”
在此,我们不难发现原诗中的“loitering”和“sing”的押韵,由于汉语和英语的不同,在译文中无法展现出来,造成了一定审美潜质的缺失和审美距离的拉长。同时,译者也做了一定调整,尽量达到押韵效果,如在
“She found me roots of relish sweet
And honey wild, and manna dew
And sure in language strange she said——
“I love thee true.””这一诗节,查译作
“她为我采集甜美草根
吗哪甘露、野生蜂蜜
她所说言语 也甚奇异——
“我爱你,全心全意””
译者为了在译作中达到“蜜”和“意”的押韵效果,在翻译过程中调换了“honey wild”和“manna dew”的顺序,这样虽破坏了两种意向的层次和次序感,感保留了押韵,符合中国读者对诗歌琅琅上口的要求。
(2)诗歌内容
“无情的妖女”以歌谣的形式再现了一个不幸凡人的古老传说,诗中的主人公抵挡不住妖女的诱惑,最后变成了妖女的俘囚。透过诗人对骑士和“妖女”的情感经历的再现,我们可以管窥诗人的内心世界,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济慈是一个透过世俗世界的感官体验,升华精神至崇高境界的诗人。对于西方读者而言,他们不难解读出济慈描写的梦境对于骑士来讲就是仙境,是伊甸园的再现。那儿有青绿的草坪、美味的果子、特意给“我”配备的“女人”。她向“我”表示爱意,给“我”采集食品,又用奇异的语言哄“我”,从“仿佛真心爱我”到“说是真心爱我”。“我”抵挡不住诱惑,就迫不及待地吃了这看似免费得到的“禁果”,“我”暗自庆幸自己的佳运,深深陶醉其中。“我”装扮她,带她在骏马上,她给“我”唱歌,歌声使人神魂颠倒,以至于“我”整日什么都不做,享受着“乐园”带来的“快乐和温馨”。当诗中的骑士正处于感受“妖女”美的忘我状态中,读者也和骑士同醉的时候,浪漫故事却出现了突变:“伊甸园”失去了, “我”做了一个惊奇的噩梦。在梦中“我”看到了形似骷髅的国王、王子和无数的骑士。此时“我”才恍然大悟,明白自己已经做了“妖女”的俘囚。騎士作为欧洲中世纪时期的传统意向,具有基督教信仰,勇敢善战,是中世纪基督教伦理的卫道士。所以,济慈“无情的妖女”使人感受到一种宗教情怀的萦绕以及折射出宗教神秘主义思想的光彩。而这一深层意象,在翻译的传递过程中,几乎对于一般中国读者说来,这一审美客体无法通过读者的审美经验转化为审美对象,反而会进入另一番“化境”,有一种人鬼故事,捎带恐怖色彩的风味。
(二)审美距离的影响因素
(1)物与言的先后之离
诗人在初次创作过程中,所感觉之景与其创作距离最为贴近,也就是说,是一种“随景宛转”,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只能通过原作者笔下之言,相隔历史和空间去再度体会当时之景色,便是“随言宛转”,如是审美旨趣便不可避免存在距离。
在本诗的译作中,查将
“I set her on my pacing steed
And nothing else saw all day long
For sidelong would she bend, and sing
A faery's song”
译作“我抱她上马
一整日啊 再看不到其他
眼里只见 她那侧身的模样
耳中只闻 她唱的妖灵歌谣”
此处,译者将“A faery's song”译作“妖灵歌谣”,“faery”原义即为“仙女的,幻想的”,并无“妖魅”之含義,此处译者应是根据自身的理解,为译文加入了“妖灵歌谣”这层含义,实则当时骑士沦入冷酷仙女温柔乡之中,并不会觉得歌声冷酷无情,此处翻译的“化境”由于译者和原作者所观之景,所想之念不同,故济慈之“物”与查之“言”出现一定偏离。
(2)近譬与远譬的远近之离
“由于原作者和译者采取不同的取材方式,原诗中被审美主体化了的物象或意象,以另一种语言形态呈现在译文读者的眼前时,已因为隔着青山千万重而变得陌生与遥远了。”(刘,p60)译者努力想将原作者的“近譬” 转化为读者的“近譬”,但此时对于原作者而言,就成了“远譬”
在
“She found me roots of relish sweet
And honey wild, and manna dew
And sure in language strange she said ——
“I love thee true.””这一诗节,查译作
“她为我采集甜美草根
吗哪甘露、野生蜂蜜
她所说言语 也甚奇异——
“我爱你,全心全意””
Manna一词,来自《圣经》故事所述,是古以色列人经过荒野所得的天赐食物,也就是中文中所说“天赐甘霖”之意,此处译者将其处理为“吗哪甘露”,对不熟悉西方圣经故事的中国读者来说,便是一种“远譬”,而若处理为“霖汁甘露”,对原作者而言,便成为了“远譬”。
五、结语
在翻译过程中,审美距离最小化是译者努力的目标,而不论在英诗汉译或是汉诗英译的过程中,都存在影响审美潜质的因素的存在,进而使得在读者眼中,审美客体无法转为审美对象。《冷酷仙女》作为经典英国浪漫派诗歌,在中国拥有大量读者,爱好者,研究者,通过翻译距离论的研究从而达到译作的最佳传递和表达有着长远意义。
参考文献:
[1]刘华文. 诗歌翻译的审美距离 [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33(3): 59-65
[2]罗兰·巴尔特. 写作的零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3]马蓉. 翻译审美与佳作评析[M].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
[4]马月兰. 从“无情的妖女”看济慈的宗教观[J]. 世界文学评论, 2010, (3): 3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