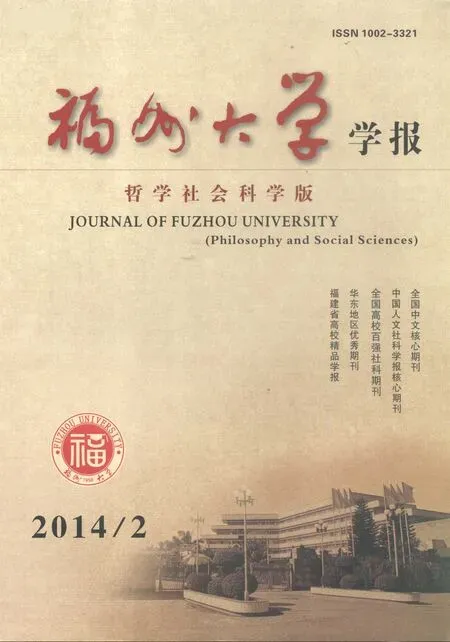题画词与书画传播
王晓骊
(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1620)
题画词一般是指题写在画幅之上(既包括画面,也包括画面之外的拖尾、诗堂、引首等位置)的词,可以看作绘画题跋的一种特殊形式。所谓题跋泛指题写于书画文献前后的文字,标于前者称题,系于后者为跋。题跋以诗文为主,但是随着词的文人化,以词为题跋也渐成风气。《全宋词》收录160余首,《全金元词》收130余首,《全明词》和《全明词补编》收近600首,清代题画词创作更为繁盛,仅据《全清词钞》等清词选本所选题画词就多达2000余首[1],其中不少是题写于画上的。题画词作为一种“副文本”[2],与绘画作品一起形成了以画为主,书、画、词三者合一的艺术整体,绘画传播相应成为三者并行的综合传播行为,由此形成更为丰富的传播内容和传播路径。从另一角度来看,题画词又是书画传播的产物,其产生和发展都受书画传播需求的推动,传播风气的变化直接引发了题画词的演变。
一、图文并传:题画词在书画传播中的作用
由于词具有更为严格的体式和韵律的规定,相较于诗文,以词为题跋通常难度更大。同时词婉约唯美的艺术风格又能为文人画增添诗文所无法体现的情韵,因此,优秀的题画词往往能够提高绘画作品的知名度,吸引更多的传播者。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题画词作为绘画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也为书画传播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可能。
从现存文献来看,词与绘画结缘最早当在中唐。据《太平广记》卷二十七引沈汾《续仙传》:“玄真子姓张,名志和……鲁国公颜真卿与之友善。真卿为湖州刺史,与门客会饮,乃唱和为《渔父》词,其首唱即志和之词,曰:(词略)。真卿与陆鸿渐、徐志衡、李成矩,共和二十五首,递相夸赏。而志和命丹青剪素,写景天词,须臾五本。花木禽鱼,山水景像,奇绝踪迹,今古无伦……今犹有宝传其画在人间。”[3]张志和并不以画而名,但是其题写于画上的《渔父》词却使他的画“宝传人间”。可见,在题画词的萌芽时期,词画结合的形式就有助于绘画作品的传播。又据《宣和画谱》卷八,南唐卫贤“尝作《春江图》,李氏(煜)为题《渔父》词于其上”[4]。李煜是南唐国主,又是著名的词人,且工于书画,他题写于画上的《渔父》词,使卫贤《春江图》成为较早因词、书、画合一而著称的艺术作品。《宣和画谱》著录其画二十五件,而详记此画,必须承认,李煜的题词是其重要因素。中唐乃至五代,词作为新兴的文学样式刚刚在文人阶层盛行。这种新鲜活泼的形式进入绘画领域,它引起的审美惊奇对于绘画传播势有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时期的题画词虽然数量很少,但却影响深远。以《渔父》词或《渔歌子》题渔父图在后代几乎成为定式,如元代赵孟頫妻管道昇水墨短卷《渔父图》,上有管、赵二人所书五首《渔父》词;吴镇《渔父图长卷》上录《渔父》词十六首;明代周臣《渔乐图卷》后有文彭录五代李珣《渔歌子》四首;清代纳兰性德以《渔父》词题谢彬《枫江渔父图》等,由此可见张志和、李煜所开创的词画结合的艺术形式,不仅扩大了原画的传播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渔父图在后代的创作模式。
宋代题画词在书画传播中承担的作用愈见显著。如南宋扬无咎[5]《四梅图》上因题有画家所作《柳梢青》四首而为时人所盛赞。南宋刘克庄《跋杨补之词画》就有这样的评论:
艺之至者不两能,善画者不必妙词翰,有词翰者类不工画。前代惟王维、郑虔兼之。维以词客画师自命,虔有“三绝”之名。本朝文湖州、李龙眠亦然。过江后称杨补之,其墨梅擅天下,身后寸纸千金。所制梅词《柳梢青》十阕,不减花间、香奁及小晏、秦郎得意之作。词画既妙,而行书姿媚精绝,可与陈简斋相伯仲。顷见碑本已堪宝玩,况其迹乎?孟芳此卷宜题曰“逃禅三绝”。[6]
由此可见,扬无咎的墨梅之所以“寸纸千金”,很大程度是由其“词画既妙,而行书姿媚精绝”的“逃禅三绝”而决定的。
如果说单篇题画词的创作,其影响是有限的,那么围绕题画词出现的唱和之风,就能在最大范围加强其传播效果。扬补之的《四梅图》在后代的传播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柳梢青》的唱和。据《郁氏书画题跋记》卷一记载,元代柯九思即有四首和词,到了明代,唱和者更多:“逃禅梅子四词脍炙人口,宋元和之者已多,国朝名公追和不下数十人。”[7]《郁氏书画题跋记》卷一即载有文徵明、文嘉和彭年所和各四首《柳梢青》。直到近代,词人画家吴湖帆还作有《柳梢青·扬补之梅花卷即次逃禅韵二首》[8]。必须承认,扬无咎的题画词及其唱和大大提高了这幅画的地位和影响,使之成为中国花鸟画历史上不可忽视的作品之一。
类似的例子在宋代以后并不鲜见,如元代陆行直《碧梧苍石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画上所题张炎《清平乐》词也引发了广泛唱和。据《全金元词》著录,共有陆行直、陆留、王铉、元卿、叶衡、卫德嘉、施可道、曹方父、卫德辰、赵由儁、陆承孙、徐再思、竹月道人、郝贞、刘则梅等十五人参与创作。清代曹尔堪为樊圻《柳村渔乐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题《满江红》词,据《词苑丛谈》卷九:“柳村在恒山之南,梁冶湄使君读书其中,属金陵樊圻画《柳村渔乐图》……曹顾庵学士题《满江红》云:……和者数十家,於是赵郡自雕桥柏棠村而外,无弗知有柳村矣。”[9]这些都是画因词而闻名的典型例子。题画词的唱和使绘画作品的流传超出了书画领域,即便是不善绘画的文人也能以自己的创作行为参与其中,可见,题画词的存在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传播和接受方式。
这种题画词唱和又常常和文人结社活动相关。明清两代文人结社之风盛行,文人雅集常常以词会友,“吾州里诸君子,行敦道义,艺崇风雅。凡燕集过从,以词倡酬,或用韵,或限韵,恒循击钵刻烛故事,而相角不相下,骚坛称盛焉”[10];又辅之以书画鉴赏,“借了以文会友的题目,而集团生活却只是文酒之宴,声伎之好;品书评画,此唱彼酬,成为一时风气”[11]。一幅“书、画、词”三绝的书画作品可以让结社文人用各种形式参与创作,而对题画词的唱和无疑是参与人数最多的活动。如清代戈载《秋宵吟》词小序曰:“孟秋中旬九日,董琢卿集广川书屋,出示萚石老人《秋叶图》,写温飞卿‘一叶叶,一声声’词意,索座客题咏。”[12]再如咸丰年间,苏州词人潘钟瑞曾集嬉春吟社和秋社,都是以绘画为题材的文人词唱和,如其《香禅词》收《疏影》一词,其小序云:“泖生属题《古红梅阁图》,因忆戊午岁,同人访小市桥遗址,嬉春吟社中以此命题。”从这些词序来看,这些词社集会都是以题画词为核心的创作及唱和活动。
同时,由书画传播引发的文人词唱和,并非表现为由书画而词的单向影响过程,很多唱和活动也伴随着新的书画创作,是书、画、词合而为一的综合艺术行为。典型的例子有明代吴中文人围绕倪瓒《江南春》词的唱和活动。吴门画家领袖文徵明不仅参与了弘治十一年(1498)和嘉靖九年(1530)的两次唱和,而且他还以此为题材创作了多幅山水画,创作时间分别是嘉靖庚寅(1530)、嘉靖壬辰(1532)、嘉靖癸巳(1533)、嘉靖甲辰(1544)、嘉靖丁未(1547)和嘉靖丙辰(1556)[13]。在作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的《江南春图》上,文徵明又题写了作于弘治十一年(1498)和嘉靖九年(1530)的两组《和江南春词》。这些词、画的创作时间相隔四十六年之久,而文徵明将之录于同一幅作品之上,可见文徵明对倪瓒《江南春》的接受是书画与文学二位一体的。除了文徵明外,唐寅、仇英、居节、文嘉、钱谷等都曾作《江南春图》,其中除仇英、居节外都参加了《江南春》词的唱和,而仇英虽未有和作,但其《江南春图》卷上题写了十位名家的《和江南春词》,亦足证当时《江南春》词唱和活动与书画创作和传播的密切关系。
明人对宋代扬无咎《柳梢青》词的唱和,也存在类似的情况。现存文徵明《梅花四段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画上题有四首《柳梢青》词。[14]据画上题跋:“补之梅花,固无容赞,其词亦清逸。此四段尤余所珍爱。旧藏吴中,屡得见之,今不知流落何处。闲窗无事,遂仿佛写其遗意。每种并录俚语于左,以志欣仰之私,非敢云步后尘也。”可见其画其词均为追步扬补之的拟作及和词。这种书、词、画结合的传播和接受方式是中国古代艺术传播中的特殊现象,殊为珍贵,值得重视。
由此可见,题画词大大丰富了绘画元素,从而为其传播提供了更为多元的方式和更为广泛的接受群体。尤其是明代以后,文人结社带来的题画词唱和,以及词画结合的创新型接受方式,都让绘画作品的传播突破了单一的图像文本流传,呈现出书、画、词三者融合的局面。
二、书画传播:题画词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推力
在文人词发展史上,题画词虽然不能与艳情、咏物、山水等传统题材相比,但在数量上既呈渐增趋势,在内容和形式上又形成了与其他题材有所不同的特殊性,从而成为文人词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书画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绘画的角度而言,题画词又是题跋的一种特殊形式。题跋作为文字手段和语言艺术的介入,是为了弥补绘画在表意方面的不足,正如清代方薰《山静居画论》所谓:“高情逸思,画之不足,题以发之”,一方面增加其承载的信息量,另一方面保证画家意图在传播中不被误解。由此可见,传播是题跋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推力。题画词的产生也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传播的需求,而传播带来的附加意义,又促使题画词形成相对独立的艺术特征,从而成为特殊的文人词题材。
宋代题画词的产生,大多与绘画作品的传播有关。其中有的是由画家所作,与自己的绘画作品一起赠送给友人,如张炎《浣溪沙·写〈墨梅〉二纸寄心传并题其上》、《浪淘沙·作〈墨水仙〉寄张伯雨》等。而前文所述扬无咎《柳梢青》四词,也属于这一类型:
范端伯要余画梅四枝:一未开、一欲开、一盛开、一将残,仍各赋词一首。画可信笔,词难命意,却之不从,勉徇其请。予旧有《柳梢青》十首,亦因梅所作,今再用此声调,盖近时喜唱此曲故也。端伯奕世勋臣之家,了无膏梁气味,而胸次洒落,笔端敏捷,观其好尚如许,不问可知其人也。要须亦作四篇,共夸此画,庶几衰朽之人,托以俱不泯耳。[15]
可见,扬补之作词的缘由是“勉徇其请”,内容是“共夸此画”,有着明确的传播目的。有的则由画作的观赏者所作,如吴文英《惠兰芳引·赋藏一家吴郡王画兰》、周密《夷则商国香慢·赋子固〈凌波图〉》、张炎《清平乐·题处梅家藏所南翁画兰》等。仅从词题和词序就可看出,这些词的创作与绘画传播的密切关系。
唐宋时期的题画词大多有以虚为实的特点,即把绘画形象当作实景来描写。词人如同置身于真山真水,面对的是真实的花鸟山石,强调是人在画里的仿真效果。扬无咎《柳梢青》、张炎《浪淘沙·题陈汝朝〈百鹭图卷〉》、《祝英台近·题陆壶天〈水墨兰石〉》、《临江仙·作〈墨水仙〉为处梅吟边清玩》等词,都有紧扣画面,以摹物为主的特点,与一般咏物词并无区别;而张元干的《念奴娇·题徐明叔〈海月吟笛图〉》、《渔家傲·题玄真子图》、张炎《甘州·题戚五云〈云山图〉》等则以写景为主,并抒发隐逸之想,沿用的是宋代山水词的结构和手法。这都说明宋代题画词还只能看作是咏物词或山水词的一种特殊形式,并没有成为独立的文人词题材。
题画词的对象不仅是画面所呈现的形象,也是凝结着画家个人创造的艺术作品。从传播角度而言,后者更为重要。因为从本质上来说,任何传播行为都是一种人际交往行为,其目的为了达到与他人的一致,获得他人的认可。画家的创作不管着重于表达情感心志,还是体现艺术才华,都有被他人认可的心理预期,也就是说都或多或少有传播的动机。从创作者角度而言,题画词是用来表达自我的文字工具,提醒接受者画家的存在是题画词的重要作用;从接受者的角度而言,如果将绘画形象或场景完全等同于现实,其实是对画家艺术再创造的否定,这种忽视画家的做法明显不符合书画传播中的交往目的。因此,随着书画传播的日益频繁,从元代开始,题画词开始关注画家及画作本身。如张翥《疏影·王元章墨梅图》:
山阴赋客。怪几番睡起,窗影生白。缥缈仙姝,飞下瑶台,淡伫东风颜色。微霜恰护朦胧月,更漠漠、暝烟低隔。恨翠禽、啼处惊残,一夜梦云无迹。 惟有龙煤解染,数枝入画里,如印溪碧。老树枯苔,玉晕冰圈,满幅寒香狼藉。墨池雪岭春长好,悄不管、小楼横笛。怕有人、误认真花,欲点晓来妆额。
王元章即元代画家王冕,善墨梅。张翥的这首词与前代题梅花图词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词人并没有将画梅当作真梅来描写。词作开篇即从画家入手,王冕曾隐居山阴(今浙江绍兴)九里山,故称之为“山阴赋客”。又据王冕《梅谱》自述“月夜未寝,见疏影横于其纸窗,萧然可爱,遂以笔戏摹其影”,《疏影》词上阕“怪几番睡起”以下,所写即为画家夜半睡起,见疏影横窗的情景。下阕着重描写画中之梅,过片承上启下,因爱梅影,所以写入画中。“老树枯苔,玉晕冰圈,满幅寒香狼藉”三句,是对王冕梅图艺术特色的概括。王冕画梅,老干苍劲如铁,圈墨为花,在构图上又变宋元的疏梅为密梅,词人运用联想和通感的修辞手法,从繁枝密花想像寒香扑鼻,既丰富了梅花的形象,又委婉地赞美画作已达到神似的地步。词作最后反用“梅花妆”的典故,极言画梅之逼真。由此可见,词人着重描写的是画家及其画艺,紧扣的是墨梅绘画形象的艺术特征,而不是物理特征。
词人的描写视角也发生了从画里走向画外的显著变化,开始以主体的身份对绘画作品进行描绘或评价。比如郑燮《一剪梅·题兰竹石图》:
几枝修竹几枝兰。不畏春残,不怕秋寒。飘飘远在碧云端。云里湘山,梦里巫山。 画工老兴未全删,笔也清闲,墨也斓斑。借君莫作图画看,文里机关,字里机关。
上阕描写画面形象和意境,不乏从画面延伸开来的想像,让人有身临其境的感受。下阕则以画家的身份自述绘画的特点和创作的用意,就完全是人在画外的视角了。而即使是借画抒情的题画词也往往会在词中点明吟咏对象的绘画特征,如清代陈维崧《沁园春·题徐渭文〈钟山梅花图〉》,咏史怀古,在章法结构和情感内涵上,与周邦彦《西河·金陵怀古》非常相似。但词作最后数句,却点明了这是一首题画词。“寻去疑无,看来似梦,一幅生绡泪写成”是从画家的角度揭示此画浸润的浓厚的家国情感;而“携此卷,伴水天闲话,江海余生”则是从自己作为观赏者的角度表达对这幅画的珍视之情。类似的破题之笔成为元代以后题画词的常见写法,如元代王德琏《清平乐·题黄公望〈丹霞玉树图〉》之“画出洞天清晓”、明代高启《水龙吟·题〈朱竹图卷〉》之“细看来、不是天工,却是那春风笔”、明末清初曹溶《浪淘沙·题〈收纶濯足图〉》之“欲展丝纶还有待,人在图中”、近代吴梅《清平乐·题郑所南画兰》之“千古伤心留一纸,认取南朝天水”等,都以各种手法提示接受者其题咏对象的绘画性质。
词人常常会在题画词中表达自己对绘画作品内涵意义的解读。如宋末遗民郑思肖画兰,往往构图简洁,笔墨舒展,寄托了对故国的哀悼之情和不事异朝的决心。宋末张炎有两首《清平乐》题郑思肖画兰,其主旨都在于点明画家的寄托之意。张炎的这两首题画词深刻影响了郑思肖兰花图在后代的接受,如民国著名词人吴梅、朱孝臧作《清平乐》和张炎词,都是从画家的寄托之意着眼的,如吴梅词云:“骚魂呼起,招得灵均鬼。千古伤心留一纸,认取南朝天水。北风吹散繁华,高丘但有残花。花是托根无地,人还浪迹无家。”这首词题写于《国香图卷》拖尾,是吴梅应收藏者吴湖帆的邀请所作题画词。[16]词人将画家比作屈原,歌颂了郑思肖的拳拳爱国之心,同时也寄予了自己的家愁国恨,是一首借古抒怀的词作,但其情感基调却来自于张炎原词。可见,张炎题画词对郑思肖画兰深意的解读得到了后人的一致认可。
也有着重于形式意义解读的题画词,如吴湖帆《鹧鸪天·题峒关蒲雪图》:
唐人画几无真迹,绢八百年将失魄。幸有峒关蒲雪图,香光传写杨升笔。 谩施朱粉堆金碧,枫叶芦花秋瑟瑟。正恐天昏地黑间,霎时锦绣江山出。
吴湖帆有慨于“唐人画派,凡有清三百余年来无问津者”(《〈峒关蒲雪图〉跋》)的画坛风气,借词作表现自己的艺术主张,评价唐代绘画的历史地位,同时也批评了当时画坛盲目仿效石涛的风气。在传播过程中,各类接受者或赏其笔墨,或叹其用心,但都不能忽视这首题画词所阐明的形式意义。
作为绘画作品的一部分,题画词不是作为独立文本被传播和接受的,它同时承担着书画传播的功能,这从根本上改变了题画词的性质,带来题咏对象、描写视角和表现内容的转变,从而体现出与咏物、山水类词作的不同艺术特征。
三、酬赠与收藏:题画词异化的传播诱因
绘画作为传播载体,承载的可以是作者的思想情感,也可以是作品的笔墨意趣,对作品内容和形式意义的解读是传播的基本目的。同时,传播行为又带来了作品以外的附加意义,书画传播也可能是无关作品意义的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的人际交往,甚至可能是一种商品交易。赠予、收藏、交换和购买等传播环节的日益繁杂,再加上传播目的的多重性,这些既拓展了题画词的内容和功能,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题画词的异化。
在书画赠予行为中,画家常借题画词来表达自己的志向,抒发彼此的友情,从而达到沟通情感的作用。如清代戴本孝的《晓窗梅影图上》题有《菩萨蛮》一首,词云:“晓窗抱砚浴寒碧,萧森古树山堂寂。终日闭云萝,尝闻人浩歌。 峰欹阁半倚,梅影松声里。知为卧游来,芙蓉天外开。”词作虽然也紧扣画面进行了描述,但更多地是表达自己隐居之乐。同时,根据画上题跋,这首词是为其道友所作,所以词的结尾两句表现自己对朋友的欢迎。词作由己及人,既点明了此画此词都是友朋之间的酬赠之作,同时也体现出性爱自然的共同人生观。受赠者有时也会以题画词回应,如元末邵亨贞《摸鱼子·题王德琏山居图》、《贺新郎·题王德琏水邨卷》两首,将画家比作得道升天的刘安和携西子隐居的范蠡,包含了对画家的揄扬;再比如近代向迪琮《浣溪沙·题吴湖帆〈双兔图〉》从籍贯、家世、名声、画技等各个方面盛赞画家。也有题画词与绘画一起作为酬赠之物的例子,如明代沈周《山水图》为朋友祝淇的九十大寿而作,文徵明题写于画上的《鹊桥仙》词也同样以祝寿为内容,是应酬交往词的典型。此外,还有记录画坛佳话的,如吴湖帆《菩萨蛮·题陆抑非〈双飞图〉》:“东坡文友张先两,吴兴洛下疑相向。今道姓名齐,争传陆一飞。 西湖双燕语,桃李春风弄。佳话二难并,画坛分擅名。”据画上题跋可知,这幅画是常熟陆抑非(字一飞)巧遇余姚陆一飞后所作,吴湖帆此词既记录了此次巧遇和绘画的缘由,同时也对这两位同姓同名的后辈画家进行了评价和揄扬。这些题画词关注的重点是书画传播中的交往应酬行为,它们和绘画作品一起成为文人社交的中介。由书画和文学作为媒介,这些交往显得高雅不俗,富有艺术情趣。
随着书画收藏之风的盛行,对绘画传播过程的记录和考订,也成为题画词的重要内容,题画词由此形成了考据化、学术化的发展倾向。这一倾向在清末民初尤为显著,其中又以吴湖帆的题画词创作最为典型。吴湖帆是著名的书画家和文物收藏鉴赏家,其“梅景书屋”所藏极富,据不完全统计,仅书画就有五百多件。[17]他也长于作词,受叶恭绰影响颇深,后又师从吴梅。吴湖帆因此创作了不少有关书画收藏的题画词,其词集《佞宋词痕》第二卷所收大部分都与书画藏品有关。如《锦缠道·黄子久〈富春山居图〉残卷》:
大岭横云,七里浅泷流露。指严陵、钓台危据。小舟江上盟鸥鹭。醉惹痴翁,健笔名山赋。
溯前朝六家(沈石田、樊舜举、谈思重、董玄宰、吴澈如及天籁堂),几经珍护。诧荆溪、化情尘土。叹石渠、清秘深宫妒。剩山缘分,惟我天相许。[18]
词上阕追溯黄公望创作《富春山居图》的情形,为历代题画词所常见。而下阕则叙述这幅画的收藏源流。“溯前朝六家”句是指明代收藏《富春山居图》的六家:沈周、樊舜举、谈志伊、董其昌、吴志正和天籁堂。“诧荆溪、化情尘土”句,说的是此图收藏过程中的一段惊险历程。荆溪即宜兴,《富春山居图》曾为宜兴收藏家吴洪裕所得,吴爱逾性命,临终前竟要将此焚毁殉葬。后来虽从火中救出,但已被烧成一大一小两段,大的被称为《无用师卷》,小的则称为《剩山图》。“叹石渠、清秘深宫妒”是指《无用师卷》为乾隆所得,被收入《石渠宝笈三编》。而《剩山图》则辗转于诸收藏家之手,直到抗战时期为吴湖帆所得。下阕以三十余字的篇幅记录了此图自明代以来曲折传奇的传播经历,体现出以考据为主的特点。
除吴湖帆外,当时词家,如吴梅、朱孝臧、夏敬观、赵尊岳等人都有考据词作。如吴湖帆所藏宋刻《梅花喜神谱》上就留存了19位词人题写的22首词,其中不少都以记录递藏源流为内容,如吴梅所题《暗香》词:
桂堂故迹,是雪岩剩稿,苕川骚笔。(伯仁字器之,号雪岩,苕川人。此书为景定辛酉金华双桂堂本。)画取冷香,妆点孤山好春色。闲里功夫自遣,休重忆、冰天消息。(伯仁自序云,以闲功夫作闲事业,语颇沉痛。)但试看、数点幽芬,留得此瑶册。 南国,富载籍,算佞宋艺芸,几度珍惜。(旧为荛圃、阆源藏本,后流转归滂喜斋。)百窗巷陌,鱼米长安佐清癖。(吾乡文征仲旧藏此书。百窗楼在高师巷。后由五柳居人转赠某邸,得京米一挑、鱼肉一车,一时长安传为佳话。)还我吴中掌故,应付与、眉楼吟席。正论古,谁唤起、马塍倦客。(伯仁寓西马塍在嘉熙二三年间。)[19]
《梅花喜神谱》的流传颇具传奇性,据黄丕烈册前题诗及注,此谱于清初曾经苏州五柳居陶氏收藏,后归京师某王爷,获京米十挑,鱼肉一车。[20]后归黄丕烈,此后经苏州艺芸书舍汪士钟、文登青棠红豆庐于昌遂、苏州滂喜斋潘祖荫辗转收藏,于民国十年(1921)归吴湖帆。吴梅词不仅详载此谱从南宋到民国的流传过程,还以词间注的形式标明典故出处,可谓学人词的典型。
以词来记录书画的流传过程,是文人词在书画传播影响下衍生出的新内容。对这类词的评价,诸家看法不一,或以为有开辟之功,如冒广生:“几使明诚《金石录》与《漱玉词》合而为一,此真能为词家日辟百里者”;或以为非词家所应有,如汪东谓“别创规格,虽有佳者,疑不足以示范”[21]。作为文人词发展的尝试,这带来了词题材和风格的开拓,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然而词从宋末以来,倚声的特点日益消亡,而其赖以自立于诗歌之外的特点除了长短句的体式外,主要在于深幽委婉的抒情特征。冒广生和汪东的分歧正在于对文人词发展道路的不同预期。
事实上,交往酬酢向来被视为文人词发展的不良倾向,王国维对南宋词“羔雁之具”的批评即可见一斑。而在书画传播的影响下,这却成为题画词的重要功能和特征。如果单从文学角度而言,这几乎可以视为题画词的整体缺陷。但如果从更为宽广的视角来看,题画词介入书画传播,却推动了文人画文学、书法、绘画三者合一的审美特征在创作、传播和接受各个层面的实现。对题画词艺术性的评价,也许更应考虑其词与题跋的双重文体性质,将之放置于文学和书画并存的艺术整体空间之中来考察。
注释:
[1]刘继才:《中国题画诗发展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77页。
[2]副文本是指围绕在作品文本周围的元素,如标题、副标题、序、跋、题词、插图、图画、封面等。参见[法]弗兰克·埃夫拉尔:《杂文与文学》,谈 佳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1页。
[3]李 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80页。
[4]俞剑华注译:《宣和画谱》,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191页。
[5]扬无咎,亦作杨无咎。无咎为汉代扬雄之后,故其姓当作“扬”,参见唐圭璋:《读词札记》,《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3期;又有云“杨扬”同姓,而扬无咎之“扬”姓为徽宗所改者,《宋代画家姓氏籍贯考略》,《江西历史文物》1987年第1期。
[6]曾枣庄、刘 琳:《全宋文》第329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406页。
[7][15]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卷一,清辛亥(1911)八月顺德邓氏依旧抄本校印。
[8][18]吴湖帆:《佞宋词痕》卷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9]王百里:《〈词苑丛谈〉校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557页。
[10]陈如纶:《二馀词序》,赵尊岳:《明词汇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8页。
[11]郭绍虞:《明代的文人集团》,《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526页。
[12]黄燮清:《国朝词综续编》卷十,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
[13]韩雪岩:《文徵明〈江南春图〉》,《中华文化画报》2010年第4期。
[14]文徵明画上所题四首《柳梢青》词,当为文徵明之子文嘉所作,而文徵明所和则另有四首。参见《郁氏书画题跋记》卷一《宋杨无咎补之画梅四帧》“文徵明和”、“文嘉休承和”条。
[16]陈福康:《〈清词三百首〉的误收及其他》,《中华读书报》2001年4月11日,第3版。
[17]顾海音、佘彦焱:《吴湖帆的艺术世界》,上海:文汇出版社,2004年,第186页。
[19]宋景定本《梅花喜神谱》今藏上海博物馆。词录自于柳向春:《南宋宋器之〈梅花喜神谱〉年谱》,《版本目录学研究》第三辑,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第100页。
[20]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第324页。
[21]吴湖帆:《佞宋词痕》卷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