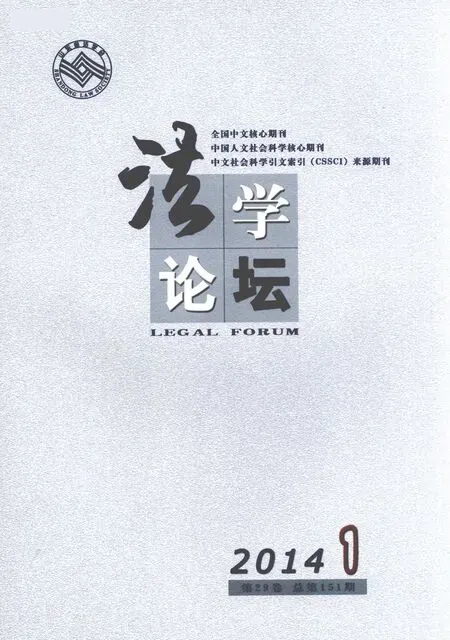在“规范拘束”与“个案正义”之间——论法教义学视野下的价值判断
孙海波
(北京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1)
在“规范拘束”与“个案正义”之间——论法教义学视野下的价值判断
孙海波
(北京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1)
在概念法学的乌托邦被破除之后,法官如何做到既受“规范拘束”又能兼顾“个案正义”,一直以来成了法学方法论上的一个难解之谜。疑难案件的频发和社科法学的异军突起,使得法教义学陷入了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由于“依法裁判论”和“自由裁量论”两种对待疑难案件的极端裁判理论,均未能成功地回答法官在落实疑难个案中的正义时又如何能受到规范的拘束,以价值判断为核心综合平衡论应运而生,通过遵循形式规则、融贯性和最小损害原则,它可以达到捍卫疑难案件裁判中法律属性的基本立场,同时又可以最大限度地确保司法判决的确定性。
法教义学;价值判断;疑难案件;规范拘束;个案正义
传统法教义学理论强调在法教义学内部进行形式化的解释和推理,尽可能避免或减少对规范性价值预设的质疑和挑战,以此最大限度地维护法秩序的安定性和可预期性。在面对疑难案件时它却显得力不从心,由此导致的一个危险倾向便是认为对疑难案件的裁判,必须引入诸如经济的、政治的或道德的方法才能解决,从而否认了疑难案件中裁判结果的法律属性。自概念法学的迷信被抛弃之后,我们似乎又陷入了另一个新的魔阵,亦即“规范拘束”与“个案正义”之间的两难困境。借用我国台湾学者黄舒芃的话说,就是“究竟法官在必须受法拘束的前提之下,要如何妥当衔接法规范与眼前个案,进而在实现个案正义的同时,又能满足法规范体系性的要求?”*黄舒芃:《变迁社会中的法学方法》,元照出版社2009年版,第41页。在对待这一难题上,传统的“独断式”法教义学面临着崩溃甚至被否弃的危险,因为在批评者们看来它对大量裁判尤其是疑难案件的裁判无所助益,它在过分地追求法官裁判要受到规范拘束的同时,不恰当地错失了落实疑难个案中正义的重要目标,因此一种成功的法教义学理论必须能够同时在规范拘束与个案正义这两个维度内有所作为。
在多种可能的进路中引入价值判断将成为必然的选择,在这种背景下本文将先对传统法教义学进行回顾,指出其在当下所面临的种种困境。紧接着,围绕法教义学所开放出来的价值判断,来批判学界对待疑难案件的两种基本立场,其中“依法裁判论”由于过分地依赖法教义体系的完美性而不免落入概念法学的窠臼,“自由裁量论”则由于或多或少地否定了疑难案件裁判中的法律属性,进一步否定了法教义学在疑难案件裁判中的作用,这两个极端均不可取。所谓“超越法律”的雄心抱负仍要受到法教义学体系和法教义学方法的双重限制,而真正能够最小损害法教义体系的决疑方法,当属以价值判断为核心的综合平衡论,它具有多种不可企及的美德。本文最后将采取一个批判性的观点来反思价值判断如何受到限制的问题,回应“甲判乙判随便判”的恣意化裁判立场,*反对这种裁判立场的另一派理论主张要在法教义学的基础上通过协商和沟通形成“法学通说”,以服务于公共视野中疑难案件的裁判。关于“法学通说”理论,可以参见石世豪:《甲说乙说随便说——法学上“学说”的性质及其取舍问题》,载台北《全国律师》2002年第4:9期;庄加园:《教义学视角下私法领域的德国通说》,载《北大法律评论》2011年第1辑;黄卉:《论法学通说》,载《北大法律评论》2011年第1辑;孙维飞:《通说与语词之争——以有关公平责任的争论为个案》, 载《北大法律评论》2011年第1辑;姜涛:《认真对待法学通说》,载《中外法学》2011年第5期。以此捍卫司法判决的确定性。为抑制司法判决的恣意性,一来价值判断需要遵守若干规则,这是法教义学体系的内在要求;二来还要保持与法教义学体系的融贯一致,同时坚持法律论证中的融贯性;最后还需要引入“最小损害”这一新的法律原则,保证价值判断对法教义学体系的损害控制在一种最小的幅度之内。综合以上三方面的要求,以价值判断为核心的综合平衡论方能有效地证立疑难案件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最终维护疑难案件裁判的根本法律属性。
一、传统法教义学的困境
近年来法教义学的自足性备受质疑,这种批评主要来自于社科法学的兴起,后者主张用外部的视角引入经济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的方法来经验地研究法学。社科法学指责传统的法教义学仅仅在简单案件的裁判过程中有用武之地,而案件只要稍显疑难它便无力应对了,此时唯有依靠法官基于后果导向式的自由裁量才能落实疑难个案中的正义。还有一些论者走的更远,甚至主张在一切案件的裁判中法教义学只能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经济分析、后果考量、利益权衡等才是主导司法裁判的思维方法。*关于社科法学的讨论,可以参见苏力:《也许正在发生——中国当代法学发展的一个概览》,载《比较法研究》2001年第3期;苏力:《法律人思维?》,载《北大法律评论》2013年第4辑。蔡桂生也表现出了这种担忧,过分执拗于“A法学”和“B法学”争论实属无益,法律学者过多地越过法科边界并挤进其它人文社科之疆域,这本身就是法律学者不自信的表现,他们将自己装扮成社科法学家并且轻视实在法,从而使得真正意义上的法(教义)学受到挑战。参见蔡桂生:《学术与实务之间——法教义学视野下的司法考试(刑法篇)》,载《北大法律评论》,2009年第1辑。与之相关,现实司法实践中疑难案件的频繁发生也将传统的法教义学打的个措手不及,从而使其在当下中国的地位更显尴尬,以至于人们踌躇于“弃教义学而从其它方法”的十字路口。正如某些学者所质问的那样,“法学在中国应该更多地学习美国的,引入其他社会科学及经济学方法,注重研究‘活法’,或是法律制度背后的经济学原理,而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法律规范?还是延续一直以来效仿以德国为代表的欧陆式‘正统的’法教义学方法?”*卜元石:《法教义学:建立司法、学术与法学教育良性互动的途径》,载《中德私法研究》2010年第6卷。这要求理论家们必须直面传统法教义学所面临的上述困境,而试图提出更加强有力的辩护理论。诚然,如欲准确地回应这一问题,最好还是先来说明学者们是在何种意义上争论法教义学的,从而明确讨论的前提以避免自说自话。
法教义学是一个地域性很强的概念,更多地生长于以立法为传统的民法法系国家中。在德国它无需做过多解释而被法律学人所普遍接受,而在中国却还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概念,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也只是刚刚起步。*目前法学界关于法教义学的研究文献还比较匮乏,比较系统化的只有6篇,这分别是:武秀英、焦宝乾:《法教义学基本问题初探》,载《河北法学》2006年第10期;焦宝乾:《法教义学的观念及其演变》,载《法商研究》2006年第4期;许德风:《论法教义学与价值判断——以民法方法为重点》,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2期;白斌:《论法教义学:源流、特征及其功能》,载《环球法律评论》2010年第3期;卜元石:《法教义学:建立司法、学术与法学教育良性互动的途径》,载《中德私法研究》2010年第6卷;陈坤:《法律教义学:要旨、作用与发展》,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法教义学的德文是Rechtsdogmatik,英文中有legal doctrine和legal dogmatics两种指称,中文则有法释义学、法律信条论、法律教义学、教义法学和法教义学等多种译法,本文采纳“法教义学”这一主流译名。*关于译名的检讨和批评,可以参见武秀英、焦宝乾:《法教义学基本问题初探》,载《河北法学》2006年第10期。佩岑尼克说,在专业法律著作之中法教义学占据了中心的地位,它将私法、刑法、公法等法律实体系统化并做分析性的评价阐述,其核心组成便是对有效法律的解释和系统化,不仅对法条、先例等的字面含义进行描述,有时还伴随着许多道德和其它的实质理由。*参见Aleksander Peczenik, Can Philosophy Help Legal Doctrine? Ratio Juris, Vol. 17 No. 1, 2004.法教义学是一个形式与实质高度统一的概念,从形式主义的角度来看,所谓的“教义性”是指“从某种未加检验就被当作真实的、先予的前提出发,法教义学者不问究竟是什么,法律认识在何种情况下、在何种范围中、以何种方式存在。”*[德]考夫曼:《法哲学、法律理论和法律教义学》,郑永流译,载《外国法评议》2000年第3期。也就是说在形式上法教义学为法体系和法秩序预设了一个不容置疑的权威,法教义学者的任务仅仅是在此权威之下解释法律和适用法律,这体现了法秩序的最高性和安定性;然而,从实质意义上来看,法教义学反对概念法学的价值无涉,它仍然为价值判断的产生开放出了一定的空间,只不过在它进行反思批判时,比如检验某条法律规范的合宪性,仍然要在体系范围内进行论证,也就是说现行有效的体系并未被触碰。*参见[德]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因此,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关于法教义学概念的基本要旨:(1)法教义学要对一国现行实在法秩序保持确定的信奉为基本前提,这也是所谓的“教义”的核心要义所在。(2)法教义学的对象是一国现行有效的实在法,包括民法、刑法等部门法规范,这一点区别于法哲学或法理学,后者更多地以应然法为研究对象,前者的任务“不是对预设的法进行创造性地具体化,而是去认识预设的法。”*[德]诺依曼:《法律教义学在德国法文化中意义》,郑永流译,载《法哲学与法社会论丛》(第5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3)法教义学并不必然拒斥价值判断,而只是限制价值判断发挥作用的范围和方式。
德国法学家阿列克西认为广义的教义学至少包含着对现行有效法律的描述、对这种法律概念体系的研究以及提出解决疑难案件的建议三个层次,并由此分别对应“描述—经验”、“逻辑—分析”和“规范—实践”三个维度。*参见[德]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作为法律证立理论的理性论辩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10-312页。笔者以为上述界定对我们的研究而言意义重大,它毋宁揭示了法教义学的核心意旨。本文所研究的法教义学大致等同于狭义上的法学,在这个意义上,法教义学实际上也可以用来指称部门法学,也可以说部门法学就是法教义学,比如民法就可以被称为民法教义学、民法解释学,刑法也可以被直接称为刑法教义学、刑法解释学等。*参见林来梵、郑磊:《基于法教义学概念的质疑——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载《河北法学》2007年第10期。拉伦茨实际上也是在此意义上使用法教义学的,他将法学界定为“以处理规范性角度下的法规范为主要任务的法学,质言之,其主要探讨规范的‘意义’。它关切的是实证法的规范效力、规范的意义内容,以及法院判决中包含的裁判准则。”*[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77页。从语义上来考察,可以看出传统上法教义学与宗教神学共享着某种东西。从诠释学的早期发展来看,在古代和中世纪更多地是以一种“独断性的诠释学”姿态立足于世,其前提就是文献中的意义是早已固定和清楚明了的,无需我们重新加以研究,我们的任务不过是把这种意义内容,应用于我们当前的现实问题中。*参见洪汉鼎:《诠释学: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当时这种诠释学以“神学诠释学”和“法学诠释学”为典型,前者探究圣经的教义,以回应宗教信仰的一些基本问题;后者则致力于揭示法律条文的内容和意义,从而明确法律适用的依据。
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独断型法教义学”一直支配着法律人的法律教育、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它主要是和德国的概念法学联系在一起的,19世纪受到自然科学和实证之风的影响,法学家们试图将法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概念法学”的提法就是一个最为清晰的例子,认为只要通过抽象的概念操作就可以完成对法的科学创造,以至于温德沙伊德主张法教义学有三项主要任务:其一,法律概念的逻辑分析;其二,将此一分析综合而成一体系;其三,运用此一分析结果于司法裁判之论证。*参见颜厥安:《法与实践理性》,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页。这种理念在法律解释学上的基本立场就是,主张对文本之规范意旨的探究应仅仅围绕着立法原意,在解释中尽可能地避免法官的主观价值判断,这仍然是一种独断型的解释学。*参见焦宝乾:《法教义学的观念及其演变》,载《法商研究》2006年第4期。如果前述社科法学的矛头所指向的是独断型法教义学的话,那么笔者在某种程度上就并不会完全反对它们的指责,因为传统的独断型法教义学的确缺乏足够的开放性,而过度地执拗于法体系内的概念分析和逻辑推理,在对待疑难案件的裁判方面它难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新知识和方法。于是疑难案件便成为了一个十分恰当的讨论基点,可以以此来检讨由其所牵引出的几种裁判理论在对待规范拘束与个案正义之难题上的得失,并进而为法教义学提供一种全新的辩护思路。
二、法官如何面对疑难案件
疑难案件(hard case)是相对于简单案件、常规案件而言的,通常意指由法律适用所导致的裁判上困难的案件,这类案件要么是由于法律规定出现了语义模糊,要么是由于对待决案件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此外还可能是由于对待决案件存在着多个相互冲突的法律理由,因而无法直接通过演绎推理获致妥当的判决。*笔者曾在别处专文探讨了疑难案件的语义争议、产生原因以及当今英美法哲学中对待疑难案件的若干争议。请参见孙海波:《疑难案件的语义争议及成因初探》,载《研究生法学》2011年第6期;孙海波:《案件为何疑难?——疑难案件的成因再探》,载《兰州学刊》2012年第11期;孙海波:《疑难案件的法哲学争议——一种思想关系的视角》,载《法律科学》2013年第1期。当今法学方法论的讨论预设了一个基本的前提,更准确地说是存在着一个普遍性的共识,那就是法律体系必然存在着漏洞,无缝之法网只是概念法学曾经的美梦。也正是基于这个前提,才会出现前文所提及的“规范拘束”与“个案正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简单案件不重要,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简单案件的裁判同样离不开价值判断,但是这种价值判断的基础和目的在于服务既有规则的正确适用,因而通常无害于法教义体系,而只有疑难案件中的强价值判断才能推动法教义学体系的不断更新和完善,突显和化解“规范拘束”与“个案正义”间的矛盾。
(一)裁判疑难案件的两种基本立场
早在1842年的温特波顿诉怀特(Winterbottom v. Wright)一案中,Baron Rolfe法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法律箴言,亦即“正如我们经常所看到的一样,疑难案件出坏法”。*参见William L. Reynolds, Judicial Process, 3rd Edition, Thomson West, 2002, p.65.后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哈兰于1877年在美国诉克拉克(United States v. Clark)一案中引用了前面的这句判词。而美国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霍姆斯在北方证券公司诉美国(Northern Securities Co. v. United States)案中也有类似陈述,即“热点案件,就像疑难案件一样,制造坏的法律”。*Northern Securities Co. v. United States, 193 U.S. 197, 1904.与简单案件不同,在疑难案件中司法裁判的证立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在“穷尽了规则”仍然无法解决问题时,我们便需要对做选择所依据的理由进行论证,也就是要论证如何在相互对立的裁判可能之间作出选择。*参见[英]麦考密克:《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姜峰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96页。我们似乎再次回到了“规范拘束”与“个案正义”的难题,笔者接下来便检讨目前学界对待疑难案件的两种裁判立场,每一种裁判立场本质上属于方法论的内容,它们无疑都对应甚或决定于论者对待疑难案件所秉持的认识论态度。Ralf Poscher认为疑难案件虽为偶发现像,但它却是裁判的核心,也是作为职业和学科的法律实践的核心。*参见[德] Ralf Poscher:《裁判理论的普遍谬误:为法教义学辩护》,隋愿译,载《清华法学》2012年第4期。的确如此,相较于简单案件,疑难案件的裁判更能突显法律人在教义学与价值判断之间所做的精细选择,同时也再一次宣示了法教义学对于疑难案件裁判的必要意义及价值判断的客观限度,以此突显疑难案件裁判中的法律属性。
1、依法裁判论。依法裁判论,笔者也称之为体系决定论,在对待疑难案件存在论的态度上坚持“否定论”,认为既有法律体系是张无缝之网,它可以覆盖到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因此一切案件都是简单案件,法教义学体系完全可以为其提供“唯一正确答案”。19世纪在德国兴起的概念法学以及在美国盛行的法律形式主义,是这一裁判理论的典型代表。概念法学过度强调了司法裁判中的法律属性而断然否定疑难案件的事实存在,遭到了其后利益法学和评价法学的猛烈抨击。*当然,概念法学也并非完全一无是处,格罗斯菲尔德曾坦言不讳地赞誉概念主义,认为其有助于阐明法律体系内在的各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法律工作者从不同时代习得的全部知识的一个概括与缩影,更重要的在于它是使得各种判决获得理性化的手段。参见[德]格罗斯菲尔德:《比较法的力量与弱点》,孙世彦、姚建宗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耶林认为概念法学只是一场天国幻梦,并呼吁法学要返回尘世生活的彼岸。*哈特曾将耶林对概念法学的批判总结为五点:(1)过度关注抽象的法律概念,而不考虑它们在现实生活中适用的条件;(2)在利用和发展法律概念时,无视必须要考虑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3)确信能够区分某一法律规则或概念的本质法律后果;(4)无视法律的目标和目的,并拒绝追问“法律为什么这样”的问题;(5)法律科学在概念和方法上对数学进行了错误的模仿,以至于所有的法律推理都变成了纯粹的数学计算。参见[德]耶林:《法学的概念天国》,柯伟才、于庆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英]哈特:《耶林的概念天国与现代分析法学》,陈林林译,载邓正来主编:《西方法律哲学家研究年刊》(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2页。法律形式主义也由于其机械性和僵化性也被讥讽为“机械法学”,法律现实主义者的反叛终结了法律形式主义主导美国法律界的时代。可以看出,这种“唯一正确答案”的理论受到了来自内、外部怀疑主义越来越多的批判而濒临破产。对此一个可能的主张毋宁在于,对于疑难案件事实上的确存在着答案,但并非一定是“唯一的”和“正确的”答案。就此而言,体系决定论者过于信奉法教义学体系的完美性,在疑难案件的存在论上普遍持消极态度,加之其过分地强调司法裁判中的法律因素,因而走向了“依法裁判”的极端。对待所谓的“疑难案件”通过投掷硬币的方式依然可以寻求到“正确答案”,但这种裁判方式严重背离了法教义学的真正要求,同时也不恰当地遮蔽了“规范拘束”与“个案正义”的难题。
2、自由裁量论。法理论家尤其是法实证主义者们,从“疑难案件中法官的裁判义务”发展出了自由裁量论。然而裁量(discretion)这一概念却是十分含混的,德沃金区分了自由裁量的两种版本:(1)弱式意义的自由裁量,表现为法官所必须使用的标准不能够被机械地适用而需要使用判断;(2)强式意义的自由裁量,是指法官在疑难案件的裁判中可以不受现有法律准则之拘束而可为法外裁判,这与法官通过造法并回溯性地应用于眼前个案的行为同义。*参见[美]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3-54页;Ronald Dworkin, Judicial Discretion,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60, No. 21, 1963.这一点可以以哈特的主张为例证,“处于边际地带的规则,以及由判决先例的理论所开放出来的领域中,法院则发挥着创造规则的功能。”*[英]哈特:《法律的概念》(第二版),李冠宜、许家馨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30页。此处,笔者并非简单地反对弱式意义的自由裁量,一般而言这种理论基本上能够做到“依法裁判”,诚如德沃金所言,“一个官员享有自由裁量权,并不意味着他可以不顾情理和公平的准则,可以随心所欲地裁决,只是意味着,当我们提到自由裁量权这个问题时,我们心目中的特定权力所规定的标准不能支配他的决定。”*[美]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6页。问题在于这种弱式意义的自由裁量论缺乏相应的操作规程,最终难以解决法官该如何具体地行使判断权以保证其所为裁判并未偏离法体系,基于这一点可以说它有时徒有依法裁判之名而行偏离、扭曲甚至改变法律之实,依法裁判仅仅成为了一种虚假的粉饰。对于强式意义的自由裁量论而言,其最大的问题在于法官进行疑案裁判时可以超越法律,从而走向了依法裁判的极端对立面。*具体来说,强式意义的自由裁量论面临着如下三个难题:(1)疑难案件中偏离法教义学体系必须给出足够充分的理由,也就是必须要给“为何不受规范拘束”一个说法。由于它默示或根本否定了疑难案件裁判中的法律因素,允许法官通过司法立法的方式解决争议个案,已经构成了对法教义学体系的极大损害,必须对其加以严格的限制;(2)在严格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之下,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各司其职,如果法官可以通过司法立法实现个案正义,那么这必然会背上“司法权染指立法权”的骂名,而无法获得正当性证明;(3)法官通过回溯立法而进行的创制性裁判,如何来解释“法不溯及既往”这一普遍的法治原则。因而在面对疑难案件的诸多裁判理论当中,该理论由于缺乏竞争力而必须被抛弃。由此在法律规则所未能覆盖到疑难案件中,法官可以诉诸于法外的标准或因素而为裁判,这同时也否认了疑难案件中当事人先定的权利和义务。
(二)两种裁判模式的局限
体系决定论相信案件的答案就存在于法教义学体系中,只要法官通过“依法裁判”总能发现每一个案件的正确答案。这种“依法裁判”的立场,要求法官固守封闭的法教义学体系,他们虽说理论上不太愿意区分简单案件与疑难案件,事实上在那些无法通过运用演绎推理而径直获得裁判结论的案件中,他们下意识里仍然会认识到这种裁判艰难的存在,为了忠于“依法裁判”的基本信条,首先通过法感或裁判经验获致一个大体的结论,然后再回溯性地去“找法”以证立这个判决。尽管在后一种情形中法官们也进行了教义学论证,但只不过是为了掩盖其进行价值和自由裁量的事实,也难怪一些法律现实主义者将这些法官嘲讽为“说谎者”。这可能导致的一个后果是,体系决定论很难在疑难个案中落实正义。比如许霆案中,*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穗中法刑二初字第196号刑事判决书。先定后审的裁判方式在该案的判决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一审法院以盗窃罪判处许霆无期徒刑,然而利用ATM机故障反复取款的行为本身是否构成“盗窃金融机构”本身就是一个争议性很大的问题,一审法官在判决书中完全回避了这一点,而径直选择适用了《刑法》第264条“盗窃金融机构”的加重条款。该判决作出后遭到的最大批判在于量刑过重和表现出来的极端不公正性,法官在拒绝法律漏洞存在的前提下必然在其专断意志的指引下选择适用僵化的法条,不免最终牺牲掉对个案正义的追求。
自由裁量论(这里主要是指强式意义的自由裁量论,笔者对弱式意义的自由裁量论是否能够真正做到依法裁判持保留态度)完全站在了依法裁判论的对立面,它虽然过多地关注疑难个案中正义的实现,但某种程度上却违背了“规范拘束”的基本要求,进而也或多或少地否定了疑难案件裁判中的法律属性。*再做一些补强性说明,强式意义的自由裁量论,试图通过引入道德推理、经济分析等方法来应对疑难案件的裁判,有时也很难说能够实现“个案正义”,它有可能将我们引向一种司法裁判的法律虚无主义,难以成为一种适格的裁判理论。具体一点讲,在“自由裁量论”中,法官活动的本质被还原为一种将抽象规范适用到具体案件中的工作,有鉴于此就需要在一般性的法律规范与活生生的个案现实之间拉开一定的距离,在这个距离的射程之内法官得以行使自由裁量权以落实个案正义的问题。这种理论的核心主张便在于,现有法教义学体系或法规范体系不可能为任何案件都提供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假若如此,法官的手脚便会被束缚起来,从而不得不被迫放弃对个案正义的追求。自由裁量论试图寻求一种“超越法律”的裁判规则,不再固守“依法裁判论”的决定主义立场,而表现出一种非决定主义的裁判进路,从而自然而然地在疑难案件的裁判中偏离法律标准。在凯尔森看来,法官的裁判要在法律中获得证立,意义无非是指法官裁判遵循法律所提供的框架界限,它并非意味着法官裁判呈现出法律这个一般规范所指示的唯一个别规范,而是意味着法官裁判符合了在法律这个一般规范的框架范围之内所容许的、众多可能的个别规范的其中之一。*参见Hans Kelsen, Introduction to the Problems of Legal Theory, translated by Bonnie Litschewski Paulson and Stanley L. Paulson, Clarendon Press, 2002, pp.67-74.总之,以上两种对待疑难案件的司法裁判理论,简单地在“规范拘束”与“个案正义”之间各执一端,最终未能成功地化解这一难题。
三、以综合平衡论为基础的新法教义学
在争议案件面前法官究竟是要坚持“规范拘束”还是追求“个案正义”?我们所需要的理论并不是去遮蔽上述问题,而是要揭示和解决这一难题,这也是一种合格的司法裁判理论所必须具备的实践品质。笔者以为,在最小损害法教义学体系的前提要求下,以一定的方式来纳入价值判断,并能够通过对价值判断的制约来达到保证司法裁判的确定性和正当性,在此意义上发展而出的新法教义学将不失为一种成功的替代性选择。这种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的综合平衡论,就像古罗马的双面神杰纳斯一样,既回望过去又展望未来,它需要在法教义学体系内进行反思均衡,并同时展开两个向度的论证:(1)综合平衡论的逻辑起点是法教义学体系,它要求法官忠实于法律,无论简单案件中所为的演绎推理还是疑难案件中所为的实质推理,都必须以现有的法律规则为基础,以此捍卫“依法裁判”的基本立场,也就是说即使在疑难案件的裁判中也并不否定法律属性的存在,裁判结论的证立需要在一个开放的法教义学体系内进行,从而驳斥经济分析、道德推理和法官造法等极端裁判理论;(2)综合平衡论致力于落实争议个案中的正义问题,但它否认对于任何案件都存在着“唯一正确的答案”,而毋宁通过价值判断的方法诉求一个对争议个案实现最佳化证立的判决,以此驳斥天真的概念法学和法律形式主义的体系决定论。不难看出,综合平衡论既拒绝“依法裁判论”的决定主义的绝对论立场,同时又反对“自由裁量论”的非决定主义的极端化立场,而试图在坚持简单案件与疑难案件二分的基础上,引入价值判断的方法在决定论与非决定论之间走出一条中间道路。
(一)价值判断对于个案正义的落实
对此一个最为直接而常见的批评莫过于,“这不过就是一个简单的折中论吗”?再简单一点说,“它不过是既坚持依法裁判,同时又尽可能允许法官在必要时进行自由裁量吗”?事实上远非如此,综合平衡论主张最为核心的要义在于如何处理好法教义学与价值判断的关系,二者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像太极球中的阴阳两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张骐:《形式规则与价值判断的双重变奏——法律推理方法的初步研究》,载《比较法研究》2000年第2期。也就是说在法教义学体系中所运用的诸如法律解释、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等法教义学方法离不开价值判断,同时价值判断的使用又不能偏离法教义学体系。在这个意义上讲,综合平衡论既不是简单的依法裁判,也不是恣意的自由裁量,而是一种高度复杂的在法教义学体系与价值判断之间往返穿梭的裁判理论。苏力曾在许霆案中对法教义学提出过尖锐的质疑,“我质疑以个体法官思考根据的法条主义(主要是法教义学和法律论证推理)在难办案件中的排他有效性。……在难办案件中,法官无论怎样决定都必须首先作出一连串政治性判断。”*苏力:《法条主义、民意与难办案件》,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1期。这一批评固然意在诘难法教义学的功用有限性,却也道出了价值判断在疑难案件裁判中的必要性。
我国台湾学者王立达曾指出,法教义学“未来应挥别概念法学的魅影,不再自限于法律效力之偏袒面向,并且明白承认法效力与法规范论述的多样性,致力于发展足以统合道德的、伦理的、政治和政策的、实用的等多层面规范论述的研究架构。”*王立达:《法释义学研究取向初探:一个方法论的反省》,载《法令月刊》2000年第9期。由此观之,法教义学必然展现出两个不同但又彼此关联的面向:其一,描述性的维度,这是由实在法本身的“实在性”所决定的,教义学者的任务在于通过概念分析的方法厘清实在法的含义和探寻立法者的实际意图,分析实在法的规范结构及逻辑体系,协调各种冲突规范间的关系,并为司法裁判提供体系化和妥当化的裁判规则,概念法学曾在这方面做过杰出的工作;其二,也是更为重要的,是规范性的维度,实在法本身也是一个“价值负担者”(value-burdened)的存在,教义学者需要对某个规范的解释、某个新的规范或新的制度提出建议并加以证立,或者对法院裁判就其在实践上的缺陷进行批评,提出某个相反的建议。*参见[德]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作为法律证立理论的理性论辩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12页。这是与作为法教义学核心品质的实践性而非超理性联系在一起的,“即以理性的、可理解的方式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法教义学的前提并非不可动摇,而是如已承认的那样,是可变化的:法律甚或法庭习惯是可以并且得被改变的。”*[德]维亚克尔:《法律教义的实践功效》,王洪亮译,载《中德私法研究》2010年第6卷。概念法学所提供的完美教义学体系在现实面前被击的粉碎,由于它并不承认法律存在漏洞,所以它自然无法协调“规范拘束”与“个案正义”间的紧张关系,换言之对于疑难案件它要么无法提供答案,要么提供一个无法得到有效证立的答案。
价值判断进入法律解释、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证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司法裁判中恰当地运用价值判断可以保证获得一个符合正义的个案裁判,简言之其目的就在于推进个案正义的落实。当下争议最大的则是法教义学与价值判断的关系问题,进言之价值判断究竟如何使用才被可以认为是妥当的。卜元石认为二者上升到哲学层面实际上就是“忠于法律”与“结果公正”的关系,对此他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法官在一目了然的案件中只适用法律规定即可,无需过问法律规定背后价值判断的合理性,只有出现了法律规定不明确或法律漏洞时价值判断才成为必需。总而言之,司法过程中进行价值判断只是一种例外而非常态。*参见卜元石:《法教义学:建立司法、学术与法学教育良性互动的途径》,载《中德私法研究》2010年第6卷。许德风则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法律规则的适用无法与价值判断割裂开来,即使三段论下单纯的找法活动以及区分简单案件与疑难案件的本身都会涉及到价值判断。因此,在他看来价值判断是一项贯穿裁判始终的工作,在进行司法裁判时,法教义学的分析可以减轻裁判者价值衡量的负担,而直接得出契合法律背后基本价值选择的结论。*参见许德风:《论法教义学与价值判断——以民法方法为重点》,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2期;许德风:《论基于法教义学的案例解析规则——评卜元石:〈法教义学:建立司法、学术与法学教育良性互动的途径〉》,载《中德私法研究》2010年第6卷。对此,笔者基本同意后一观点,但同时认为又有必要进一步区分简单案件裁判中的“弱价值判断”与疑难案件裁判中的“强价值判断”,法教义学分析固然内涵价值判断,但如不做上述区分我们仍然无法洞悉价值判断发挥作用的具体方式。“弱价值判断”是以法教义学体系内的规则适用为基础和核心的,其作用的发挥一般情况下丝毫无损于既定的法教义学体系;而“强价值判断”试图通过反思和批判来修正或否弃既定规则,甚至诉求规则背后的实质理由或一般原则来实现个案正义,它通常会构成对当下法教义学体系的损害,因此其实践运用须慎之又慎,在这个意义上引入下文的融贯性和最小损害原则将成为必要。这种被学者们所普遍漠视的区分,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真正重要的真理性知识。
(二)价值判断的制约对于裁判确定性的满足
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的综合平衡论还可能面对另一个质疑,即价值判断如何保证司法判决的确定性,而不至于使其沦为“甲判乙判随便判”的恣意化裁判。笔者的基本观点是,即使在司法裁判中引入价值判断,并不必然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司法裁判的确定性。此处笔者并未使用“客观性”这一术语,*长期以来,“真理”、“客观性”被视为一种形而上学的概念,在法学界找到冷落甚至抛弃。事实上,英美法理学界近几十年来已经对法律领域尤其是司法领域中的客观性做了很多有益的探讨,这方面的代表文献有:Kent Greenawalt, Law and Objectiv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Nicos Stavropoulos, Objectivity in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Brian Leiter edited, Objectivity in Law and Moral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原因在于人们对客观性的概念尚未达成基本共识,从而导致这一术语在学术讨论中被极其混乱地使用,以至于论者基本上都是在自己的语义框架下讨论客观性,从而不免自说自话。这里有三个比较易混淆的概念,即客观性、正确性和确定性。司法判决的正确性(correctness),相对于判决的错误性而言,意指司法裁判违背了某些形式化的规范标准或实质化的价值标准;司法判决的确定性(determinacy),正是相对于司法裁判的不确定性而言,核心要义在于强调裁判要受到规范的拘束,不能恣意而为;司法判决的客观性(objectivity),对应于司法判决的主观性,表明司法判决不是裁判者主观意愿的表达,而是依凭一套可控的标准作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看出司法判决的确定性和客观性有交叉之处,均强调裁判的作出必须基于一定的法律规则,因此对于当事人及代理律师而言具有一定程度的可预测性。因此,为避免不必要的争执和混乱,本文仍然选择使用确定性这一概念。
价值判断滥觞于赫克所倡导的利益法学,到了拉伦茨所开创的评价法学那里则发展到了一种巅峰之势,再往后一直被视为法学方法论的最核心内容。评价法学以开放的姿态承认法律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漏洞,另外法教义学体系中还存在着所谓的不确定概念或概括条款、尚未被立法者预见的新问题、立法评价的前提要件消失、不同的法律理由间出现冲突等棘手情形,那么在这些情形下引入价值判断,固然可以在争议个案中落实正义问题,但也不免会招致如下批评:“法律的内容取决于法官在个案中的裁判,在我们的法律传统中所建立并且规定在宪法中的要求——法官受法律的拘束,根本无法实现,所谓的法律支配,只是一种幻想。”*[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页。拉伦茨以新黑格尔主义的立场,试图通过诉求所谓的“正确之法”来重构法规范的适用,他将法官的活动重新界定为一种在抽象法规范与具体个案现实之间的来回游走的辩证过程,以辩证取代传统的涵摄和打破“应然与实然”之分立,而真正能够最终拘束法官的在于法规范和现实所指向的“客观精神”。*在拉伦茨那里,只要在统合实然与应然、现实与规范的客观精神的基础上,法官的决定既能满足法体系对于“唯一正确决定”的要求,又能落实个案正义。就此意义而言,“法体系性”与“个案正义”之间看似对立的紧张关系,其实恰可以透过法官在每一次个案审判中的辩证对于客观精神的一再寻求而得以化解。参见黄舒芃:《变迁社会中的法学方法》,元照出版社2009年版,第55-62页。拉伦茨的解决方案并不是非常成功,很大的一个问题在于他所谓的法规范的真实意义,其实是根据眼前活生生个案而定的,这就意味着法规范的真实意义会随着纷繁复杂的个案而不断地发生演变,从而会失去法规范最为根本的一般性和确定性,因而难以保证司法判决的确定性。另一个问题在于“客观精神”本身就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带有唯心色彩的概念,究竟到底什么是客观精神、如何寻找客观精神以及它是如何制约和保障司法裁判的,这些问题都很难得到明确的回答,因此以“正确之法”为导向的辩证模式由于无法确保司法判决的确定性,在“规范拘束”与“个案正义”这个难题面前失败了。
1、价值判断的教义学体系约束。为了确证价值判断下司法判决的确定性这个问题,第一个必需的条件是价值判断要受到规则的约束,即价值判断本身需要受到一系列规则的限制。“穷尽规则适用,方能进行价值判断”实质上是一个长久以来被误解的命题,形式规则与价值判断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许德风认为“成文的法律已是人们最低价值判断的产物”这一论断意义重大,*参见许德风:《论法教义学与价值判断——以民法方法为重点》,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2期。也就是说单纯的教义学体系内法律规则的演绎适用本身就包含了第一层次的价值判断在内,即使是法律规定与案件事实之间的涵摄也无法离开价值判断,目光在事实与法律之间的往返本身就内嵌了价值判断的运用。就此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价值判断受到何种限制才能最大限度地确保司法判决的确定性?2003年轰动一时的“河南洛阳种子案”中,李慧娟法官“以身试法”,公然在判决书中宣布“《河南省农作物种子管理条例》作为法律阶位较低的地方性法规,其与《种子法》相冲突的条款自然无效。”*参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洛民初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显然李慧娟法官的这一决定是价值判断之后的结果,然而她超越了现行法律框架下中国法官的职权范围,因为《立法法》对于审查规范性法律文件是否违宪规定了专门的启动程序,*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90条。她追求一种“更高品质之法”本还有别的选择。李慧娟法官的悲剧也警惕我们,价值判断必须遵守形式规则,否则价值判断有可能沦为恣意的主观判断,甚至还有可能为判断者带来某些政治或人身方面的风险。
第一,价值判断的基础。价值判断本身并不能直接作为裁判规则而使用,比如“类似的案件要得到类似的处理”这一形式正义原则,自身不能单独作为某一案件的裁判依据,但可以约束法官通过法规范的类推适用的方法来实现个案正义。又如,诚实信用、契约自由、合同正义、公序良俗也同样不能通过单纯的价值判断而成为裁判依据,而必须要借助于案例实现类型化,以落实疑难个案中的正义问题。如果法教义学体系中对某一事项已有明确的规定或明令禁止在该规则之外进行“超越法律”的价值判断,如《立法法》第90条关于“审查规范性法律文件是否违宪的启动程序”的规定,法官就不得越权代专门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某一规范性文件因违宪而无效。
第二,价值判断作用的方式。疑难案件之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乃是由于仅仅凭借既有形式规则难以推进裁判。此时法官运用价值判断方才成为一种必要,问题则在于价值判断究竟是以何种方式进入裁判,以及这种价值判断的可能限度是什么?在笔者看来,价值判断可以表现为两种具体的方式:一种是法官在疑难案件的裁判中进行了明显的价值判断,比如在规则与原则并存之时,他选择适用那些比较富有弹性的诚实信用、契约自由等法律原则,虽然法律原则仍然属于法律大家族中的一员,但由于规则和原则在逻辑上存在差异,规则的典型适用方式是涵摄,而原则的典型方式是权衡。*参见Robert Alexy, A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47-48.又如,法官通过后果考量来选择、解释和适用法律规则,并以此证立所作出的判决;另一种为非明显的价值判断,它隐藏于法律的法律解释和法律之中,只有深入到法官的说理之中,才能发现这种非明显的价值判断的运用。
第三,价值判断的限度。若将价值判断推向极致,必然会导向前文所谈的强式意义的自由裁量论所存在的难题,因此我们必须为价值判断设定一个限度。具体来说,首先,非明显的价值判断几乎贯穿于一切案件的裁判中,即使在那些单纯地运用演绎推理的案件中亦是如此,正如德国法学家魏德士所指出的,“涵摄的过程(将某一生活事实归入某一规定了相应法律后果的规范)总是包含着评价的因素”。*[德]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01页。然而需注意,无论是在演绎推理、等置模式还是法律论证中,价值判断只是促使着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不断趋于适应的关系,案件结果的最终作出仍需依凭逻辑,故而逻辑本身便构成了对价值判断的一种强有力的制约;*笔者曾指出,新近颇为流行的类比推理、等置理论以及法律论证,构成了对三段论及形式逻辑的巨大冲击。然而,在形形色色的批评声中实际上存在着对逻辑与经验、形式逻辑与非形式逻辑之关系的误解。离开了三段论的基本框架上述理论均难以自足。形式逻辑在法律推理中的地位与作用必须重新地得到捍卫,否则告别司法三段论只会走向恣意化的司法裁判。参见孙海波:《告别司法三段论?——对法律推理中形式逻辑的批判与拯救》,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4期。其次,在现有法教义学中已对某一事做了具体而细致的调整,则法官不得为明显的价值判断而只能严格依法裁判;最后,在对待模糊规范、概括条款和法律漏洞时,法官可以进行明显的价值权衡,但仍要受到整个法体系之内在原则的制约,其所为判决应该满足合法性与合理性两个维度的要求,至于是否超出限度可以通过融贯性和最小损害原则来具体判定。
2、以融贯性制约价值判断。融贯性(coherence)是一个与一致性比较接近的概念,事实上严格讲二者之间仍有差异,比克斯认为“这是一个比纯粹的一致性更强硬的或更原则性的问题”,但‘某些更强硬的问题’是很难清晰地表达出来的。”*[美]比克斯:《牛津法律理论词典》,邱昭继等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它主要表现为法律体系的融贯性和法律论证中的融贯性。但需要指出的是,融贯性只是实现司法判决确定性的一个必要而非充分条件,侯学勇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指出融贯性不是对推理或论证的确定性证立,尤其是在疑难案件中往往会存在两个或以上同样具有融贯性的解决方案,这时候很难说哪一个是最为融贯的,而只能选择一个相对而言较为融贯的裁判。*参见侯学勇:《法律论证的融贯性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页。以此来看,融贯性只能客观上通过制约价值判断的行使方式来促进司法判决的确定性。
第一,法教义学体系的融贯性。融贯性的第一个要求,即法律体系的融贯性,实质上也就是指法教义学体系的融贯性,它要求将某一法律体系视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同时将不同的规则在司法适用之前进行全盘地考虑,以尽可能地达到一种协调一致的状态。简单地说,它是指各种法律价值之间的相互支持与证立,以形成一个在逻辑和实质上无矛盾的体系。在此意义上,麦考密克提出了法教义学体系融贯性的两种判准:其一,一组规则能够有助于增进某种相关的价值或多种价值,并且能够减少其它相关价值的冲突;其二,一组规则如果能够满足(satisfy)或符合(fit)某种单一而又更加一般化的原则,或成为某单一而又更加一般化的原则的例证。*参见Neil MacCormick, Coherence in Legal Justification, in Scott Brewer edited: Moral Theory and Legal Reasoning,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8, p.268.索里亚诺指出法律体系的融贯性不同于法律论证的融贯性,它所关心的是“如何将一个法律决定融入某一法律体系之中,并将其与法律体系的其它要素融合在一起”。*Leonor Moral Soriano, A Modest Notion of Coherence in Legal Reasoning: A Model for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Ratio Juris. Vol. 16 No. 3, 2003.正如爱德华法官在为司法能动性辩护时所指出的那样,“在一个判例法体系中,法官必须从一个案件到另一个案件来发现决定,从而使得法律体系呈现出一致性、融贯性、现实可用及实际有效。”*Edward, David, Judicial Activism: Myth or Reality? in Angus I. L. Campbell and Meropi Voyatzi eds: Legal Reasoning an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European Law, Trenton, 1996.对此也可以帮助我们增进对法律体系融贯性的认识,在运用价值判断时必须注意协调好法律规则之间、法律原则之间以及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之间的关系,此外还要处理好法律规则、法律原则与法外的政治道德原则、既往判决(包括普通法系国家中的判例、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先例以及中国当下正在推行的指导性案例)中所确立之规则之间的关系,尽可能使法律体系成为一个融贯的整体或系统。
第二,法律论证的融贯性,也可以称作推理的或裁判的融贯,强调在各种论证之间形成一种相互支持的结构。坚持融贯论的学者,一般并不会否认融贯性能够证立疑难案件中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关于融贯性对疑难案件中当事人权利义务证立的讨论,请参见孙海波:《疑难案件的法哲学争议——一种思想关系的视角》,载《法律科学》2013年第1期。融贯性在某种意义上和中国古代道家的“阴阳相济、虚实相生”是相通的,这与本文一以贯之的论证主题紧密关联,规范拘束要求法官要严格地依法裁判,而疑难案件的存在又要求法官通过价值判断去实现个案正义,法教义学体系与价值判断分为阳、阴和实、虚,二者彼此交融、相容共生,在这种合力的作用下疑难案件裁判中的法律属性得以捍卫。融贯性落实到法律论证或法律推理中,体现为裁判结论如何在相互支持的论证结构中作出,并实现对案件争议的最佳化证立。德沃金整全法之下的建构性诠释理论实质上就是法律论证融贯性的一种表现,整全性的裁判原则引导法官尽可能地基于以下假定来确认权利与义务,亦即它们皆由“人格化的社群”这一单一作者所创设,他表达了正义与公平的一个融贯性观念。同时,根据整全法,如果法律命题出现于或推导于为社群法律实践提供最佳建构性诠释的正义、公平和程序性正当程序诸原则,那么该法律命题为真。*参见Ronald Dworkin, Law’s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225.法律论证中的融贯性除此之外还要求事实以及证据之间的相互兼容和相互推导,尽可能地做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和矛盾,从而形成一个完美的证据链条。最后,只有将法教义学体系的融贯性和法律论证的融贯性结合起来,才能最大限度地促成司法判决的确定性,以防止法官恣意而为裁判。
3、最小损害原则的引入。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法官首先拥有一套来源于法教义学体系的知识,它们是关于法律体系的结构、法律条文的理解及案件事实的认定等方面的内容;其次,除了上述专业的知识以外,法官还具有个人的偏好、道德和宗教信仰、政治信念等其它知识,所有这些因素集中起来就组成了法官的知识信念体系。而一旦我们反思我们的信念,便会发现我们对某些信念比另一些信念更确信,也就是说我们有理由信任那些我们更为确信的信念。当多种信念之间彼此冲突之时,我们通过反思平衡的办法来考虑哪些信念是我们最为不确定的来决定哪些应该放弃。如果我们必须放弃某些信念时,理所当然应该放弃那些我们认为最为可疑的信念。*参见[美]波洛克、克拉兹:《当代知识论》,陈真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9页。因此可以看出,对那些最为可疑的信念的修正与放弃,本身可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和支持我们既有的信念体系。相应地在法学领域中,通过运用价值判断来对疑难案件所涉及的规则或原则的修正或否弃,也必须追求一种对法教义学体系的最小损害。法教义学体系实质上是由不同层级的规范性命题组合而成的,而这些不同层级的规范性命题之间又具有内在的融贯性。由于法教义学体系是一个不断自我调整和更新的开放性体系,而疑难案件的出现意味着法教义学体系中存在着规范性命题之间的冲突,那么此时必然要在冲突的规范性命题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这一选择的过程同时也是价值判断发挥作用的过程。
为确保司法判决的确定性,价值判断必须受到最小损害原则的制约,换句话说基于价值判断做进行的利益衡量必须使得对法教义学体系的损害控制在一种最小的幅度之内,否则这种价值判断的行使方式本身是要受到指责和否定的。为实现这一目的,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建构最小损害原则:首先,对处于法教义学体系较为外围层级的规范性的损害,优先于对核心层级的规范性命题的损害。具体来说,对调整同一事项的上位法之规则的损害大于对下位法之规则的损害,对调整同一事项的特别法之规则损害大于对一般法之规则的损害,对某一具体法律规则的损害大于对抽象法律原则的损害;其次,损害结果不确定的损害优先于损害结果确定的损害;最后,判断最小损害还要观察特定的损害所带来的潜在影响,也就是损害波及度的大小。*参见陈坤:《法学方法论的困境与出路》,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比如在“广西驴友案”中,*该案事实及判决结果,请参见: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2006)青民一初字第1428号民事判决书。一审法院认为如果简单地以法律未对自助旅游的性质及责任作出规定,而以此认定同行驴友无责任,便会导致自助旅游活动的盲目化和轻率化,于是便以侵权责任法的过错责任条款判决驴头梁某承担65%(16万元)的责任比例和其他驴友承担15%(4万元)的责任比例。*驴友案主审法官在接受采访时谈到,“我们需要判决透露这样的信息:如果你没有相关资质和能力,请你谨慎行事,否则就不能逃避可能造成的损害后果。”不难看出,这一判决乃是基于对各种可能后果的综合考量下所作出的。参见陈华婕、田波:《“驴友案”:主审法官“吃螃蟹”》,载《法律与生活》2007年第1期。然而,这一判决是否做到了对法教学体系的最小损害呢?
该判决我们权且称作D1,第二种裁判进路D2,以“风险自甘原则”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可能会来得更直接一些,*2011年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就以“风险自甘原则”判决同行驴友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参见: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2011)金民一初字第20171号民事判决书。D1和D2构成了“驴友案”的两个极端判决,一个最大限度地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另一个则从根本上否认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该案“主审法官吃螃蟹”果断地选择了D1,它最大的弊害在于采纳了侵权法上的过错责任原则,违背了“风险自甘”的自由原则,警惕自助旅行者有义务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而挽救受害者。D1和D2均无法符合或消除自由与公正价值之间的冲突,在这个意义上讲这两种裁判进路均无法实现裁判结果与法教义学体系的融贯性。由此,法官比较明智的选择可以采取D3,基于“公平原则”的裁判进路,各方虽都无过错,基于公平原则的考虑判令其进行酌情的补偿。D3一方面满足了自由和公平原则的基本要求,成功地避免了二者之间的冲突,同时又不会对《民法通则》中关于侵权责任规定构成损害。因此,D3相对于D1和D2对民法教义学体系的损害是最小的,它同时兼顾了自由和公平原则,因此是一个最能够为当事人所接受的判决。
四、结论:法教义学的重生
本文通过讨论“规范拘束”与“个案正义”这一法学方法论的核心问题,试图解决法教义学视野下的价值判断难题。由于司法实践中疑难案件的频发,而法教义学对此似乎无能为力。如学者所说,“我们在当代中国常常看到的是,当实践真正需要智力支持的时候,法学却并不在场。面对疑难的个案,几乎所有的人都显得手足无措。”*舒国滢:《并非有一种值得期待的宣言——我们时代的法学为什么需要重视方法》,载《现代法学》2006年第5期。由此,对法教义学的批评声接连不断,甚至一些社科法学阵营的学者主张要抛弃法教义学,而试图引入经济分析、道德推理等法外之“法”来应对疑难案件,主张法官在此种情形中可以通过行使自由裁量权来造法,进而否定了疑难案件裁判中的法律属性。前文分析已经成功地证明,任何试图否认疑难案件裁判中的法律属性的理论都是站不住脚的,只有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好法教义学与价值判断间的关系,也才能游刃有余于“规范拘束”与“个案正义”的两难之间。严格的“依法裁判论”和“自由裁量论”在对待“规范拘束”与“个案正义”上各执一端,均不足以应对实践中频发的疑难案件,在这两种极端裁判立场之外笔者提出了一种新的法教义学理论,也就是前文所谈的以价值判断为核心的综合平衡论,它能够成功地化解“规范拘束”和“个案正义”的难题。同时,价值判断的引入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司法判决的确定性,相反,一方面价值判断需要受到法教义学体系的约束,另一方面融贯性和最小损害原则可以客观地制约裁判者的判断行为,使得整个裁判能够获得前后一致而又不至于对法教义学体系造成较大损害,进而也就确保了司法判决的确定性。
现今并不是一个要告别法教义学的时代,相反而是需要发展出一种更加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和精致化的法教义学体系和方法。*Ralf Poscher事实上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指出教义学理论能够为疑难案件的裁决提供理论上可行、规范上可欲和实证上充分的说明。教义学理论以法律论证场域为基础,而法律论证场域又有其特殊的教义学结构,这一结构能够确保疑难案件裁判的法律属性。参见[德] Ralf Poscher:《裁判理论的普遍谬误:为法教义学辩护》,隋愿译,载《清华法学》2012年第4期。我们将看到,以综合平衡论来容纳价值判断的新法教义学,符合学说史上法教义学发展的趋势。随着施莱尔马赫建立了普遍诠释学之后,哲学诠释学实现了从特殊诠释学到一般诠释学的转变,而到了伽达默尔则再次实现了其第二次转向,即从本体论哲学的诠释学发展为一种实践哲学的诠释学。这种诠释学既不是一种单纯理论的一般知识,也不是一种光是应用的技术方法,而是一门综合理论与实践双重任务的哲学。*参见洪汉鼎:《当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下),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51页。自耶林的目的法学以及赫克的目的法学破除了概念法学的迷信之后,法教义学也经历了从封闭的独断型法教义学到开放的实践型法教义学的转变,一方面,它不再固守一个封闭的概念体系,也不断然地拒斥一切形而上的价值判断,而是主张建构一个包容的和开放的法教义体系,这一体系是由法概念、规范和原则的砖瓦堆砌而成,并公开承认自身“未完成性”的高尚品格;另一方面,它更加注重教义学方法,这种方法既包括常规的法律发现、法律解释、法律推理与法律论证,还包括价值衡量与试错,在疑难案件中教义学方法通过寻求一个妥当的判决来进一步明确、修正、更新和完善教义学体系。*参见陈坤:《法律教义学:要旨、作用与发展》,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近年来,法律论证作为一种新兴的法学方法也不断主张要在“开放的”教义体系中论证,法教义学越来越具有开放性和反思品格,今天的法教义学不再局限于纯粹形式逻辑化的思维,而越来越注重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这几乎也成为了人们的一种普遍共识。因此,对法教义学而言,这不仅不是告别,反而是一种发展之后的重生。
[责任编辑:吴岩]
Subject:Between the Norm Constraint and Justice of Individual Case: On Value Judgment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Dogmatics
Author&unit:SUN Haibo
(Law School,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fter the conceptual jurisprudence has been got rid of, how can judges well receive “norm constraint” while maintain “justice of individual case”, has been an enigma of methodology of law. Frequent emergence of hard case and rising of social legal science, has made legal dogmatics caught in an embarrassing situation. Meanwhile, due to these two extreme judicial theories of “adjudication according to law” and “Discretion”, fail to respond the proposition of how could judges be bound by legal norms when they pursue justice of individual case. Value judgmen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mprehensive balance emerges at the right moment, it can defend the legal attribute in adjudication of hard cases by following formal rules, coherence and the principle of minimal damage, while it can also ensure furthest the certainty of judicial adjudication.
legal dogmatics; value judgment; hard case; norm constraint; justice of individual case
2013-11-06
孙海波(1986-),男,江苏徐州人,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哲学、司法制度和法律方法。
D90
A
1009-8003(2014)01-007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