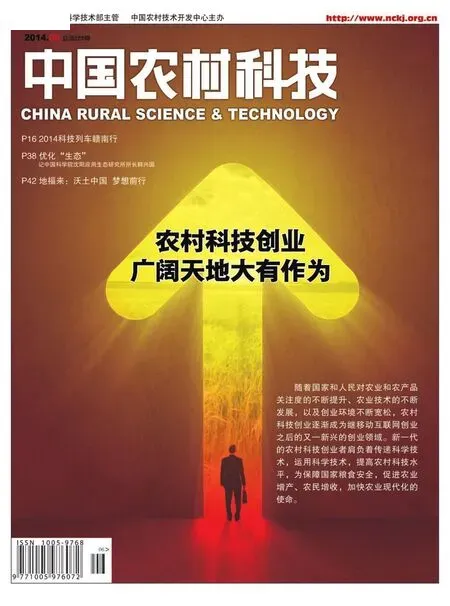优化“生态”记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所长韩兴国

生态,即生命的状态,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生态学,是生物学的一个分支,研究生物之间及生物与非生物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他是生态学领域的知名专家,一直努力为自己寻找更好的生态环境,也一直殚精竭虑为他人创造更好的生态环境,营造更好的生态群落。
他叫韩兴国。
祖国的“生态环境”最适合自己发展
1992年,在美国学习工作了7年的韩兴国回到了中国,在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工作。当时,许多人问过他为什么回国,他的答案是“我想俺娘了”。他说,回到祖国,才是真正回到了适合自己发展的“生态环境”。
在美国,韩兴国研究“新泽西北美湿地松林的土地管理对地下食物链的影响”项目,回到祖国后,他主持了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浑善达克沙地与京北农牧交错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实验示范研究”等许多重大课题。对科研有独特思路的韩兴国,心中最明了土壤对植物根系的影响以及其相互间的作用。他同样明白什么样的“土壤”更适合自己成长:“只有中国这块土壤最适合我,我在中国这块土壤里最适合生长。”
从事生态学研究的韩兴国,少年时代的“生态环境”却不怎么好:他家是富农成分,1959年他出生时,家里不仅穷,而且还受歧视。
韩兴国说,自己16岁初中毕业后就回到生产队干活了,在生产队里当记工员,也算是一个“脑力工作者”。那时,父亲在镇上的收购站从事过磅、记账工作,自己还盘算着去接班。没想到,“文革”很快就结束了。国家恢复高考,1977年公社中学办起了高中重点班,韩兴国有幸被录取。他这个没有读过高中的初中生,第二次考试就得了班里第一名。1978年,他考入了山东农学院农学系。
4年后,他毕业留校,做了3年老师。1985年到美国后,先在乔治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又去阿肯色大学做助教,后到罗格斯大学做博士后研究。
生态学研究领域的大家
在生态学领域,韩兴国是同行们公认的大家、领军人物,他的系统研究和创新观点在业内产生了重大影响。近些年,韩兴国主要研究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系统功能、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他提出,不同物种和功能群之间的补偿作用导致生态系统稳定性增加,回答了国际生态学研究中争论已久的多样性与稳定性的关系问题。同时,从进化生态学和生态系统学的角度,韩兴国提出了植物在群落分布中的优势度与该植物在水分、养分和能量等因子的利用率上有极为显著的相关性的观点,对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原则。
韩兴国先后主持承担了国内外10余项重大科研项目和国际合作项目。他两度主持国家973项目,分别是“草地与农牧交错带生态系统重建机理及优化生态—生产范式”研究和 “北方草地与农牧交错带生态系统维持与适应性管理的科学基础”研究。两度主持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作为学术带头人,他主持了国家基金委创新群体项目“北方草地全球变化生态学研究”和国家基金重点项目“草原生态系统中生源要素的计量化学关系及其耦合机理”研究。
研究草原生态,需要经常往基地跑。1998年至2011年,韩兴国一直兼任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站长。2012年夏天,他作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决定:动用了8辆车,带领40多名研究生和青年科研人员进行了一次长距离的野外考察,从新疆的巴音布鲁克到大兴安岭附近的额尔古纳,历时39天,行程15000多公里,针对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高寒草甸几种不同的草地生态系统,开展大规模调查,获得了大量的基础数据。整个行程中,他们平均布点,每个点都要做20个样方,既取表面植物,还要测一米以下的土样。39天,仅土钻就打折了几十个,用了几十万个纸袋子,每天往沈阳发货,邮寄费花了十几万元。一路上,冒着酷暑与骄阳,与泥石流遭遇,与毒蚊子周旋,修抛锚的车,真是辛苦异常。但韩兴国却很开心:“这次野外考察,我们饱览了祖国的美丽风光。我负责打前站,插旗子布点。在草原上,在旷野中,尽情地驰骋,自由地呼吸,那种感觉实在太美好了。”
其实,这次考察的真正收获,是为研究草原生态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后来韩兴国邀请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研究员周集中来生态所讲课,周集中对这次考察取得的成果评价很高。他说,这些珍贵的土样,用基因芯片进行分析总结对比,可以形成很多篇有价值的文章。韩兴国一直看重与国外华人科学家保持合作。在留学期间,他就担任过中华海外生态学者协会主席,积极推动海内外生态环境科学家之间的联络。
作为著名生态学家,韩兴国多次参加国际有关生物多样性方面的谈判,为中国、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利益。韩兴国认为,很多发达国家往往把眼睛盯着发展中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却故意忽略他们把许多高排放的工业基地设在发展中国家的事实,这对发展中国家是非常不公平的。“
“所长生态系统”生态学
在中科院,韩兴国先后担任植物所和沈阳生态所的所长。他任所长,善于把生态学原理和生态规则运用到管理工作中,适当地调整单位的“生态结构”,把所内的“生态环境”营造到最理想的状态。
韩兴国说:“搞生态系统生态学,比如长江三峡大坝建成后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我们要研究长江三峡生态的结构及其功能;办研究所也是如此,也要研究其‘生态’,适当地调整组织结构,将它的功能发挥到极致。”
“没有顶尖的人才,哪里能来顶尖的科研呢?”他常常这样说。
很快,林光辉、王晓茹、鲁迎青等一批优秀的年轻人从世界各地来到植物所,他们为韩兴国的真诚与热情所感动,更看重植物所为自己提供的能施展才能、做出成就的那个平台。
相对于一般“环境”而言,“生境”对生物具有更实际的意义。韩兴国说:“既然要吸引优秀人才,就要给优秀人才创造出优良的‘环境’与‘生境’。”林光辉教授放弃美国的教席到植物所当首席研究员,韩兴国把他作为“百人计划”引进,成立了“稳定性同位素生态学”课题组,投入200多万元购置质谱仪,让他在所里挑了两名助手。从瑞典一所大学引进的另外一位“百人计划”人选王晓茹,植物所积极帮助她申请国家级重点课题。为解除在美国研究进化生态学的鲁迎青的后顾之忧,在她回国之前,植物所就为她安排好了住房。
韩兴国对植物所振兴所付出的努力和所里取得的巨大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服在心里。2002年,植物所试行职工代表对全所管理人员信任投票,韩兴国得了“A”。中科院每年对所属研究所进行分类评价,植物所年年是“A”。
2006年,连任两届所长的韩兴国从植物所卸任。他专心搞科研,认真地给研究生上课,空闲时随着心性读点书。他讲授的“生态系统生态学”,深受研究生们好评。
2008年,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所长职位出现空缺。科学院领导班子反复斟酌,决定请韩兴国出山。路甬祥院长亲自和他谈话,为他分析生态所的发展形势,韩兴国再次挑起了一所之长的重担。
当时,沈阳生态所和北京植物所在人员配备和影响力上,相差较大。而急需改进的,就是加强与国内外顶尖科学家的交流,快速壮大研究队伍和科研力量,拿到国家级大项目,组建有影响力的研究平台。
为改变生态所力量相对薄弱的状况,韩兴国首先从壮大研究队伍抓起。明了国家的大需求,熟悉相关领域的人才,在同行中有较强的影响力,爱为朋友帮忙形成的好人缘,这些都赋予了韩兴国组建队伍的特殊优势,他很快就引进了一批科研骨干。不到两年,生态所拿到了两项973国家重大研究项目,申请到了森林与土壤生态、土壤养分管理两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实现了科研力量上的重大突破。
借鉴植物所成熟的运转模式,在沈阳所,韩兴国进一步加强课题组的建设,强化组长的责任。每个课题组都有相对稳定的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年富力强的科研骨干和思维活跃的年轻人共同打拼。这种运转模式,可以充分发挥团队的优势,集中力量攻克难关。更重要的是,不同年龄段的成员相搭配,可以在工作中更好地锻炼培养年轻人。当一个课题组的实力足够壮大时,他会将其拆分成两个或者3个课题组,继续培养更多的年轻人。课题组之间相互协作,形成组群,集中目标凝练研究方向。
在生态所,韩兴国最看重的还是吸引顶尖的优秀人才。遇到有影响力的年轻人才,韩兴国会下大气力做工作,喝酒聊天交朋友,积极解决现实困难。两年前从美国回来的谢灵天说,决定回国之前,他考察过很多地方,韩所长的坦诚一下子就打动了他。除了引进,韩兴国更看重培养现有的年轻人。他和所里几位知名专家一起,选拔了一批30多岁的年轻人,成立了5个青年创新团队,重点培养。这种培养的方式很特别,一个年轻人可以有几位导师,一位导师也可以同时指导几个年轻人。年轻人和导师自由沟通,有问题随时交流,接受点拨。这种培养方式非常有效,2012年,所里有两位年轻人申请到了国家优秀青年基金。
韩兴国所作的努力几年就得到了回报。2008年之前,在科学院对所属研究所的评价中,沈阳生态所位居中游,评级介于B和C之间。2012年,该所一步迈进A类所行列,进步之大,引人注目。
始终保持自己心底的“原生态”
韩兴国个子高,体型瘦,善交友,喜读古书,走路迈大步,说话果断利落,做事讲规则,欣赏人批评人都喜欢直截了当。对国家、对单位、对母校,以及对家人、对学生,他的关心与爱也是热烈直接、坦诚实在,是一种至情至性的原生态的爱。这种原生态,来自他良好的素养,来自他心灵深处的浓浓情意。
韩兴国对学生做的论文要求很高,但也给他们足够的成长时间,并努力教会大家方法。为了帮助更多的学生,他花了一两年的工夫,拆开了5000多篇文章,形成了《生态系统生态学英语例句库》,免费发布在Planta论坛上。句库里包含了16630个词条的用法,72460个例句,先后有10万人下载。同学们可以从这个句库里学习规范的表达方式和重要词汇的用法。目前,韩兴国正在编辑中英拉丁文植物学词典,做了3年,已完成了大半。做这些事情,韩兴国凭借的是兴趣和过人的记忆力,真正把这些东西呈现出来,则是靠熬夜工作。
家庭是韩兴国最看重的。他孝顺母亲,关心兄弟姊妹,深爱着自己的妻子和女儿。1992年,韩兴国从美国回来,告诉别人他回国最直接的理由就是“我想俺娘了”。从1992年回国到2005年母亲去世的十几年间,不管工作多忙,每逢春节、五一节、中秋节、国庆节、母亲的生日和父亲的忌日,他雷打不动地一年回6次寿光老家。回到家,陪着母亲说说话,看着母亲脸上的笑容,他觉得那是最心安的时刻。家里兄弟姊妹7个,他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如今,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大都完成了大学学业,韩兴国备感欣慰。他动情地说:“在寿光老家,我经常体会到被亲人需要的感觉,特别美好。”谈起女儿,韩兴国更是充满骄傲,女儿在北京受到了良好的中小学教育,在香港读了大学和硕士。
沈阳生态所图书馆里,有三排架子,放的全是韩兴国捐献的杂志和图书,这是他多年积累的最宝贵的财富。在美国读书和工作时,他最兴奋的事情就是去买书,甚至经常托朋友从法国和意大利买书捎给他。几年间,仅书费就花了上万美元。中间,还复印了多本专业杂志。回国时,这些书刊被装进24个箱子,花了700美元海运回国。回国后,这些书刊跟着他去了云南,后来又回到北京,中间不停地增添壮大。2008年到沈阳生态所工作后,韩兴国决定把他这些宝贝送给所里。课题组的老师在北京整理打包,六七十个箱子又坐上火车到了沈阳。生态研究领域里的代表性杂志,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韩兴国都复印并留存着,2万多篇文章,俨然就是一个小小的专业数据库。
这里,A1、A2、A3的定义同式(11).与式(40)中等号右边第3项分析类似,可得窃听节点信号部分的功率值趋于零,即窃听节点在第2跳中的接收SINR为0.因此,N→时,窃听节点两种用户间干扰处理能力情况下系统可实现保密和速率将分别趋于
“我想给母校的老师提一个建议,退休后把自己的书都捐献给学校。这些书放在自己家里用处有限,但对青年学生来说却是珍贵的资料。”谈起母校、老师、同学,回忆起大学生活,韩兴国充满了感情。
当时他们班里32个学生,最小的只有15岁。最年长的大哥、班长曹荣玖和韩兴国住一个宿舍。刚入校时,曹大哥经常一个人去提满所有热水壶,很快,小兄弟们也争着去了。吃饭的时候,一大盆菜端到饭桌上,曹大哥负责分,但他从来不给自己盛肉吃。“很可惜,曹大哥现在已经去世了。”说起同窗好友的英年早逝,韩兴国很伤感。
即使毕业后,同学们也相互激励、相互帮助。现任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的曹鸿鸣,与韩兴国是同窗好友。毕业后在德州农校工作期间,韩兴国鼓励他考硕士、读博士,一路向前走。两家人是至交,两家女儿的小名听起来就像姊妹,连大学专业、找的工作都是相近的。“同学加兄弟,是我心中最为珍贵的情感。”韩兴国说。
谈起老师,韩兴国有说不完的话:“王洪刚老师那时大学刚毕业,当我们的班主任,师生在一起,跟兄弟似的。丁巨波、余松烈、胡昌浩、陈希凯、张高英老师,每个人讲课都有特点,到现在还想得起他们在课堂上的神态。包文翊老师不爱说话,我跟着他在农场实习小麦育种,一粒一粒地数麦子。教外语的赵松祥老师格外和蔼,大声地领着我们读英语,常常是下课了师生还意犹未尽。毕业后跟着李风超老师当助教,从农场回来,李老师每次都买两包烟,一包送给我,一包带回家给薛坚老师。”
韩兴国很郑重地给母校提建议:“我们学校出了不少杰出校友,我熟悉的就有时玉舫、刘同先、李云聪、黄炳如等。我建议学校充分发挥这些著名科学家的作用,在他们退休之后,聘他们回来教一门课,或者带带学生,可能会影响到很多学生的未来。”
热情淳朴,坚定执著,坦荡赤诚,富有爱心,这就是韩兴国心底始终保持着的“原生态”。从在乡下老家务农到考入高等学府,从远赴海外求学到学成报效祖国,几十年来,韩兴国一路走来,无论年龄、阅历、学识、职位怎样变化,他身上所始终不变的就是心底的“原生态”。正是有了这一“原生态”作底色,韩兴国在致力于不断优化个人、单位和自然“生态”环境的事业中,书写了色彩斑斓的人生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