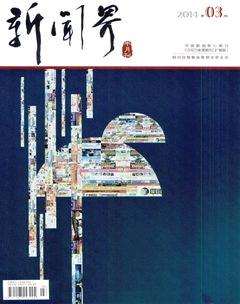政治与文艺的合谋:五十年代台湾报纸副刊研究
摘要:20世纪50年代是国民党在台湾推行文艺政策最为关键的时期,这些文艺政策的推行经常诉诸道德或伦理内化于社会集体的无意识。当时副刊推动“战斗文艺”已不仅仅是配合“文宣需求”的表态,而是文化界一种所谓的“共识”。一方面,当时聚集在蒋经国周围的“青协”作家群,以及以张道藩为首的“文协”阵营,都融入到这股氛围里;另一方面,也少有编辑、作者敢于公然冒犯文艺政策背后的威权文化。
关键词:五十年代;台湾;副刊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 刘晓慧,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广西南宁530004
1949年5月,台湾地区实行“戒严令”,从此进人长达38年的“戒严状态”。20世纪50年代,台湾社会政治上是绝对的威权统治;经济上是土地改革后的农业形态;社会遵循的是儒家伦理。报业在这十年可说是由重建到紧缩。许多专业报人以及对新闻事业有高度兴趣的人士随国民党迁台初期,或复刊旧报,或创办新报,其办报理念与办报手法为台湾报业的发展注入生机,极大地促进了当地报业的发展。台湾地区于1949年8月公布《台湾省新闻杂志资本限制办法》,并相继提出“限证”、“限印”、“限张”、“限纸”等十余项法令后。新闻出版自由被严加控制,动辄得咎。“报禁”政策对申办新报或维持经营都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整体上导致了传播媒介在公共言论领域的萎缩,公、党、军营报纸固然如此,就连民营报纸亦复如是,舆论功能完全由台湾当局操控。这种以行政措施干预言论自由及新闻事业的做法,彰显着报禁时代台湾特有的媒介生态,也带来台湾报纸副刊发展的特殊形态。
一、从可有可无到固定刊登:五十年代台湾报纸副刊发展
50年代台湾报纸上的副刊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每家报纸都有的文艺副刊,如《中央日报·中央副刊》、《台湾新生报·新生副刊》、《中华日报·中华副刊》、《联合报·联合副刊》;一种是每周一次或若干次的各类专刊,如《中央日报》每周一的《儿童周刊》、周二的《读者之声》、周三的《大陆透视》、周四的《储蓄园地》、周五的《地图周刊》、周六的《现代家庭》,《联合报》每周一到周日的《家庭》等。本文主要探讨的是传统的文艺副刊,以下简称副刊。台湾戒严初期,发行量较大的报纸非党营即公营,较有影响力的副刊也大多居于这些报纸之上,如《中央副刊》、《新生副刊》、《中华副刊》、《青年战士报·青年副刊》等。民营报业中,《联合副刊》、《公论报·日月潭》、《自立晚报·万家灯火》等也颇具影响。然而早期的副刊是名副其实的“报屁股”,“可大可小”一一随新闻、广告之多寡决定当日版面之大小,刊载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一一既有文学创作,也有漫画、菜谱、科技发明、生活小常识、笑话趣谈等。前《中央副刊》主编孙如陵曾如此描述当时的副刊:“可七可八,可上可下,可有可无。”亦即副刊栏数不定,位置不定,甚至还处于有时未能见报的尴尬地位。这一时期副刊编辑运作以作者投稿、编辑选刊为主。早期的副刊编辑基本上由报社工作人员兼任,且“唱独角戏”。“限张政策”限制了报纸空间,为了扩充内容、多登广告,版面“分割”极为严重,副刊直接受到冲击。当时的副刊由于篇幅不大,五千字以上的作品不能容纳,所登文章多短且杂,最多的还是涉及怀念故土风光、污蔑共产党以及日本、欧美作品译介的文章。
台湾文学史将50年代的文学归为“回忆的文学”,主要是“战斗文艺”,副刊隶属于文学场域,自然无法避免。台湾当局常常以政经援助的形式,使副刊充当“战斗文艺”运动的阵地。副刊在寻求台湾当局支持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程度不同地沦为政策文学(宣传文学)的工具。台湾各报副刊,如《民族副刊》、《新生副刊》、《中央副刊》、《中华副刊》、《全民日报·副刊》、《经济时报·副刊》等,纷纷调整征稿范围和办刊路线,尽量突出具有“战斗意识”的作品,或自动或被迫地带上程度不同的特殊时代的政治色彩。
1954年,在台湾当局的授意下,“中国文艺协会”掀起文艺政策风潮,通过“文化清洁运动”,把“战斗文艺”推向台湾社会各界。众多直接或间接地为“战斗文艺”服务的副刊,对当时的文艺发表渠道形成垄断与操纵的局面。以“军中文艺”的推广为例,“战斗文艺”占领《新生副刊》后,为了接受现役战士的投稿,小说、散文、新诗分别聘请了几十位作家,为投稿的战士改稿。《中央副刊》、《中华副刊》等纷纷辟出版面,以特设管道鼓励“军中文艺”的创作。50年代文艺阵地的互为网络、彼此影响,使它们往往“以统一的步伐最大限度地控制文坛走向,掌握着作品发表的生杀大权”,为“战斗文艺”运动的泛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集体书写的模式由权力共谋阶层所发动,副刊上“战斗文艺”的泛滥显示台湾当局在报业领域和文艺领域强大的控制力,能达到驱策作家持续营造,以笔为枪的重要目标。
从50年代开始,台湾报纸副刊逐渐趋于随着政经情势变化,报业体制改变,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报业、不同的副刊内容导向。二·二八事件后,台湾地区以整肃思想言论作为政治控制的一种手段,标志着“白色恐怖时代”的来临。在文化传播上通过“出版法”、“广电法”内的部分条文,限制传播媒介的创设及内容的发表;在新闻出版业的管理上,主要由四家机构进行:其一是“国民党文化工作委员会”;其二是“警备总司令部”;还有台湾新闻主管部门以及台湾法务部门调查机关。这一时期,国民党在台湾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政治力及文化力呈现被扭曲与宰制的畸形面貌,而报纸副刊也见证了当时媒介与文艺的处境。
二、作为阵地的副刊:“战斗文艺”运动的推广
(一)副刊“战斗文艺”量产的组织背景
因应文艺政策,台湾当时奖金最高的文艺奖项与规模最大的作家团体,在国民党刚败退至台的1950年便匆忙在一个月内相继成立。先是蒋介石指示张道藩创办的“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于4月成立,紧接着5月4日“文艺节”当天,仍由台湾当局通过张道藩,结合陈纪滢等大陆赴台作家约两百人联名发起“中国文艺协会”。《中央副刊》以整版制作“纪念文艺节专号”,刊发陈纪滢的《感慨而不悲哀——祝中国文协成立》、茹茵的《开张大吉一一祝中国文协成立》等散文及诗。这两个文艺团体领导层的权位之高,是之后的文艺团体所无法比拟的,决非一般的民间团体,何况“文奖会”一年数十万台币的财源,全由国民党宣传部门编列经费。文艺团体为政治服务的中心思想不言而喻。
(二)封闭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副刊与“主导文化”亲密而复杂
国民党文艺政策的始作俑者张道藩在1952年“五四文艺节”当天的《联合副刊》上发表《论当前文艺创作三个问题》,大肆鼓吹“战斗文艺”。在此前后,《新生副刊》、《民族副刊》、《中央副刊》等台湾当局“战斗文艺”主要媒体开设的一系列“战斗文艺”笔谈、大讨论、座谈会,都是围绕国民党文艺政策所进行的种种鼓吹,其目的不外是把台湾的文艺运动以及报纸副刊纳入到政治服务的轨道上来。
台湾当局的授意与副刊的鼓吹使文艺界“战斗文艺”的呼声颇为喧嚣,1950至1952年三年内从事“战斗文艺”写作的作家便达1500至2000人之多。1954年,在台湾当局的授意下,“文协”掀起文艺政策狂潮,通过“文化清洁运动”,将“战斗文艺”推向台湾社会各界。11月5日,台湾内政主管部门公布“战时出版品禁止或限制刊载事项”,对出版及新闻自由诸多钳制。1955年春,蒋介石正式提出“战斗文艺”的口号。国民党的文艺政策成为台湾文坛及文学传播的主流,而“带给文艺以战斗任务”的50年代台湾文学传播,表现在报纸副刊上,则形成一个“被系统扭曲”的传播体系。文艺政策配合着来自政治力量结构的运营,通过“戒严法”、“总动员法”、“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管制办法”、“出版法”以及报纸“限张”、“限证”等政策之控制,严格地限制与操纵副刊上的传播内容。有关“战斗文艺”的创作,蔚成一大风尚。各报副刊都竞相发表此类文稿,以表明立场和态度,《新生副刊》前主编尹雪曼说,当时征集到的作品就达万件。“战斗文艺”运动以台湾当局话语霸权的姿态,深深影响了50年代的报纸副刊,而“战斗文学”占据了50年代副刊版面的重要位置。
实际上,国民党于政治和军事上的败局,致使台湾全岛陷入所谓的“狂飙猛进”、“惊心动魄”之中,并衍化成一种无所不在、有形或无形的“权力”。当时台湾当局所塑造的重归故里的愿景“正好代表了流放者的心态”,国民党统治台湾初期,这种愿景“在人民的政治心理上根深蒂固,没有人敢怀疑”。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对此做了精辟的注解:社会集团主流话语无疑会表现为社会精神与道德的领导权。而且,作为一种现实的政治权力,特别是在社会结构的“重组”这一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下,也必然会构成对整个社会历史文化空间的强有力的覆盖和制约。因为任何借助政权的“物质力量”实施的文化领导或文化渗透,都只能建立在强制性的灌输上,而不是劝说和感动。诚如当年直接受命于台湾当局的《民族副刊》,就在发刊词中明确提出:“配合战斗!配合建设!配合革命!我们必须歌颂战斗!”某种意义上,副刊及副刊文学“精神与道德的领导权”与主流意识形态具有特别暖味的关系,甚至达到难以剥离的胶着状态,其自然就充当了这一政治权力意志的体现者;顺理成章地充当了社会话语权对社会矛盾认知功能的实践者,情感上价值评判的精神代表。可见,在台湾当局威权式掌控文化生产与消费的时代,副刊始终是推行文艺政策的一大主力。
三、文艺团体与副刊的互动及影响
(一)两大文艺团体对副刊的渗透
50年代副刊成为战后一个庞大有力的文艺作品生产机构,也是文坛重要的组成单位。副刊的运作彰显出“文化场域”与“权力场域”的曲折关系,更显现当时文化场域整个被笼罩在一个更大的权力场域之下。当时各报副刊皆以配合台湾当局的“政治宣传”为编辑主轴,为进行对文艺界的监控,台湾当局刻意扶植两大文艺团体。
1950年5月4日由张道藩领导成立的“中国文艺写作协会”,为当时台湾当局最重要的文艺宣传机构。此协会前身即国民党于1950年3月策划组织的“副刊编者联谊会”。“副联会”汇集了当时主导文艺界的各大报副刊主编,包括《中央日报》的耿修业、孙如陵,《中华日报》的徐潜,《公论报》的王聿均,《经济日报》的悉志全,《扫荡报》的萧铁,《大华晚报》的薛心镕,《华报》的沉哈、周鸡晨、顾孟鸥,《台湾新生报》的冯放民、袁良等,还有国民党宣传部门的任卓宣、高荫祖、罗时旸以及张道藩、陈纪滢等当局要员皆名列其中,这些成员即后来运作“文协”的主力人物。在“文协”的带动和副刊的倡导之下,作为“战斗文艺策源地之一”的“中国青年写作协会”于1953年8月2日成立。两大组织以服膺台湾当局文艺政策为原则,致力于文艺与政治的结合。
50年代严峻肃杀的社会氛围使作家团体纷纷采取主动向当局表态的模式彼此规约,因应国民党当时内外交迫的形势,进行“效忠”、“守分”的宣示,并对其中的重要角色委以重任,让他们担任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副刊的主编,如《中央副刊》、《新生副刊》、《民族副刊》、《日月潭》等。而副刊主编与作者一旦被强行纳入文宣战争的一元化轨道,其御用性格和工具效用也就不可避免地日益暴露出来。毋庸置疑,副刊作为文坛聚光灯照射的大舞台,势必被纳入文艺团体的操控之下。当时“文协”、“作协”之中坚分子多为报社副刊主编,文艺政策自当得以贯彻落实。
(二)“文人圈”对副刊的把持
与此同时,从另一个方面来看,50年代那些活跃于副刊的作家及知识分子,也未必是受到政治的压迫而不得不表态,相反,他们之中也有国民党的拥护者与支持者。他们随国民党败退赴台,通过创作“彻底响应国民党对文艺发展的指示”,这亦显示了50年代政治威权的有效性,正如赫伯特·马尔库塞所言,“个人若对加诸身上的要求作自动自发的再生产,并不表示他确立了自主性,反更证明了控制的有效性。”此外,我们也需注意到,植基于与政治权力、意识型态一致之上的这些作家,同时也是“50年代台湾文艺界(文化界)的霸权所在”。通过“文协”、“青协”,他们全盘地掌控了国民党控制下的台湾文坛,垄断了整个文艺活动达十年之久,掌握了所有文艺传播的主要媒介,副刊自然也不例外。《民族副刊》主编孙陵、《新生副刊》主编冯放民、《中央副刊》主编耿修业等都是“文协”成员,50年代的文学与副刊“几乎由大陆来台第一代作家所把持”,他们构成了当时特有的“文人圈”。无论外省还是当地作家都积极地向这个“文人圈”靠拢。因为,作家最迫切的需求在于晋身为“文人圈”中的一份子。一个作家一旦可以进入“文人圈”,就等于他获得了一个身份证明而可以在“文人圈”这个权利场域中游走,因此,50年代的作家紧随“文协”、“青协”,因为“50年代任何一个作家一旦被文艺协会所摒弃的结果,正是被放逐在文坛之外”。
除了作家,不少“文艺爱好者”也想“占据”作家“位置”而投入到副刊“战斗文学”的创作中。副刊作为当时文艺作品极为有限的发表平台之一,作者只要努力让作品在副刊版面上出现,次数一多自然能引起读者注意,从而具有“作家”资格。且副刊作为每日或一周数次出刊的文学版面,作品的需求量较大,对新晋作家来说,命中率较高。换句话说,副刊是当时想“占据”作家“位置”的人必先经过的道路。如此也就导致了作者依据副刊的“喜好”进行创作,比如“战斗文艺”作品的大量出现。直到1958年钟肇政与钟理和在通信中,依然强调个人书写碍于台湾当局文艺政策、文艺团体及副刊的主导,必须寻求妥协以达到登载的效益。当时钟肇政提及:“报纸扩版后,各种副刊都有了些转变,‘战斗文艺大批出笼,大家都在拼命登着,战斗性文字,内容多半拙劣不堪……我们需要多写,磨练文笔,偶尔发表发表,系也属不可厚非,有限度的迎合是可以原谅的。”
50年代“文协”、“青协”两大组织的庞大动员力主要源自台湾当局的政经援助,致使这些文艺团体能有效地贯彻台湾当局的文艺政策所赋予的任务,成为台湾当局确保其统治的有效手段。个人主义被台湾当局文艺政策的整体机制所压迫,不进人“组织”便面对噤声的焦虑,这种危机意识充分宰制着文艺界,使得个人与台湾当局命运互相依赖的书写结构得以持续推演下去。致使台湾当局意志对报纸副刊的全方位控制,也宣告了一个为政治服务的副刊时代的到来。但到50年代末期,“战斗文艺”运动逐渐式微终成强弩之末,“战斗文艺”的弊端也暴露无遗,甚至连“御用文人”都在1958年1月5日的《联副》上刊发文章《岁首说真话》,表达对这种“只战斗”“不文艺”的创作的反感。
结语
1949年,国民党败退至台,同时宣布全台戒严,对于新闻言论更是严格管控;1951年以“节省纸张”为由,停止新报登记,“报禁”开始,形成“一报五禁”扭曲的媒介生态。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副刊在报业结构中,基本上被限定在“文艺性”的传统框架之中,这一方面是源自副刊传统的延续,另一方面也由于报业本身所受到的政治力的控制。在报业运作中,外有政治压力的警戒,内亦有“自我检查”的功能存在,而副刊由于其论述功能易触犯“禁忌”,因而被作为守门人的主编们有意识地朝向文艺及娱乐的方向发展。此外,除了上述所谓政治结构的外力影响之外,这段时期的副刊也承受着国民党文艺政策下文艺传播的扭曲与压制,造成五十年代的“噤声现象”。
50年代是台湾当局文艺政策推行最为关键的时期,除了张道藩主导的文艺政策,1951年蒋经国还发表了《敬告文艺界人士书》,号召“文艺到军中去”,1953年蒋介石又发表《民生主义育乐两篇的补述》作为国民党在文化层面的“施政纲领”。这些文艺政策的目的在于“通过文艺推动革命”。而且,这些文艺政策在建构过程中或多或少都借用了“道德”的合理性,亦即文艺政策的合理性经常诉诸道德或伦理内化于社会集体的无意识。当时媒介推动“战斗文艺”已成为一种“应然”的态度,换言之,那已不仅是配合“党政文宣”需求的表态,而是当时文化界一种所谓的“共识”,汇聚成一种伪道德力量。一方面,当时聚集在蒋经国周围的“青协”作家群,以及以张道藩为首的“文协”阵营,都融入到这股热潮的氛围里;另一方面,也少有编辑、作者敢于公然冒犯文艺政策背后的威权文化,以免受到政治立场不稳的怀疑,遭致杀生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