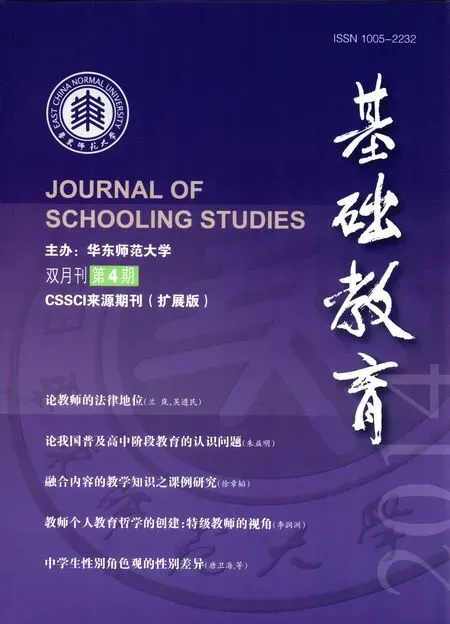民国时期农村基础教育政策及其变迁特征*
慈玲玲,曲铁华
(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吉林 长春 130024)
民国时期农村基础教育政策及其变迁特征*
慈玲玲,曲铁华
(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吉林 长春 130024)
民国时期农村基础教育政策变迁研究是上承清朝末期农村基础教育政策研究和下启新中国时期农村基础教育政策研究的关键性、重要性研究内容。民国时期农村基础教育政策变迁大致经历了民国前期发轫与渐进、民国中期发展与改革与民国后期调整与拓展三个阶段,并在政策制定、实施与变迁中体现和遵循着其特有的历史规律,回眸民国,以期总结得出符合当前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进一步发展的变迁特征。
民国时期;农村教育;基础教育;教育政策
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在觉醒中逐渐走向重生,艰难地开始着现代化的历程,其政治、经济、文化也均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渐发展、成熟和完善着,作为构成要素之一的教育,也必然包含在内。民国时期农村基础教育政策的变迁是上承清朝末期农村基础教育政策变迁和下启新中国时期农村基础教育政策变迁的关键性、重要性连接历程。纵观民国时期农村基础教育政策的发展,大致经历了民国前期发轫与渐进(1912—1926)、民国中期发展与改革(1927—1936)与民国后期调整与拓展(1937—1949)三个阶段的变迁历程。进行民国时期农村基础教育政策变迁的细致研究,不仅是对民国时期农村基础教育政策领域研究成果的充实,同时也会对我国当前基础教育、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基础教育政策的科学发展、完善与超越储存着智慧、启迪着思绪,表现出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一、民国时期农村基础教育政策的变迁历程
(一)民国前期农村基础教育政策的发轫与渐进(1912—1926)
1912年1月19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14条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11条,这是民国成立之初改革清末封建教育的纲领性指导文件,其政策内容虽未直接针对农村教育但其对于农村基础教育的恢复和发展仍起到了全局性承上启下的过渡性指引作用。时至1913年末,“壬子·癸丑学制”在学校教育内在发展的必然轨迹下最终确定,更是极大地推动了民国前期包括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基础教育在内的学校教育转型、过渡和发展。同时1913年,教育部拟定《强迫教育办法》共6条,其中“(二)调查属内村镇相距若干里及村乡镇户口数目,以便比较。(三)各县各村乡镇内派学董若干,以专责成。(五)此项经费由各村乡镇人民担任,不得在该属内已筹定之学款挪用。”[1]322强迫教育(即民初基础教育或义务教育)正式以法定形式颁发于民国前期教育政策与法律的文本中,同时6条内容中有3条内容直接涉及到规定“村”字样的农村基础教育发展办法。这不仅对于民国前期义务教育的普及与扩展发挥着重要的规范与导引作用,而且内容层面上对于农村行政区划范围内的关注与侧重更加突显出民国政府在农村基础教育领域内的政策支持与保障。1915年,袁世凯颁发了《颁定教育宗旨令》和《特定教育纲领》,倒行逆施,并在封建复古教育宗旨的指导下随之颁布了《义务教育实施程序》(1915)、《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1916)等一系列倒退桎梏性政策文件。1916年范源濂再次出任教育总长,且于本年9月教育部通令各省区撤销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期内所颁布的《教育纲要》,随后,教育部又修正了一些有关政策、法令,再度取消了小学读经。这就基本恢复了民国元年的教育宗旨和政策,民国时期的基础教育政策几经波折之后再次踏上了偏向于进步性发展方向的轨迹。
1919年3月,教育部公布《全国教育计划书》,明确指出教育的重要性,并对作为国民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国民基础教育作出了合理性的全面规划,以期指导全国范围内各地区,尤其包括农村地区基础教育的方向性发展。1920年4月2日,教育部拟定《分期筹办义务教育年限》,从而确定了分期筹办全国义务教育发展清单,即“国民十年省城及通商口岸办理完竣。民国十一年县城及繁镇办理完竣。民国十二年五百户以上之乡镇办理完竣。民国十三年三百户以上之市乡办理完竣。民国十四、五年二百户以上之市乡办理完竣。民国十六年一百户以上之村庄办理完竣。民国十七年不及百户之村庄办理完竣”。[1]327-328基于农村基础教育而言,其明确规定“1927年完成一百户以上之村庄义务教育的普及与发展,1928年完成不足百户之村庄义务教育的普及与发展,全国义务教育分期发展规划自上而下分级分层完成”且已经明确规划至村庄,并以一百户为限,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地规划与管理,这将对包括义务教育在内的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与普及产生规划性的全局引导与推动作用。1925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议决《实行义务教育应规定筹款颁发案》,明确指出各县市筹集义务教育经费办法,并最终形成以地方政府自筹为原则,各县市乡镇承担筹集义务教育经费重任的政策规定。从积极意义上讲,这使得全国范围内义务教育经费的筹集有了权责分明的责任承担主体,明确了义务教育推行的经费承担对象。
(二)民国中期农村基础教育政策的改革与发展(1927—1936)
1927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政变”,从根本上背叛了孙中山“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新民主主义思想,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1929年4月26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1931年9 月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检送《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致国民政府公函,这对于三民主义教育宗旨及其思想如何在教育领域尤其是基础教育领域也必然包括农村基础教育领域内的落实和推行作了具体规定和说明,三民主义教育逐渐形成完整的政策理论与实施体系。基于实行三民主义乡村教育的必要性与重要性,1930年3月17日,国民党中央秘书处检送实施三民主义乡村教育案,并致中央训练部函即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公函第297号,于同年3月4日讨论、决议了《实施三民主义乡村教育案》。“实施乡村教育之办法与步骤:第一,必须训练健全之师资;第二,必须奋起开办乡村学校于各省。兹就此二部方法,确定其主要内容如左:一、造就师资;二、分期举办乡村学校。”[2]《实施三民主义乡村教育案》明确指出造就师资与分期举办乡村学校成为实施乡村教育的有效方法与步骤,并分别从乡村教育培养期限、训练标准、课程类型和实施方法与乡村学校程序施行和经费来源作清晰明了的阐述,从而为三民主义要求下乡村教育的迅速发展与全面普及指明了确切的方向。随后,1931 年4月29日,教育部颁发《乡村小学充实儿童学额办法》,“一、乡村小学儿童名额,除有特殊情形,经主管教育行政机构许可者外,每一教室不得少于二十五人,其名额不足者,应设法充足之。二、乡村小学校长教员,应劝导附近人民速送已届学龄之儿童入学。三、乡村小学为应付特殊环境起见,得由校长商请校外热心教育人士为本校义务招生委员,调查本校四周一公里内之学龄儿童,并督促其入学。四、乡村小学学额不足时,其附近一公里内,不得另设招收九周岁以上儿童之私塾。其有设塾影响于学校招生时,得由校长呈请主管教育行政机构勒令停闭之。五、二所以上之乡村小学校校舍邻近而学额无法补足者,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得酌量合并学校或学级。六、乡村小学得减缩寒假或年假日期,酌放农忙假,其时期由各地方教育行政机关规定之。七、乡村小学为减轻人民负担使子女易于入学起见,得多设免费学额。并得由主管教育行政机关,酌给书籍用品,或购办书籍用品,以供贫苦儿童借用。八、乡村小学应酌设补习班,招收十岁以上失学儿童入学补习。”[3]217-218这就使得乡村小学的儿童入学率得到了更进一步的重视,且已然成为民国中期农村基础教育普及所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之一。
1932年12月,国民政府颁布《小学法》,1933年3月,教育部颁发《小学规程》,这表明国民政府完成了初等教育在学制方面的局部修改与变动;同时1932年10月,教育部对各地实验的教学科目酌加修正,颁定《小学课程标准》,三部政策法规的相继颁行标志着民国中期初等教育体系基本定型。1935年6月20日,行政院颁布关于《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施行细则》之教育部指令。《教育部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施行细则》主要由总则、强迫入学及缓学免学、施行程序、师资、校舍设备、经费、机关、奖惩和附则共9章34条内容构成,且第3章第10条更是明确规定“各省市在实施义务教育第一期内,为供给儿童受一年义务教育起见,应举办下列各事:(一)广设短期小学,限令各小学区就预定设校地点设置一年制之短期小学,招收九足岁至十二足岁之失学儿童。此项小学以采用二部编制为原则,每日上下午各教学半日或全日间时教学,至少各授课三小时或四小时,修业年限一年。乡村短期小学及其他学校与公共机关内,并得附设前项短期小学班……(三)试行巡回教育,得令各地方设置巡回教员,依时轮住穷乡僻壤交通不便利处教授失学儿童,其程度与短期小学同。各省市为推行义务教育之便利,除上列各项办法外,并得采用其他适宜之方法。”[4]624-630《教育部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施行细则》的若干规定详尽细致到乡村短期小学和巡回教育,其在政策层面上对于民国中期农村基础教育的具体规定极具重要性与科学性。1937年6月,教育部检发《二年制短期小学暂行规程及课程标准总纲》的训令,其中《二年制短期小学暂行规程》第12条规定如下:“二年制短期小学假期以与普通小学一致为原则,在乡村地方酌量情形,免去星期例假、缩短寒暑假,另放农忙假、赶集假等;每年上课日数,不得少于二百日。”[4]638-6401937年6月1日,教育部公布《实施巡回教学办法》,并规定“区域辽阔,村落星散,交通不便,儿童不易集中者”[3]315-317可设置巡回教学班,由一个教员巡回施教。同时,“巡回教学班分下列二种:(一)长期集合者:每乡村或每一适中地点设置一班,学额须在十五人以上。每班儿童数不满二十人者,一教员至少教学二班。儿童全日或上下午半日在校,教员来校时,由教员直接教学或考核;教员离校时,由导生领导自动学习。(二)临时集合者:每乡村或每一适中地点设置一班,学额约五人至十五人,一教员至少教学三班。平时儿童各自分散至规定时间集合,由教员来班教学,或由导生领导学习。”[3]315-317《二年制短期小学暂行规程》《实施巡回教学办法》等一系列推动国民义务教育(基础教育)发展且在短时间内提高义务教育普及效率的重要政策选择,尤其是其对乡村义务教育的直接关注和具体规定,将会极大地推动民国中期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与普及。
(三)民国后期农村基础教育政策的调整与拓展(1937—1949)
1937年,抗日战争正式爆发,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中国基础教育事业尤其是农村基础教育事业的正常发展开始面对着极大阻碍。1938年4月,国民党政府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并通过《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领》,制定了“抗战建国”的基本国策,并最终确立了“战时当作平时看”的教育指导方针,强调“小学教育,应为国民基础教育,以发展儿童身心,培养其健全体格,陶冶其
善良德性,教授以生活必须之基本技能,养成其好学习惯,使其应对进退合乎礼节,以为将来自立之准备。故施教之对象,应及于全体学龄儿童,国家对于全国各地应普遍设立各类小学,使全国学龄儿童均有入学之机会,在预定年限内,达到普及教育之目的。同时全国人民,对于子女均应尽强迫入学之义务,使全国学龄儿童,至少须受此最低限度之义务教育”[5]22。抗战期间,基于政治统治思想控制的需要,国民党政府实行与当时战争环境相匹配的“新县制”,并于1939年9月公布《县各级组织纲要》,规定“县为地方自治单位,下设乡(镇),保、甲则为乡内的编制,以十保为一乡,十五甲为一保。新县制以所谓‘管教养卫合一’为基本指导方针”[6],同时根据《县各级组织纲要》,教育部于1940年3 月21日订定《国民教育实施纲领》。其第3章第9条明确说明:“国民学校以每保设立一所为原则,称某保国民学校,保之人口稠密、面积不及四方里者,或一村一街之自然单位不可分离者,得就二保或三保联合设立一所,称某某保联立国民学校。保之面积过于辽阔而村落疏散者,其国民学校得分设班级于名校落,或设置巡回教学班。”[5]423《国民教育实施纲要》依据“新县制”的推行,教育与战时政策一体化,将小学改称为国民学校及中心国民学校,推行儿童义务教育与失学民众补习教育且政教合一的新国民教育制度,对当时特殊战争时期国民教育的向前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导向标作用,同时也标志着民国后期基础教育政策开始由义务教育制度向国民教育制度重要转轨,农村基础教育政策的方向转轨也必然包含在内。1940年5月6日,行政院阳字第9565号训令核准公布《小学教员待遇规程》,尤其提及“乡村小学教员,呈经主管教育行政机关之核准,得接受儿童家庭关于食宿之供给,其办法另定之”。1942年3月,教育部公布《保国民学校设施要则》,其中第3则规定如下:“国民学校以每保联立一所为原则。保之人口稠密而面积不及四方里者,或一村一街之自然单位不可分离者,得就二保或三保联合设立一所,成某某保联立国民学校,保之面积过于辽阔而村落疏散者,其国民学校得分设班级于各村落,或依照实施巡回教学办法设置巡回教学班,施行巡回教学。已设有中心学校及中心学校周围距离三里以内之保,不另设国民学校,其应就学之儿童及民众,应入中心学校小学部及民教部肄业。”[5]439《小学教员待遇规程》和《保国民学校设施要则》正是对农村基础教育国民学校方方面面的直接概括,重视并强调农村基础教育的普及与发展已经成为民国后期教育政策制定与实施层面上的理论与实践认同。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在教育复员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普及国民教育的拓展方案。要求未实施国民教育的收复区省份,从1946年1月起拟定《第一次实施国民教育五年计划》,要求后方已实施国民教育的19省市,从1946年1月起,贯彻《全国实施国民教育第二次五年计划》,以充实国民学校和中心国民学校为中心工作,务求学校充实,师资健全,经费稳定,各省失学儿童和失学民众都能接受义务教育或补习教育。1946年12月25日国民大会通过,并于1947年1月1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宪法》,其专设第13章第5节教育文化一节,即“第159条,国民受教育机会一律平等。第160条,六岁至十二岁之学龄儿童,一律受基本教育,免纳学费。其贫苦者,由政府供给书籍。已逾学龄未受基本教育之国民,一律受补习教育,免纳学费,其书籍亦由政府供给……”[3]69-70《中华民国宪法》教育文化专节的具体颁行,使得国民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基础教育在教育文化、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机会、教育均衡发展、保障机制、监督机制、教育经费、奖励或补助等方面的有关规定有了宪法的保障和支持,极大地推动了民国时期基础教育政策也必然包括农村基础教育政策的法治化进程。1947 年8月6日,教育部订定《国民教育设计委员会教导组讨论纲要》,且在修订课程、改善教材、充实设备、改良编制、革新教学、加强训育和注重卫生共7个构成部分中作了详尽规定,如“为适应城市、乡村、山区、海滨、西北、东南各地方的实施起见,应由各省市编订地方性的课程,以期配合各地的实际需要。”[7]185-186“在学龄儿童稀少的乡村国民学校,采用二学年、三学年复式或单级编制。”[7]187等等。民国后期的农村基础教育政策在不断地调整与拓展中逐渐完善、详尽、科学化和法治化。直至1949年,国民党政府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溃败、失势和破产,最终结束了其长达38年的统治,从而使得为国民党政府政治目的服务的包括农村基础教育在内的国民教育事业宣告终结,并遵循历史的脚步,走进了下一个教育发展的新时期。
二、民国时期农村基础教育政策的变迁特征
(一)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发展
民国时期十分重视国民教育,并始终把发展农村教育作为国家发展、民族复兴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只有重视农村教育,重视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才能完成整个教育发展规划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重视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这不仅需要理论上的正确认识,同时也需要国家政府在具体教育实践中给予农村教育实质性的政策帮助和支持。民国政府时期,其行政院和教育部对于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和发展专门制定了诸多的教育政策文件,为农村义务教育发展过程所需要的必要人力、物力和财力提供了政策性的绝对保证,并始终把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放在国民教育发展的首要战略地位。重视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把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放在战略位置,这就需要国家政府在政策制定和教育实践中给予农村义务教育实质性的帮助和支持,主要表现在:
1.保障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经费投入
国家重视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就必须保障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财政经费投入,以避免因资金短缺而影响或阻碍农村义务教育的正常有序发展。民国时期义务教育经费的筹措问题,始终是义务教育工作者和推行者十分关注的重要议题。《各省县市筹集义务教育经费暂行办法大纲》(1925)、《义务教育经费支配办法大纲训令》(1935)和《保国民学校及乡镇中心学校基金筹集办法》(1940)等直接或间接相关于义务教育财政经费投入的教育政策措施的颁行,均试图在国民政府教育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的范围内,“开源、节流并整理”[8]219,保障发展农村义务教育过程中所需的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充足且稳定永久,从而使得民国时期各个政权统治时期的中央或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共同担负起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所需要承担的资金筹措和投入责任。
2.保证农村义务教育政策灵活变通
发展农村义务教育,不仅需要财政经费上的充分支持,同时也需要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教育政策措施上的大力支持,而相关农村义务教育政策制定上所应具有的灵活性和变通性,也将是农村义务教育实现施行目标效果的必要条件。因为“中国近代推行义务教育的基础很薄弱,条件很不成熟,这逼迫义务教育的推行者对其举措采取变通方法,从实际出发,因陋就简,实事求是,务求实效”[8]253,“所以,与其说全国推行义务教育‘齐步走’,全国一体实现义务教育的宏伟目标,不如说延迟义务教育实施之期,降低义务教育文化水准,贻误中华民族的千秋大业”[8]254。民国时期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实施义务教育一年制短期小学暂行规程》(1935)、《一年制短期小学暂行课程标准》(1935)、《短期小学实验办法》(1935)、《二年制短期小学暂行规程及课程标准总纲》(1937)、《实施二部制教学办法》(1937)、《巡回教学办法》(1937)等一系列直接或间接相关于农村义务教育政策措施的相继出台,使得农村义务教育政策的实施和推广更可因时因地制宜,同时民国后期1946年教育部公布的《全国实施国民教育第二次五年计划》更将未实施国民教育的收复区省份和后方已实施国民教育的19省市分开制定不同的义务教育发展规划,灵活性和变通性由此凸现。
(二)确保农村基础教育政策体系科学化
“同清末相比,民国时期无论在学校制度、教育规模、课程设置、学科标准、教育质量等各方面,都有较大的进步,并大体完成了从闭关锁国的中世纪‘原生态’,向同国际接轨的开放型、多元化‘新生代’过渡。”[9]民国政府在其掌握政权的38年间公布了一系列教育法律、法规、法令,教育政策体系门类齐全、内容丰富,教育立法日臻完善。农村基础教育政策框架体系进行法治化、规范化和科学化选择,各项相关规定、标准、要求趋于统一,益于推进民国时期的农村基础教育政策步入规范、统一、科学管理的发展轨迹,从而使得民国时期农村基础基础教育的发展地位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和加强,这对于促进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的提高有着积极意义。以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发展义务教育为例,1929年6月,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讨论普及教育案,议定厉行国民义务教育及成人补习教育相结合的国民教育制度。此后国民政府根据厉行国民义务教育的决定,在《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1931)的引导下,先后公布了《实施义务教育初步计划草案》(1935)、《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施行细则》(1935)等政策法规,并陆续颁布了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具体的相关于农村义务教育的政策。“这些法规分别就有关义务教育的总则、设施、组织机构、施行程序、分期实施计划、经费、师资、课程、教材、教法、视导、评估、年限、惩罚等项作了较为周密的规定”[10]215,从而使得农村义务教育政策体系在法治化和规范化的发展过程中更加科学化,对民国时期农村义务教育的提倡与推行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前,教育发展面临的形势日趋复杂多变,各种关系纵横交错,确保农村基础教育政策体系科学化,逐渐形成科学的农村基础教育政策体系,这已经成为提高基础教育政策效能的必由之路。“运用科学的理论方法,根据教育发展的客观背景和自身规律,科学预测教育发展的趋势,调整政策措施,争取主动,能够有效提高其效能,促进教育政策的不断完善”[11],农村基础教育政策体系的科学化过程就是农村基础教育政策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确保农村基础教育政策体系的科学化,对于推动农村基础教育的正常、稳定和科学的发展至关重要。
(三)强调农村基础教育政策制定本土化
民国时期是中国包括农村基础教育在内的基础教育从模仿到探索以期创新的本土化发展时期,突出中国意识和时代意识,强调农村基础教育政策制定本土化,在学习、模仿、借鉴西方先进的农村基础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探索适合本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口现实国情的本土化教育政策体系对基础教育的发展至关重要。“中国20年代的教育改革,有条件追随世界的潮流,吸收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博采各国教育之长,为我所用,改造已不适应国内国际形势的中国教育,为中国的富强独立做出新的贡献”[10]201。民国时期三次最为重要的学制系统改革就是教育政策制定的本土化过程,突破西方基础教育发展模式对民国农村基础教育政策的制定模式,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模式,对于推动当时当地农村基础教育的实施与进步具有决定性的关键作用。对我国当前农村基础教育政策的制定、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来说,制定教育政策尤其是农村基础教育政策一定要适应我国当前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口国情,一定要适应当地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口实情,因地制宜,一切从实际出发。教育政策措施的制定一定要符合当前政治、经济、文化的现实分析,尤其是根源于农村现状分析上的农村基础教育政策制定尤为重要,这是因为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口因素将影响和制约着教育发展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发展中教育目的、教育结构、教育内容、教育手段、教育管理体制、教育组织结构等方方面面的选择和决策。重视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口要素对教育发展、基础教育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影响,以广阔的视野全面审视教育,强调教育政策、基础教育政策、农村基础教育政策制定的本土化,将会直接推动着我国教育、基础教育、农村基础教育更为健康、更为科学的向前发展。
(四)提高国民接受基础教育参与度
民国时期农村基础教育政策的不断规范和完善,在政策层面上具体保障了国民基础教育普及和发展的可能性。民国时期农村基础教育虽然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尤其是个别省市县如广西和江苏省属范围内基础教育得到了实质性和成果性发展,但全国范围内的很多地区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状况并不理想,很多全民教育规划及至义务教育分期计划等最终都未真正实施和完成。民国时期农村义务教育实施和完成的现实情况必然是与当时当地的社会政治经济国情密切相关的。推行义务教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就必须全民参与,这种参与的程度越高,义务教育的效率也就越高。否则,义务教育仅仅是政府行为,失去了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仅为政府一厢情愿,其效果是不言而喻的”[8]251,可见,提高国民接受基础教育的参与度已然成为农村基础教育政策实施和推广过程中实际效果的最直接的影响要素。只有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接受基础教育的积极性,并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大力支持,规范化、合理化和科学化的农村基础教育政策才能有成为现实的可能性。总之,为使义务教育的推行收到良好的效果,就必须全面提高国民的参与程度,广泛深入地开展农村义务教育方方面面的宣传教育活动,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青少年受教育者接受教育积极性。同时,必须考虑广大农民群众的现实利益要求,自觉维护广大农民群众的合法利益,使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认识到推行基础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充分尊重广大农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主观作用,促使广大农民群众成为农村基础教育活动过程中的主要力量,全面提高人民参与农村基础教育的参与度,依法履行国民接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提高国民接受基础教育参与度,提升国民即受教育者与政府的默契度与配合度,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才会有巨大的力量源泉支持,农村基础教育政策的实施目标才能真正成为现实。
[1]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2]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M].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1022-1026.
[3]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史研究室.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1912—1949)[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M].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一)[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6]李桂林.中国现代教育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244.
[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教育)(一)[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8]熊贤君.千秋基业——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9]李华兴.民国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804.
[10]宋恩荣.近代中国教育改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4.
[11]孙绵涛.教育政策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1.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ural Elementary Education Policy Change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I Ling-ling, QU Tie-hua
(Faculty of Educatio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Jilin,130024)
The rural elementary education policy change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the link between the rural elementary education policy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at of New China, and also the important research content. The rural elementary education policy change roughly undergoes three stages:namely commencement and gradual advance in earlier days; development and reformation in the middle period; adjustment and expansion in the later time.Besides, the change reflects its historical laws of policy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review of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order to conclud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licy chang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ural elementary educatio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rural education; elementary education; educational policy
G629.20
A
10.3969/j.issn.1005-2232.2014.04.004
(责任编辑:金忠明,朱振环)
(责任校对:姚 琳,朱振环)
2014-05-12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民国时期农村基础教育政策研究”(项目编号:12SSXT11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9年度重大研究项目“中国农村教育百年历史考察与当代关照研究”(项目编号:2009JJD880007)。
慈玲玲,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曲铁华,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慈玲玲,E-mail:cill700@nenu.edu.cn